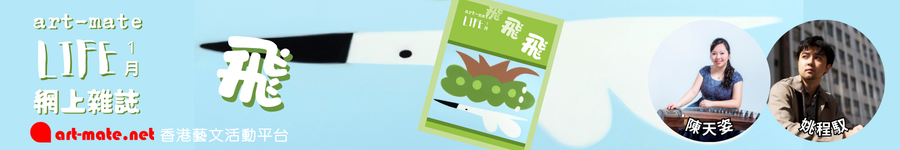跨出圈圈互相認識 激盪出不同的面貌
李昕宜X劉佩芬X鍾汶叡Q:因為國藝會藝術未來行動專案「神鬼人間道台灣劇場未來式」計畫,你們才能夠認識彼此,在開始接觸之後,你們感受到彼此的劇團有什麼差別嗎? 鍾:我覺得去年的衝擊比較強。因為第一年就是認識,去年才開始正式工作。 例如那時候來EX-亞洲劇團排《普羅米修斯》,因為Jayanta的排練方法相對凝重,對我來說,他的詮釋方法要很慢,然後要走進心裡最深的地方,再湧出來。我們自己劇團排練時,好像都沒這樣去想過一句台詞,阮劇團比較在意的是台詞背後的動機、角色之間的關係等。 李:我印象深刻是發展的速度。 像是跟Jayanta工作,通常會讓我們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去發展;但同樣的段落,身聲劇場就大概是半小時,而阮劇團會是10分鐘! 劉:對我來說也是衝擊很大。 像昕宜講到創作,Jayanta會印圖片給我們,然後看圖,要我們去延伸、去發展,這對我們來講是不習慣的,因為我們比較少用「看圖」的這種方式,也比較少用討論的方式,比較是用身體、用樂器直接做。同樣地,阮劇團也很需要動腦,所以跟他們一起排練,就得講很多話,而身聲就相對少用語言團長都說,不要用你的頭腦,放下頭腦。 同樣是即興,身聲是用身體,阮就像是在用語言。 李:每一團好像都有個自己劇團的翻譯官在解釋導演的想法,但大家其實都沒有講好,誰要負責這件事情,很自然會在過程裡面,有人出面統整這件事情。 鍾:我覺得阮劇團的演員是蠻自由的。 對我而言,我更在意的是「我們這群人」,會有點投入自己的感情,因為跟他們一起玩蠻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