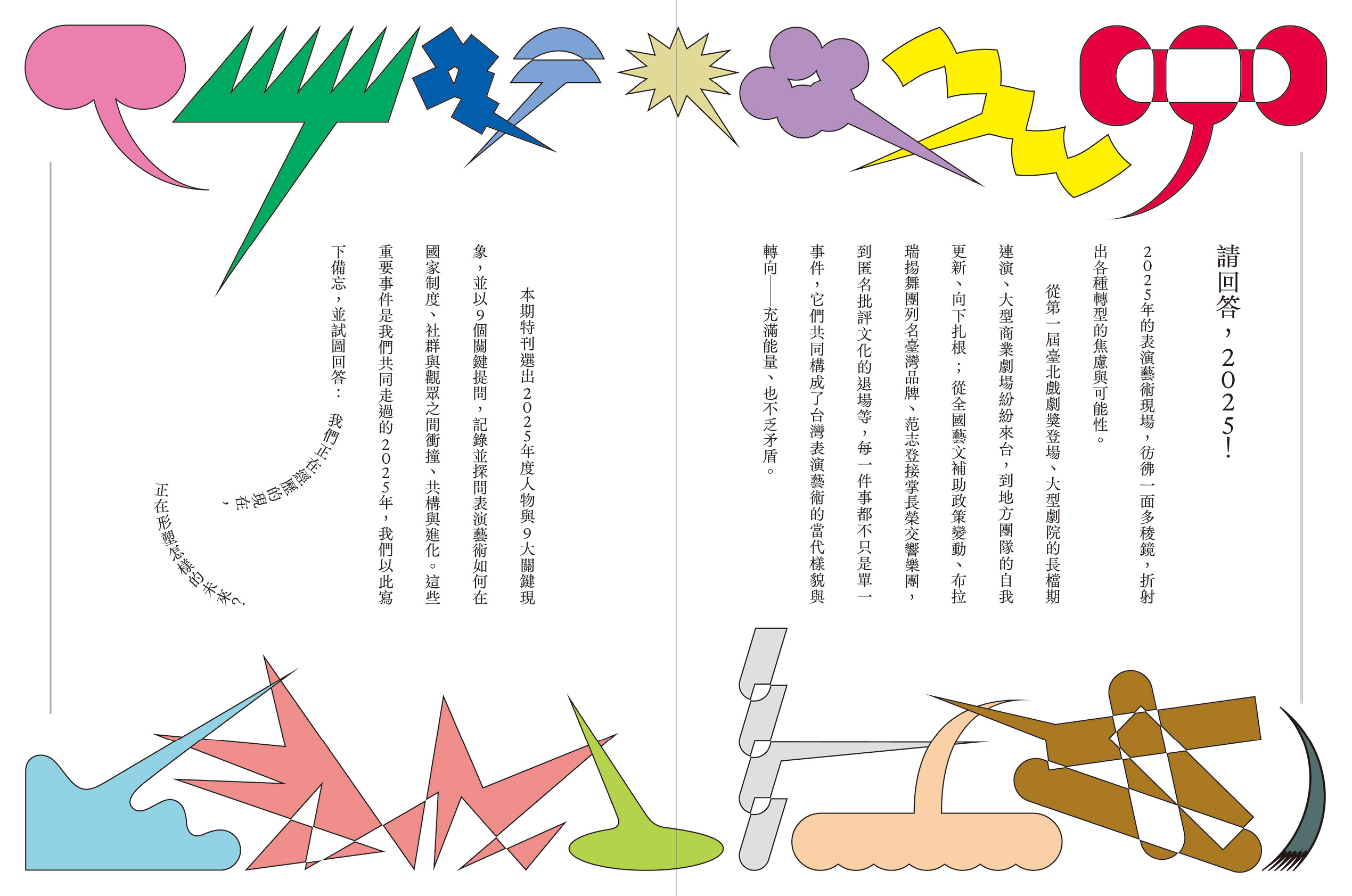二月份,国际剧评人协会台湾分会与香港分会合作,邀请罗马尼亚籍剧评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柯迪维.萨尤来台,举办为期三日的剧评人讲座与工作坊。趁此机会,本刊特地安排专访,请萨尤一谈他对剧场评论的思考:评论人与观众的不同何在?在自媒体当道的时代,评论人如何让专业得到重视?
「我们所居之地并非国家,而是语言。(We do not live in a country, we live in a language)」,这句出自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之言,是剧评人柯迪维.萨尤(Octavian Saiu)三日讲座中第二日工作坊「连结诸世界,连结众文化─论全球公众领域的戏剧批评」之开场白(注1)。的确,语言之界有时甚至比国界更严峻,它决定了我们个人的认知,更决定了文化传承与知识建构,决定了作品的创作与诠释——正如萨尤须以所谓「国际共通」的英语来介绍东欧剧场,正如三日演讲不可或缺的口译,正如访谈时一段小插曲:萨尤引葛罗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说明“Spectator”与“Audience”之差别(在此他强调的非字根视/听差异,而是个人观众与集体观众的分别),我好奇地问著,葛氏当初的思考是基于波兰文或英文呢?毕竟就我所知,中文并无特别强调这样的分别。萨尤不可置信地说,所有语言都该有单复数的观众区分(这么一说,中文写作中「令人」与「令我」倒是时常混用的)。我苦无机会解释我所居住的语言对於单复数的混用,或也反映著「个人是为了成就群体」的价值观。但这短暂的争辩倒证明了建构在语言上的文化翻译/转译,自有其不可避免的落拍。
掌握已知承认无知 才能开始面对未知
于是,拿著不同语言护照的我们,如何成为萨尤于香港座谈受访时自诩的「国际评论人(global critic)」呢?(注2)这是我对萨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毕竟我们皆同意,再有学识的评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特别是今日当我们以评论人的身分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戏剧体系甚至是跨界训练的作品时,我们又有什么立场掌握话语权?
近年与中国乌镇艺术节合作密切,且长期关注日本剧场的萨尤以自身经验回应:「我经常去日本,对日本剧场、传统演出多少有点认识,但我从不会试著要了解关于日本传统戏剧的所有一切,相反的,我会让自己保有某些空间去惊叹、赞叹那些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所见,那些我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秘。」并引用挪威剧作家乔恩.弗斯(Jon Fosse)之言:「我们全然了解的,就不再存在了。(that, which we completely understand, ceases to exist)」,强调全知就丧失了吸引力,剧场一定要有未知的神秘。在此同时,评论要能理解到自己理解力的界线。换句话说,掌握自己的已知,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面对神秘的未知。
在已知与无知间的平衡点,正是评论得以施力的空间,这也是为何萨尤提醒著:「评论也是观众,只是是更有相关知识的观众。」(注3)一旦评论人忘了自身观众的身分,误把自己当作真理代言人,以为自己有权力、有立场告诉其他观众「剧场是什么」,抑或是告诉创作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则会让评论陷入险境。「评论提出诠释(interpretation)而非判决(verdict)。」这是萨尤的信念,「武断的论断不容讨论空间,或许尚存在于十九世纪末或廿世纪初,但已非现在我们对于评论的期待。」现今的戏剧经验,需要另一种对于评论的想像,不再受传统所限制,更深刻也更复杂。
理解并贴近创作者 却须避免成为创作者
「评论也是观众」,实回应于我就萨尤引用葛氏「剧场为演员与观众之相遇」的延伸提问。当然,这或也是萨尤心目中理想评论人的立场——尽管他也坦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于评论人的定义与期待也有所不同。以此反思台湾现况,评论人在创作者与观众两种身分间游走,却早已是见怪不怪的常态。萨尤并未分享同为「小国」的罗马尼亚是否也有类似现象,倒是在一向侃侃而谈的态度中闪现一丝犹疑:「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绝对答案,事实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扪心自问。」
评论人该不该是创作者?先不论评论伦理,这却是另一个评论如何「找到平衡」的微妙处。「理想上,评论该知道所有的门派学说、潮流趋势,但同时也得独立于所有门派之外。」萨尤说。距离要够近,才能够懂剧场、够爱剧场;但距离也要够远,才能保持观众立场。针对此议题,萨尤多次强调是他的个人观点:「我反对评论太持续、太热中地投入于某一团体或门派,最终与之成为一体,无法抽身……当你身为剧场创作者时,也背叛了你的观众身分。」只是,萨尤也明言「创作」如此迷人,让评论人忍不住也想成为艺术创作者,唯只能提醒自己也能以评论的身分参与另一种创作。「理解创作者,贴近创作者,却要抵挡心中那股成为创作者的诱惑。」是萨尤对评论身分的另一提醒。
讲座之后
跨领域讨论 尚须真的「跨」出学科
萨尤的第三日讲座以艺术节为题,原以为会延伸前一日关于艺术节如何助长剧场商品化的讨论,但不知有何让他改变了心意(或是其实是题目带来的期待落差),改以两出分别在爱丁堡艺术节与戏剧奥林匹克(The Theatre Olympics)演出的作品 The Encounter 与 Armine, Sister 为讨论重心。前者是合拍剧团结合机器人与操偶形式,重现人类学家落难至亚马逊原始部落,以心电感应与居民沟通的改编故事,却让观众戴上耳机,模拟脑对脑最私密的见闻经历;后者则是TEATR ZAR试图回返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史料、音乐等素材面对屠杀之后的噤声哀歌。两出作品演出细节与回响皆可见于网路,然真正勾起我兴趣的,是萨尤提到他也以主席身分参与了上述艺术节为这两出作品举办的研讨会,除了创作者之外且各自邀请了如The Encounter 的声音设计Gareth Fry、长期参与排练过程的脑神经权威Iain McGilchrist或与亚美尼亚大屠杀研究相关的历史学家、民俗音乐学家、作曲家共同参与讨论。
这让我想到前一日萨尤对于「议题凌驾美学」的感叹,事实上又何止美学,无论评论或是创作者,能在「实质内容」上著力之处还有太多。剧场艺术既然是由「人」萌发,自然牵扯到种种环绕著历史文化、科学科技的学门,创作者须以扎实的背景梳理为作品立基,细节的掌握度正在于功课是否做足,评论人何尝不是如此?今日所谓跨领域讨论,往往仅局限于人文哲学底下的理论派别,更多时候是以文字解释文本的纸上谈兵,若能试著整合甚至掌握实务界的学科,不也因此打开了剧场的视野与评论的可能性?(白斐岚)
人物小档案
◎ 现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立戏剧影视大学副教授,主要教授剧场与戏剧文学。
◎ 自2004年至今担任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的学术会议主席,2014年开始担任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主席;目前是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总会副秘书长,同时出任「尤涅斯科—贝克特」研究中心主任。
◎ 于2010年获得「评论人奖」,亦于2013年获得戏剧艺术家协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