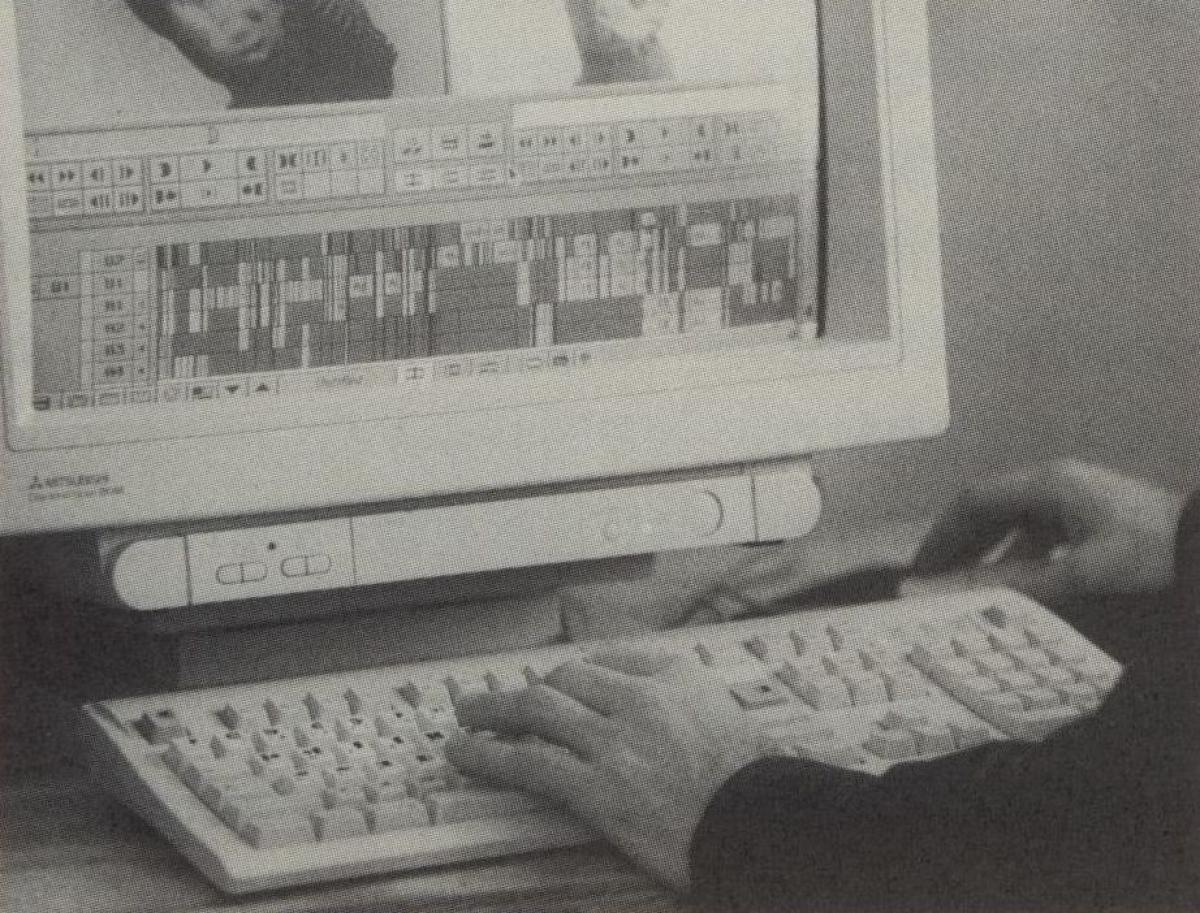原住民舞蹈镶嵌在祭仪中,以影像的方式被保留下来,
其精神可被了解、传达及尊重。
台湾原住民部落风情的影像纪录,拍摄者多以文化理解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部落发掘山地族群的各个生活面向,诸如教育、经济、工艺、祭仪、政治等传统过渡至现代的议题,而影片呈现时最吸引人的画面,往往是穿插于这些议题中的祭仪歌舞。当我们进一步探讨纪录片所载的祭仪歌舞部分时,得先厘淸拍摄时是将这些歌舞片段视为「祭仪风俗」而采集,还是视为「舞蹈艺术」而保留?中央硏究院民族硏究所硏究员胡台丽,在民族人类学的专业领域中,曾拍摄了《神祖之灵归来─排湾族的五年祭》、《矮人祭之歌》等,性质上偏向采风纪录的影片;而在担任「原舞者文化艺术团」的演出策画时,为了让来自不同部落的舞者学习其他部落的舞蹈,以摄录影机拍了好几卷的乐舞录影带,则偏向保存舞蹈艺术。
以下将以访谈问答的方式,请胡台丽叙述这两类有关原住民祭仪歌舞纪录片的构思、制作、拍摄等过程。
拍摄原住民乐舞的缘起?
我在受人类学硏究训练的过程中,曾经对民族志影片(注1)有长期的接触与反省,影像带给我的震撼触发我去学习电影理论与技术。一九八三年我从美国完成学业回来,以排湾族的「五年祭」为对象制作民族志电影。在此之前,只有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记录过此活动,因此我怀著极高的兴趣,进入台东县达仁鄕土坂村,拍摄了《神祖之灵归来─排湾族的五年祭》这部影片。
一九八六至八九年,我从事「台湾土著祭仪及歌舞民俗活动之硏究」的计划,论文是以文字形式发表的,但是做田野时我选了七个族最重要的祭仪拍摄实况录影带,这些录影带虽然是硏究用途,我还是稍微剪辑了一番。但是这个部分的「歌舞」实况,重点在于它们如何嵌在祭仪中,而不是当作「独立的」歌舞来看待,它的背后有个文化架构在。另外,在进行这个计划的同时,我还著手拍摄一部纪录片《矮人祭之歌》,以赛夏族北祭团的「矮人祭」十年大祭为对象。
资料无限资源有限
这两部纪录影片的筹拍过程、机器设备条件如何?
八三年拍《神祖之灵归来─排湾族的五年祭》时,曾企图与新闻局、中影、电视台(无线的三台)等单位合作,但没有成功。后来意外发现中硏院民族所有一部越战时期美援的十六厘米手转发条式(Bell & Howell)摄影机,我在专业摄影师周业兴的帮助下,了解如何使用这部机器,再添购二十卷一百呎的底片(一百呎约可拍摄三分钟的影片)。由于当时纪录片根本没有同步录音技术,我另外准备从美国带回来的Sony Professional Walkman录音机进行录音。
整个「五年祭」祭仪活动共十天,二十卷底片实在极为有限,每天只能使用两卷录影带(约六分钟长);录音则用了二十几卷(六十分钟) 卡式录音带。当我在访问录音的同时,也一边构思影片的剧本,再确定必要呈现的画面。在这种片断取镜的情况下,加上机器的限制每个镜头都很短,后制作期花了许多时间剪接。录音带的内容请人译出,我依据文献资料和自己的田野纪录,写出剧本一稿,然后再补拍一些画面。
八四年四月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的钱孝贞协助完成后续的工作,她利用码表计算画面中声音的长度,以达到类似同步录音的效果。影片完成版本共三十五分钟,拍摄率(以完成总长度除以花费底片总长度计)约三比一。
真实文化与展演差异
八六年拍《矮人祭之歌》时,得到摄影家张照堂及电影工作者李道明的协助,以一部二手的同步录音机(李道明自购)、CP十六同步录影带(向电视台借)进行拍摄。这部片得到中硏院民族所、文建会、柯达影片公司及台北影业冲片厂的赞助,拍了近两万呎的毛片,片子完成总长约一个小时,拍摄率十比一。由于有专业摄影、较充裕的资本,事前关于影片的设计与发想都可以较自由。
纪录片中的歌舞祭仪部分,如何采集?拍摄者的观点与选择为何?
前面曾经提过,纪录片中的歌舞不能独立来看,它们属于祭仪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进入部落要进行采访纪录时,其实要面对的是原住民祭仪的神圣与私密,「纪录拍摄」的介入与「外人异族」的参与,成为双方(纪录者与被纪录者)必须最先解决的问题。排湾与赛夏都允许我们将其歌舞祭仪拍摄纪录,只是要求片子完成后回村里播放。而我身为一个纪录者,拿著机器想要「忠实」纪录原住民的祭仪歌舞时,得先完全站在原住民的立场来设想:以影像保留住祭仪歌舞文化,而不是单纯因为歌舞的艺术性,变成镜头下的「展演」形象。
其实,一个纪录者投身的切入点、文化理解的程度,都将表现在影片的呈现上。举例来说,祭仪中出现的舞步很单纯,如果就惯常的「舞蹈展演」来看,可能会觉得它的重复与单一没有结构可言;然而在祭仪中,单纯的舞步并不是无意义的重复。影片的呈现有其限制(如长镜头到底或片段跳接的取舍),观看影片的人不容易察觉这点,而这正是「文化真实」与「展演」的差距。
贴近每支舞蹈的意义
两部纪录片之外,妳在担任「原舞者文化艺术团」的演出策划时,也拍摄了许多部落乐舞的影片,这与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原舞者」的舞者来自不同部族,为了学习其他部落的舞蹈,我们将想要学习的部落舞蹈拍成录影带,让学员透过录影带来练习。歌舞镜头的取得不光是祭仪现场,有时候也请部落里的老人家示范指导一些传统古老的舞步。当然,这与前面所说纪录片完整保存的出发点不同,对部落的人而言,只是撷取歌舞部分并且将其「挪做他用」─变成纯粹的歌舞展演,则要另做考量。
沟通取得信赖之后,我们才以V8录影机拍摄了一支支的歌舞片段。摄影时取景多为全景,以特写处理细部动作。不过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去模拟舞蹈的动作、外形,或只是传达舞蹈特殊的美感,而是希望表演者能贴近每一支舞蹈的不同意义。
利用这些实况录影带,我们请平珩编写舞谱,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纪录。总之,这些录影带内容都是来自不同部落的歌舞,为了让舞者学习用的。
回顾过去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与原住民歌舞录影带,最大的意义为何?
一直以来,在台湾拍摄纪录片从经费到人力都必须面临重重难关,我的经验是「一路找经费」,幸而有如李道明这样的伙伴以自己公司的人力及设备投入、共同制作,以及中硏院年度预算的经费可以弹性运用。当初拍摄这一部纪录片《神祖之灵归来─排湾族的五年祭》经费只有十几万,虽然很辛苦,可是能为台湾原住民祭仪及歌舞片段留下珍贵纪录。渐渐地为了纪录片品质的提升,经费与设备都必须配合扩充,百余万元的投注也是必要。不过无论资金充裕与否,我们看到原住民舞蹈镶嵌在祭仪中,以影像的方式被保留下来,舞蹈动作可供学习、欣赏,更重要的是原住民舞蹈的精神可被了解、传达及尊重。
(本刊编辑 蔡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