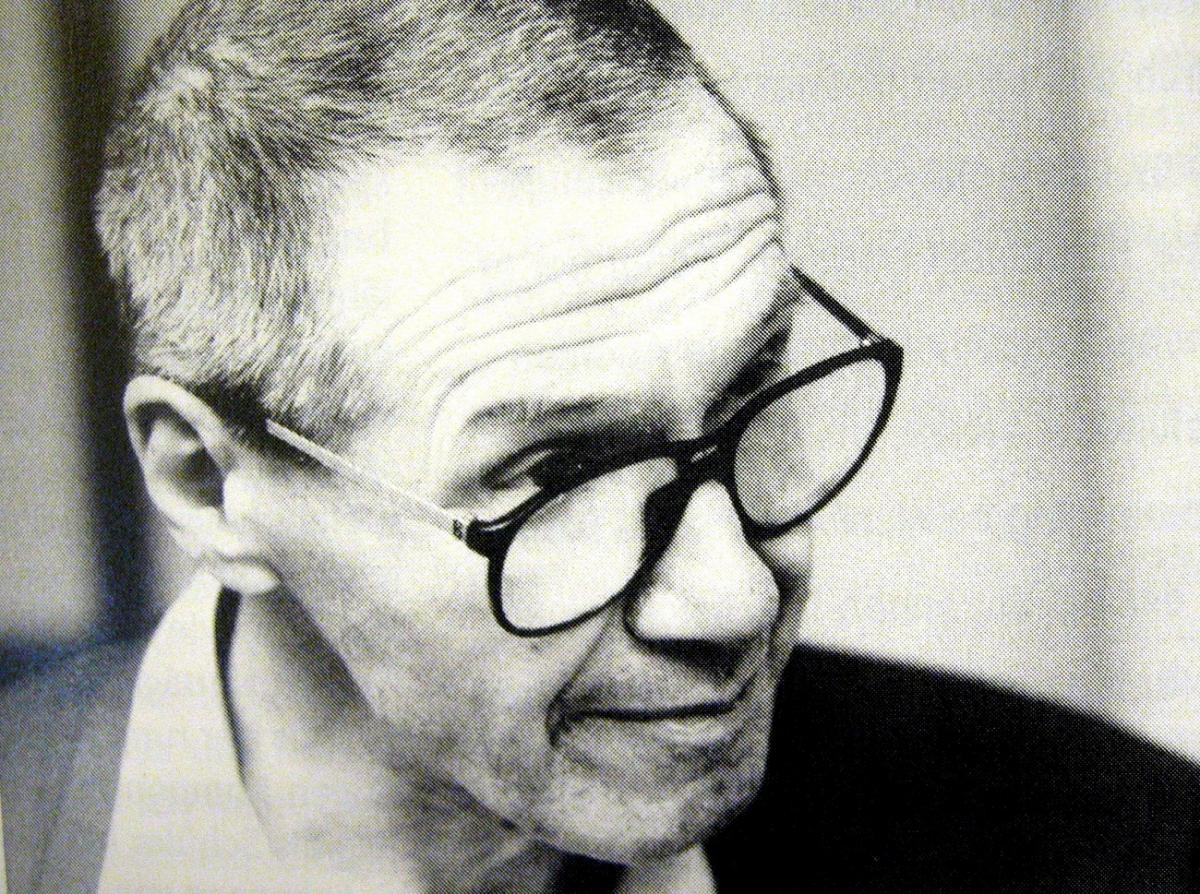黄梅戏《徽州女人》岂能为地域特性所局限?湘剧《白兔记》之动人,又岂在于宋元南戏的存古性?当戏曲已失去流行地位时,剧种特色应当「内化」为整出戏的基调内蕴,不必强调不必外显,运用多元技法触动现代人心灵,让古典和现代接轨在「感动」的情绪里,这是《徽州女人》为当代地方戏的处境指点出来的一条途径。
民国八十五年国家戏剧院和周凯剧场基金会主办「戏曲现代化」两岸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中提出〈戏曲现代化风潮下的逆向思考〉论文(编按),指出在戏曲改革过程中,编剧中心确立,导演中心也隐然成形,乐队编制扩大,序幕曲、尾声合唱、幕间曲、衬底音乐等的重要性几乎超越演员的演唱,原本以「腔调、唱功」为主体的传统戏曲质性改变,剧种之间的差异逐渐泯灭。这个说法当时引起不少讨论,与会者多认为地方戏剧种特质的淡弱是戏曲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不过我所提的是整体戏曲发展大趋势中的遗憾与失落,如果将讨论焦点集中在台湾,我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所有戏曲剧种在台湾是命运共同体
具体说来,对于大陆地方戏曲在台的演出,我并不坚持剧种特色是首要前提。我曾在多种场合中一再强调,台湾的戏曲观众人口或许有限,但是「艺文爱好者」却十分普遍,许多人把「看表演」当作生活必须的一环,他们的生活可能是:「第一个周末听苏州弹词,第二周看云门舞集,第三周看歌仔戏,第四周看表演工作坊,第五周看莎妹,第六周看京剧」,戏曲和所有艺文活动是并列的,它们在台湾的环境,不是「豫剧跟河北梆子竞争、歌仔戏和昆剧竞争」,而是「所有的传统戏曲」同为生命共同体,一起和「赖声川、李国修、林怀民、刘静敏」竞争。观众进入艺文场合就是寻求情感的宣泄和文化的陶冶,戏曲是抒情达意的载体之一,在古典和现代都已混血交融的时代,地方戏剧种特质是否能彰显,至少在台湾的环境里,我不觉得是最令人忧心的事。本文愿以近两年内的演出为例,表达我的看法。具体举证的剧目是黄梅戏《徽州女人》和「两岸戏曲大展」的秦腔、湘剧。
两岸开放以来,大陆地方戏来台数量甚多,包括汉剧、越剧、黄梅戏、河北梆子、豫剧、淮剧、川剧、徽剧、评剧、曲剧、潮剧、秦腔、湘剧、梨园、高甲、莆仙、芗剧以及一些地方小戏,票房有起有落:演传统老戏时,观众以乡亲和戏曲研究生为主;演新编戏时,观众层面比较不限特定观众群而能吸引一般艺文爱好者。回响最大的,早期有汉剧《求骗记》、《美女涅槃记》,后来川剧《荒诞潘金莲》也因复兴(现已改名戏专)京剧版的轰动而受到注意,而近两三年来最能突破「戏曲特定观众群」限制的,则是黄梅戏《徽州女人》。
《徽州女人》以视觉意象戮弄观众
我本来并不太喜欢这出戏,总觉得剧本并不很细腻,许多重要的转折关键不具说服力(例如月光和小青蛙对女子的启示),可是一进入剧场,就被整体气氛征服了。所谓「气氛」,包括一开幕的舞台景观,以及观众在还没开演之前已经「就位」的情绪。这戏最成功的是「选材」,对台湾观众而言,不太会联想到什么封建旧社会,关心的只是古代女子的命运,「曾有一个女子在等待中过了一生」,这样的宣传基调,吸引了很多不看戏曲的女性观众进入剧场。性别意识高涨之后,为女性(尤其是反面坏女人)翻案的作品已经看太多了,很多观众很期待抛弃一切「解释、新诠」,单纯地进入古代女性的世界,分享她们的心事;《徽州女人》给人这样的期待,因此许多观众一坐进剧院,还没开演就先「自顾自地」感动了起来。题材选准了,观众情绪已经酝酿到发酵的边际,只要稍稍「戳弄」一下,便足以引爆强烈的共鸣。这是编导成功的第一步,而接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戏戳弄观众的手段,不是唱念做打,而是传统戏曲一向并不重视的「视觉意象」。
戏曲的抒情手段一向放在演员的表演艺术上,对于舞美、服装等,虽然越来越有「整体剧场不可缺的一环」的认知,但是无论如何,其作用终究被视为辅助烘托,而《徽州女人》竟然反其道而行,观众对唱腔身段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某几个画面,尤其是静态画面。例如:男人有音信传回时,重新燃起希望的女人,穿起嫁时衣,端坐喜床上,喜床先在舞台前静止数秒,而后缓缓推移往后消逝,这个「被等待框住」的画面,前后好几十秒,「喜悦的凝滞」传递给人深沈的伤痛,这已经超越了「走位、舞台调度」的范畴,导演像是以舞台为画板,以演员与服装与道具为彩笔,推出一幅幅精心雕琢的「塑像」。画面构图是这戏的主体,取代了演员表演。大家对女主角韩再芬的印象不在某一句唱腔的转折,而在她某一个凝神远眺的身姿形影。这当然和戏曲的亮相不一样,像是停格,是构图的一部分,整出戏就由这些动人的「剪影」堆砌出震撼力量。
最震撼的一幕是终场前半小时,戏进入最后阶段,进入暮年的女子坐著看领养的儿子上学去,儿子长辫子一甩,雨伞一撑开,画面竟然出现了当年女子出嫁时走过的莲叶田径!就在莲叶何田田的景观开展的瞬间,时间的卷轴倏地翻转回头,像是回到生命的原点,四十年辰光,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在布幕一张一合之间流逝了!《徽州女人》的舞台上有塑像、有情感、更看得见时间,看得见时间的流逝,也看得见时间的凝滞!这感觉令人悸动,逝者如斯,原是不舍昼夜的,而有时,时间竟也可以静止不动,四十年如一瞬,动与不动间,无情总一般,这样的感悟不是来自唱词唱腔身段做表,竟来自「视觉意象、画面处理」,这是《徽》剧的创意,这不是戏曲的手段,这是现代剧场的技法。
谁想从《女驸马》听正宗黄梅唱腔
这样的观赏经验竟与香港导演的现代戏剧《张爱玲,请留言》有些类似。戏演到最后,多层透明景片布满舞台,一抹如烟似雾的浮云缓缓流荡,张爱玲脸庞的图像以拼贴的方式交替出现,在奔腾逝水的多媒体影片穿插中若隐若现,这张脸永远凑不齐对不上,人生多少失落?多少偶然?多少擦身而过?几许沧桑陡上心头。此刻,语言退位、情节不再,导演运用的是光影和色泽构成的「意象」。《徽州女人》不也是如此吗?画面取代语言、意象营造氛围,这是现代剧场的处理手段,《徽》剧因此而能触动现代人的心灵,而能与现代接轨。
或许我对黄梅戏不内行吧,所以只「看见构图」,没「听见唱腔」;可是,这个年代对黄梅戏内行的又有几人?尤其是在台湾。戏曲要面对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新观众,新观众看电影电视、玩电脑电动,却未必有戏曲历史的积淀,要「戳弄」他们的心灵首先要抓准「情绪」,而手段呢,可能要利用一些「非戏曲专业」的元素。果然,不久之后,当韩再芬顶著「徽州女人」的光环带来黄梅戏经典代表作《女驸马》时,观众就没有丝毫兴趣,没什么人想听正宗黄梅唱腔,这跟韩再芬唱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只是《女驸马》的故事显然和现代人的情思有距离。
这使我想到去年的「两岸戏曲大展」,这一系列重要地方戏的展演非常有意义,可是剧场效果却值得思考。就以打头阵的秦腔来说,秦腔在中国戏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许多剧种(尤其是梆子腔系)的原始源头,地域特性非常鲜明,足以与古书燕赵之声的记载相互印证。引介秦腔来台,当然是一重要举措,所有的宣传焦点也都集中在剧种的重要性、历史意义与剧种的特色——尤其是「绝活特技」之上。不过,如果主办单位希望这次的观众群能在「乡亲」和「戏曲研究生」之外另辟票源,所选的戏就必须在剧种的重要性与特色之外,更具有深刻动人足以引起共鸣的情感力度。
太学术专业的「两岸戏曲大展」
可是以个人看来,整个系列的设计都太「学术专业」、太戏曲「局内观」了,强调的尽是剧种的价值、剧种的特色,可是,剧场不是教室,观众不是学生,观众进剧场要寻求的不是戏曲知识,而是情感宣泄,而秦腔那许多戏,却显然技巧掩盖了情感的本质。像是重点剧目〈鬼怨‧杀生〉,只看到一再重复的「喷火」绝活,却无法让人感受到李慧娘对裴舜卿一心呵护的浓烈情意。我曾看过许多其他剧种的李慧娘,也有喷火(技巧不逊色,只是次数较少,只是穿插,不是重点),而全剧在唱念做打的均衡表现之下,体现出的是李慧娘的恳切情意,因此我心目中的李慧娘一直是一曲动人的诗篇,而秦腔这般「喷火复仇女神」的形貌,却使我对这出戏和这个剧种的印象停留在技术的层次,完全无法走进心崁里。
另一出《朱痕记‧放饭》里朱春登正在妻子灵前痛哭悼念时,却惊觉席棚外的讨饭婆可能正是其妻,此时演员用了「耍纱帽翅」的技巧,表现内心的疑惑犹豫思索。这套技巧要用颈部力量,难度很高,最初在蒲州梆子〈杀驿〉里大放异彩,很多剧种很多戏都用过,成为一套戏曲手段,可是〈放饭〉里面的使用,却让人觉得过于炫奇。以现在观众的审美需求来说,有时越贴近生活越感人,高度程式化、规范化、技巧化的动作,对于情感的抒发表达,不见得处处合适。
「两岸戏曲大展」最后一档是湘剧,共演出四场,两出古典名作(《白兔记》、《拜月记》),两出得奖名剧(《生死牌》、《马陵道》),但只有《白兔记》一枝独秀。
「感动」是剧场里唯一的情绪
不过《白兔记》的成功绝对不是文宣上说的「湘剧的存古性、宋元南戏的遗留」,而是当代剧作家改编的成功。当代优秀剧作家对于每一个人物的内心都有深入的刻划,尤其是岳氏夫人。岳夫人是刘知远投军之后另娶的妻子,丈夫在沙场征战,岳夫人在家中担忧不已,终朝每日盼望丈夫归来,而盼来盼去,竟盼到了丈夫与前妻生下的小婴儿,被老仆人送来给她抚养。乍闻丈夫有原配的当头,她当然不想接下这婴儿,然而,婴儿的啼哭勾起了女性特有的母爱,「是喜?是忧?是拒?是收?」犹豫挣扎之际,看到婴儿依偎在老仆人怀中,「老背小、小倚老,烟硝万里,飞度关山」这样的情景打动了她,终于接过了孩子,在「我就是妳的亲娘」唱腔里,婴儿在夫人怀中止住了啼哭。当灯光凝聚在岳夫人怀抱婴儿摇哄入睡的场面时,泪水满溢在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所有人的眼中,此刻,管他什么宋元南戏、剧种特质,「感动」是剧场里唯一的情绪,古典与现代,接轨在情绪里。
其实演员倒不见得怎么出色,尤其女主角李三娘,演唱功力显然生涩,但动人的剧本使她不费力地和现代观众取得共鸣;反之,该团资深一级演员左大玢在《拜月记》里展现了坚实的唱功,却因剧本太陈旧、人物太刻板而「白唱了」。当戏曲已失去流行地位时,当代的观众进入剧场绝对不只是为欣赏演员的唱念做打——能分辨得出唱腔韵味醇厚与否的观众能有几人?大部分的观众根本不管今天看的是什么地方戏(尤其在台湾,所有的方言反正都听不懂),只想要看「能触动情绪」的戏。叙事技法可以尽量多元,无论是京是昆是大戏是小戏是传统是现代是电影还是动画,只要不相互扞格,只要能动人,观众绝对欢迎。
《徽州女人》不正是如此吗?虽然剧本有明显的不足,但导演的确抓住了观众,这一点就足以为地方戏在当代的处境指点一条途径。很多观众哭著出场以后只记得曾有一个女子这样活了一生,不太记得黄梅戏,不会想在这里寻求什么剧种特色,更不会期待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徽州女人》和黄梅戏的关联在哪里呢?应该只在「通俗的唱词、旋律以及生活化的身段作表」,而这些剧种特色已潜在融化转换为整出戏的基调内蕴,不必强调不必外显,女人岂止在徽州?西递村不是一个特定的所在,它的意义是普遍性的,是中国古代封闭村镇的代表,《徽州女人》岂能为地域特性所局限?运用多元技法触动现代人心灵,剧种特色「内化」为美学基调,这或许是地方戏和现代接轨的一条途径吧?
文字|王安祈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按:
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山西《中华戏曲》21辑转载,相关论述参见王安祈《当代戏曲》(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