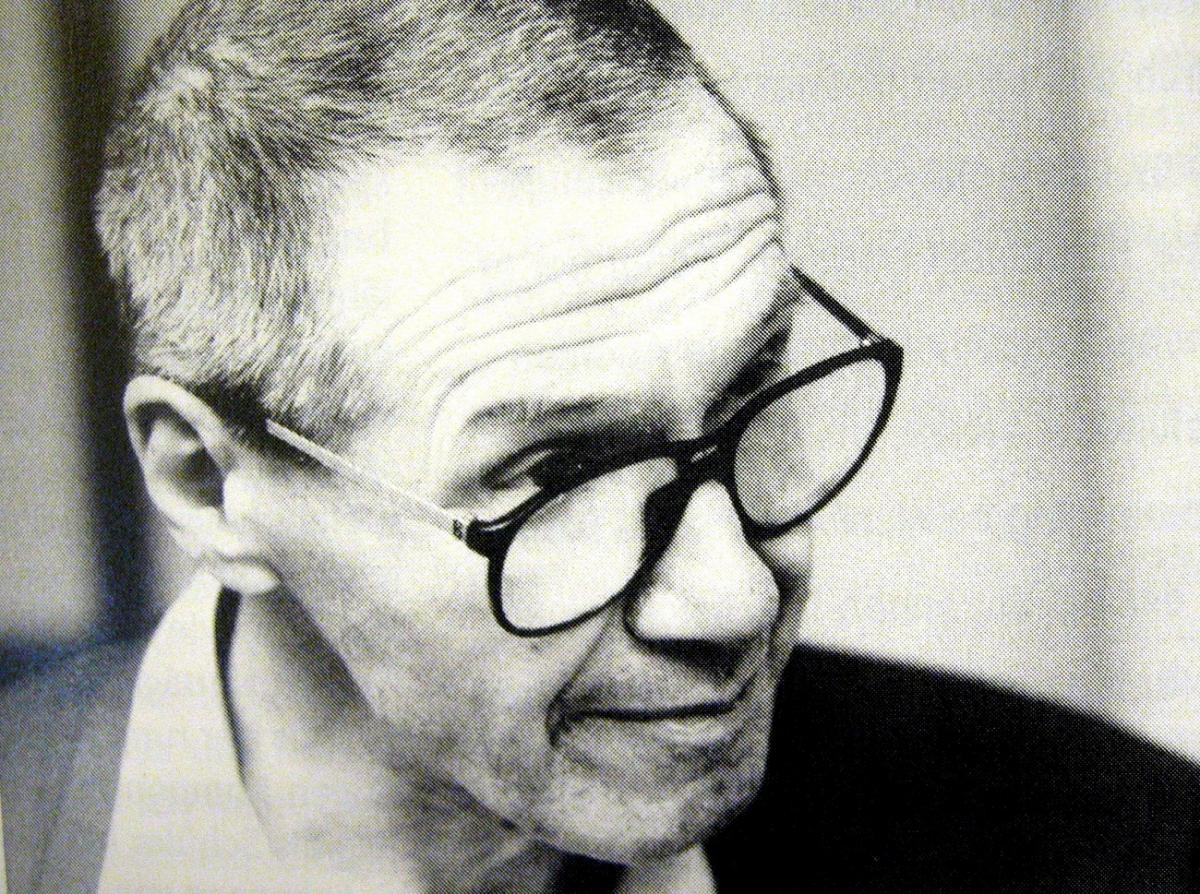面对大批要从情节、剧场视觉氛围来接受感动的新观众,新编戏的编法体现了新的美学,但《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却让编剧、导演隐身于后,让我们重新看到「演员」在「编、导」的保障巩固之下如何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线的位置,演员绝对不是编导手下的棋子。
前阵子听「豫剧天后」王海玲私下说起:「我最怕被问这出戏的人物是如何塑造的!我实在说不上来,还不就是『练』吗,不断的练反复的练,唱著唱著韵味神情就都出来了。」她嗫嚅地说著,有点不好意思,我却觉得非常有趣。
这套「理论」并不是我第一回听见,前几年在香港见到河北梆子国宝裴艳玲,她更直率,会议当场被问到如何塑造人物时,大辣辣地说:「塑造什么塑造?『拉山膀』胳膊抬得位置准确就是有人物,偏了低了就是没人物!分析什么?回去练功!」
老戏以特定的人象喻普遍的人生情境
台湾四大须生之一周正荣先生生前接受访谈时,听我转述裴艳玲的话,非常高兴地笑著说:「内行话!」接著周先生很详细地举例说明「老派」的人物揣摩法:
我们是不讲究什么「人物分析、性格塑造」的,没那么多说头,还不就是不断念不断唱,有时连戏词都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念著念著就能体会出感情了。光是「分析」绝对不够,纸上谈兵而已,分析出了情绪还得用自己念白的抑扬顿挫表现出来啊,如果念得不确实,什么都白搭。譬如说吧,分析出了人物要庄重,也不是绷著脸做出一副目不转睛的样子就真的法相庄严了,台上要「眼神」哪,台步一走,要是脚底下功夫不够,浑身的衣饰、袍角、腰带都跟著乱晃动,庄严立刻就破功!像《搜孤救孤》吧,程婴劝妻子舍亲生子的心情我也能分析出一大篇,可是「性、听、命、冥」几个字唱起来音「送不远、发不亮」还谈什么呢?
像我这么喜欢《鼎盛春秋》(全本伍子胥),可是我就怕人家问:「请问您是如何塑造伍子胥这个人物的?」我还真怕,不是骗人的!为什么呢?传统老戏的剧本并不很「严实」,很多地方松散、拖沓、重复,不过我要说的不是结构不紧凑,所谓「不严实」主要指的是剧中的感情。戏里的情绪通常很「宽广」,不一定完全扣紧住剧情,经常是以主要剧情为核心而松松宽宽地向四周蔓延,有些情绪是「溢」出于剧情之外的,这些地方看起来像是「多余的枝蔓」,其实却可以触发更多更宽的人生感悟。譬如我唱《鼎盛春秋》的〈文昭关〉时,我心里想著的未必是「伍子胥这一个人」(特定的个人),我想的是「遭遇人生大难的人」,是普遍的人生情境,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处境,也就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反应。我尽可能地唱出「危急困窘」的情绪,可是我未必完完全全想著伍子胥。我唱戏的享受就在唱出一股人生况味,希望我的唱有抚慰、宣泄的作用,至于是不是只限于伍子胥,我并不那么在意,因为剧本本身也就不著重在描写他所遭遇的具体事迹,只是藉大段唱让他抒发情感而已。(注)
新编戏的编法体现严实的新美学
几位艺术家真切地说出了老戏的特质,这不只是演员揣摩人物的特质,更是剧本编写的特质。不过新编戏就不可能这样处里了。新编戏通常都严严实实,逻辑脉络一丁点儿都不能错,演的是实实在在的剧中人,不再是以一个特定的人象喻整个人生情境。就拿红楼戏《葬花》来说吧,民国初年梅兰芳演黛玉时,重心就在出场的「西皮倒板」、「慢板」,葬花时的「二六」和后面听曲时的「反二黄」,没有什么情节事件,甚至身段也不多,就从唱腔音乐里传递一股飘零的意态。文献里记载当时一位观众说,他每听葬花,心情就要郁闷好几个月,一股说不出的抑郁压在心头,久久不得纾解。这股动人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剧本的情节(根本没有情节可言),而是演员的唱工。所以梅派《葬花》一直是名贵的,唱不出这股神韵的演员通常不敢动此戏。不过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是京剧以流行音乐身分通行全国的时代,到了近几十年,京剧音乐明显地退流行,观众根本分辨不出韵味了,进入剧场也不为听唱;面对大批要从情节、剧场视觉氛围来接受感动的新观众,新编戏的编法体现了新的美学。
新编戏的性格塑造是从「人物面对事件的反应思考抉择」中呈现,不能再以大段内心独唱「自剖心境」了;抒情唱腔的分量不能多过叙事唱腔,「点线结构」(线是情节推演、点是抒情重点,传统戏藉唱抒情时情节往往停滞不前)的传统特质也渐次打破,「严严实实、逻辑分明、曲折变换的情节」是新编戏的根本,由「冲突、悬疑、逆转、发现」所营造的必须是「情节高潮」而不是传统戏唱腔所传递的「情感高潮」,所有情绪的抒发都包融在情节转折中,不可能单独抽离表现。仍以「葬花」为例吧,「葬花」绝对是纯粹抒情的段落,但是笔者在一九九○年新编《红楼梦》时,就不敢把「葬花」当作单独的抒情重点,而是把它放在连串的情节中包裹处理,即:以透纱天幕分割前后两层舞台,黛玉(魏海敏饰)在纱幕后以慢动作葬花,宝钗(朱传敏饰)以正常速度在前面正场扑蝶,而后交错王熙凤和贾蓉的不轨情事,再以宝钗的嫁祸接回黛玉葬花唱段。程序如此复杂,戏才不觉单调。一九九一年马兰主演、余秋雨艺术指导、陈西汀编剧的黄梅戏《红楼梦》也没敢把「葬花」放大成抒情重点,简单数句淡扫轻描,随即转入「敲门不开就踢、就砸」,作为和最后宝玉哭灵时捶打棺木「重拍门板都不应」相呼应的情节伏笔。
王熙凤的戏剧性恰好对上新编戏的特质
不过,以宝玉、黛玉为主的红楼戏,无论如何都还很在意维持《红楼梦》的「诗意」,免不了用大段留白、抽离的唱,表现「由情悟道」的过程。王熙凤却不同,这位戏剧性强得不得了的人物,恰恰对上了新编戏「以情节高潮取代情感高潮」的美学。逼死尤二姐一段原书的故事就就足以布局成戏,编剧红楼老作手陈西汀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一剧最突出的表现在语言,韵文唱词写得机锋锐利,看似明白如话,其实却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孕育而出的,而这是戏剧的语言,不是学者作诗填词,节奏感十足,戏剧感十足。凭借著这样的语言功力,一个个鲜明的人物活脱脱地跃上了舞台,其中「秋桐」的人物塑造甚至强过原书。
对于王熙凤,编剧并没有用「表面化的女性主义」为她加一些空虚寂寞的感叹——这些在京剧里其实是很好加的,「点线结构、自剖心境」都是现成可用的理论,可是陈西汀老先生没有这么做,倒不全为著戏剧结构的严实,而是从人物谈人物,大闹宁国府的王熙凤机关算尽胜券稳操,忙著出招攻击的人哪里来得及寂寞?整出戏饱满到了极点,「苍凉」是从满座笑声的背后悄悄透露的:旧社会一夫多妻制度下强悍如王熙凤都只能以吃醋为手段确保家族中的地位,女性的悲哀何须多言?
这出戏于一九八二年在香港首演之后,主演者国宝级艺术家童芷苓即转往美国定居,一九九○年来台演了一场,不久即过世。如此精采好戏岂容戏随人亡?国光剧团即将由魏海敏主演王熙凤,王海玲客串老祖宗贾母,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重现舞台。剧团排练此戏的过程刻意「反现代」:先直接练唱练念白,表演熟了之后再请红学专家来作人物分析,演员再从细节上调整。魏海敏这十几年来潜心学梅,功夫下足了之后,这回从梅派剧目中翻腾而出担纲新戏,梅派的「大方、派头、贵气」内化在举手投足一身气韵之中,而「京白」与「演技」不仅是荀派的、童芷苓的,更是王熙凤的,魏海敏将以较她在「当代传奇」饰演马克白夫人时代更为成熟的姿态,施展覆雨翻云的伎俩手段。这次演出,不仅是这位杰出演员心防的突破,更是艺术层次的跃升,同时更可以让观众重新看到「演员」在「编、导」的保障巩固之下如何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线的位置。
演员在编、导保障下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线
二十年前海峡两岸都有很多精采的新编戏,当时展现的是编剧的新技法,而近十年来导演的手法越来越多,随著科技的进步,剧场的「玩法」也越来越让人目不暇给。在这样的趋势下,产生了很多好戏,然而,每当夜阑人静独自静听老唱片时,却不自觉的兴起一份「惭愧」的感觉,当视觉氛围快要取代演员表演的时刻,戏曲的本质在哪里?导演精心构设的Pose画面经常与戏曲身段无关,演员的唱腔韵味更无足轻重,那么,几十年练功为的是什么?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或许是我们徘徊在「传统、现代」甚至「编剧、导演」的时刻可以提供思考的一个实例吧。《王》剧希望清楚纯净地呈现剧本和演员,导演则隐身在后,不企图以视觉效果取代文本价值,「看不见的导演」应该是最优秀的导演吧?至少对戏曲而言。其实这出戏的编剧也隐身在后,大量精采的唱词念白不是编剧文辞的展现,而是提供演员充分发挥的机会,剧本保障了品质,却把演员推在第一线,演员绝对不是编导手下的棋子——不用任何手法掩盖表演的本质,这是深切体会戏曲特质的编剧所做的处理。
注: 王安祈《寂寞沙洲冷——周正荣京剧艺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编印中。
文字|王安祈 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教授
吃醋,秀出了什么?
谈「王熙凤」的戏弄与假扮
康来新(中央大学红楼研究室主持人)
吃醋无疑是王熙凤的招牌戏码,首先,量就惊人,再来就是不断工研,每多创发,与尤二交锋,尤其浑身解数,特别是假扮贤良,秀出了《红楼梦》「假作真的真亦假」的吊诡曲折,称得上是独家绝活。
吃醋,嗅出了什么?除了「酸」以外。
吃醋,秀出了什么?除了「妒」以外。
王熙凤吃醋的力道演出并非个案
因为吃醋,王熙凤不惜教唆诉讼、伪造官司,使青天所在的都察院黑幕重重、无中生有、暗盘交易、以假为真,刺鼻可闻,自是婚姻危机下的强酸四溢。此外,嗅觉可感的还有:司法病变的「腐」味外泄。是的,恶质的金权,势力太壮大,弱质的正义只好被戏耍、被玩弄。
司法病变,那么立法健康吗?健康的精/卵结合本是受孕、怀胎、传宗、接代的首要,然而,以前的医学不这么认为。孕或不孕,有子或无子,责任全在女方。所以,相对而言,婚姻之法较保全于男、较欠缺于女。自《礼记》始,在一男多女的设计下,便明令前者可以主导后者的「七出」之条,其中「无子」与「妒嫉」常互为因果。所谓「妒」,乃特指为人妻者对丈夫纳妾权的侵犯,而妾之所以可纳,是为了宗法家族的繁衍扩大,「妒」则妨之害之,故有罪于夫家,妻因妒被夫扫地出门,具有百分百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换言之,立法和司法差不多,腐矣、病矣。正是这不健不全的结构,加速恶化了有瑕有疵的人性,乃至「妒」的人口激增,「吃醋」形成的队伍,每多形象鲜明的力道演出,《王熙凤》并非个案。
〈跪池〉的柳氏值得另眼相看
在戏曲的表演艺术中,昆曲的〈絮阁〉、〈跪池〉堪称吃醋档案的代表作。《长生殿》里,环「肥」的杨贵妃排挤梅「瘦」的江采苹,不仅是权力的较劲,所涉造型两极的审美之争,也每每成为醋事妒史的不可或缺。至于罚跪花心丈夫的柳氏,更是「妒」之所以为「醋」的由来。苏轼取笑好友陈慥好佛,只可惜狮吼力度的如来正音听不到,时时灌耳的却是柳姓妻子高分贝的妒悍训骂。于是,柳女妒声与陈慥好佛与狮吼佛音,诞生了「河东狮吼」的典故(「河东柳」是不忘本的「姓」表述,就像「陇西李」、「鲁国曾」)。又据说狮子嗜酸,每天必喝酸奶、酸醋各一瓶,于是,妒妇与狮子,狮子与嗜酸,又诞生了妒妇吃醋的说法。
其实,狮子吼功未必是柳氏吃醋的称道处,相较于女吃女的妒妇行径,如吕后之于戚夫人,潘金莲之于李瓶儿……,例子不胜数,柳氏直接挑战第一性,颇有捋虎须、批龙麟,与父权怪兽相搏的匹妇之勇,值得另眼相看、别有评价。
从《金瓶梅》的西门庆到王熙凤
王熙凤无疑是舞台型的人物,麦克风听她的,聚光灯看她的,她呢,台词轮转,走位自如;或搞笑或催泪或爆料,样样精到;要喜要悲要闹,都难不倒这位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吃醋无疑是王熙凤的招牌戏码,首先,量就惊人,贾琏恨不得打烂这「醋罐」,小厮兴儿更以「醋缸醋坛」喻之,以别于一般容度的「醋瓮」。其次,浓度足以致命;再来就是不断工研,每多创发,与尤二交锋,尤其浑身解数,较之于多姑娘、鲍二家的前例,且精进多矣;特别是假扮贤良,秀出了《红楼梦》「假作真的真亦假」的吊诡曲折,称得上是独家绝活。
小说《红楼梦》结晶了诗歌文学的「抒情」唯美,入叙事传统的「世情」微肖,当搬上舞台,梅派〈葬花〉属于前者,里程碑的越剧《红楼梦》也偏爱抒情国度的宝、黛,戏剧张力则在于「世情」介入的掉包之计,凤姐的关键作用大矣哉。
剧场毕竟不同于书斋,「期待」不同,「接受」有异,所以「抒情」会淡出,「世情」能当道。《红楼梦》中「金瓶」属性的人与事,往往一演再演,二尤与凤姐最足说明。王国维视《红楼梦》悲剧为欲望美学的演绎,而人欲与天理的辩证,《金瓶梅》可谓淋漓尽致矣,欲望城国的天王是西门庆,到了《红楼梦》,则变性为天后王熙凤,她担纲了世态、人情、金钱、权势、风月,好戏连连,比三纲五常下的女范好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