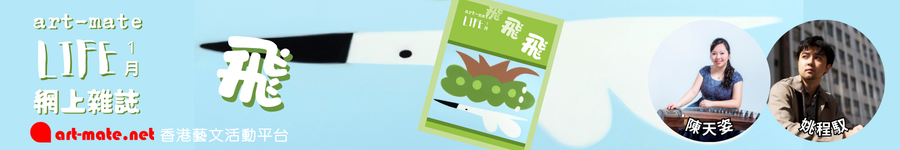在这部有如展示人类史诗的表演内,看到人类的诞生、成长、个体逐渐形成群体、出现象征文明形成的陶瓮、如箭雨落下的麦田收割、到太空人在广袤浩瀚的宇宙探勘、地球化作被肩负在人类肩膀上的球体可供嬉戏把玩,「伟大驯服者」这样的标题用来指涉人类如何成为天地万物、包含宇宙天体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驯服者,但是如影随行仍是暗黑的底蕴——死亡,这是人类所无法驯服的对象。
迪米特里.帕派约安努《伟大驯服者》
11/16~19 台北 国家戏剧院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在其《安蒂冈妮》Antigone一剧中,借由歌队来歌颂人类已能在汹涛巨浪的大海、峰谷崎岖的大地中,学习驾船和耕犁的技术,并能渔猎捕获、驯服圈养山林野兽,成为万物之灵。人类已从原初对大自然力量的崇敬与畏惧,逐渐掌握对于人类知识的追求与肯定,并以语言与思考去建立起礼仪与法制的城邦,但是即便面对未来不再怖怕,仍无法摆脱死亡对于生命的局限,医术再怎样高明,也无法克服死亡的终止。
以此「人类颂」来切入观看希腊导演迪米特里.帕派约安努(Dimitris Papaioannou)的《伟大驯服者》再贴切不过。不仅在这部有如展示人类史诗的表演内,看到人类的诞生、成长、个体逐渐形成群体、出现象征文明形成的陶瓮、如箭雨落下的麦田收割、到太空人在广袤浩瀚的宇宙探勘、地球化作被肩负在人类肩膀上的球体可供嬉戏把玩,「伟大驯服者」这样的标题用来指涉人类如何成为天地万物、包含宇宙天体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驯服者,但是如影随行仍是暗黑的底蕴——死亡,这是人类所无法驯服的对象。
打破寻常认知 相信幻觉为真实
死亡从表演的一开头,即大剌剌地展示给观众观看。一位男表演者脱下自身的衣服,模拟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画作《哀悼死去的基督》Cristo de Mantegna耶稣死去模样,全裸躺在夹板上,由另一人替他盖上裹尸布,另一人却用夹板掉落的风力,将裹尸布飞扬起来。如此不断重复一人盖上、一人让其扬起成为行动的动机(motif),亦是所指(signified)此表演的主题(theme):日复一日,人类日积月累所做的最终事情,不就是在面对死亡,遮蔽死亡,展现死亡。
而帕派约安努所运用如同希腊悲剧「迟著手点」(late point of attack)的形式,让观众先看到人类结局的终点,再回溯整个历程;但此同时导演是以拼贴的手法与内容,并未照著线性的故事时间轴,反倒是运用一个接续一个的舞台画面,奇观式像是马戏表演,展示身体延伸、切割、分离、拼凑、交缠的可能性,让观众一边赞叹人体可以突破的极限与延展的无限,另一边则进入帕派约安努在演后座谈所述,可以把整场表演视为一场「可笑的丧礼」(funny funeral),如同表演者谐谑(parody)林布兰(Rembrandt)画作《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Lección de anatimia的场景,下一刻立即将人体解剖下来的肠子、肉骨变成飨宴上的盘中飧,这里又更接近波希(Bosch)画作所呈现尘世乐园人物狂欢怪诞的场面。
荒诞与哀伤、轻盈与沉重、嬉闹与暴力等等,往往是在《伟大驯服者》展示过程中,所带给观者交错重叠的感受。一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用的疏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一再打破舞台的幻觉,提醒观众这一切都是戏,而非真实。帕派约安努亦是一再让观众看到舞台上表演者如何完成画面的过程,像日本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的变形合成,表演者有时像日本文乐的操偶师,去摆弄其他人的肢体,或集合众人去完成一个人体拼贴的组合(一位女表演者的上半身,去凑合两位男表演者各自一支腿),但表演者不会以黑布遮盖住自己的面孔。因此,帕派约安努在此的揭露,并非将观者的情绪疏远到一个距离,反而是一种邀约,邀请观众去进入到如此的幻觉想像里,如同造梦一样,去相信这样的幻觉(to believe illusion)是真实的。
欲达成如此魔幻的感受,便须打破已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框架,亦如全剧所用的音乐为小约翰.史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蓝色多瑙河》,但导演将其扭曲、延迟、分裂,使得这样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曲,听得出暗藏于音符背后的欲念与不一样的杂讯,如此解构、建构、再造,除原有的联结指涉不变外,又产生了新的诠释。《蓝色多瑙河》的音乐还可以联结到,使用同一曲子作为电影配乐的库伯利克(Stanley Kubrick)《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伟大驯服者》主旨贯穿古今、跨越地球与太空,有著异曲同工之妙。美术背景出身的帕派约安努,在《伟大驯服者》谐谑许多西洋的名画,同时观众还看到电影影像的再诠释,除《2001太空漫游》外,表演者跳上地球球体上嬉闹玩乐,也不免连想起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将地球仪像气球一样抛上抛下、互动舞蹈的经典画面。然而帕派约安努绝非落于表面的言诠(literally),这些素材都内化转变成舞台画面的底蕴,最厚实的底层仍是导演出生于希腊的文化与涵养。
广袤而幽微 体现人类的景况
愈是动态的身体与动作,愈是如雕塑般静止而宁静——此为帕派约安努最擅于呈现的舞台画面。他喜欢展示非完整而残缺的躯体,可回溯希腊出土文物的雕像,亦是断臂残肢、或无头无足。这样残缺的展现,却更突显出人类身体的美感,从完美无缺的框框内破茧而出。舞台上一位全身裹石膏的年轻人僵直无法动弹,另一人协助他一一粉碎掉身上每一部位的固著,让他可以自由自在、伸展四肢,背起自我的行囊去旅行。如此离开表面看似舒适圈(comfort zone)实则是规驯的豢养,踏上冒险犯难的旅程,其实是「认识自己」(know thyself)的过程。
从舞台上年轻旅人的形象,联结伊底帕斯(Oedipus)为逃避弑父娶母的神谕,离开科林斯生养他的所在展开的行旅,却一步步走向命运的安排,到导演此次作品的发想——一名廿岁年轻男子在雅典失踪的新闻事件,最后被发现时只是一具尸体。帕派约安努在舞台上展现尸体骨骸的画面,又像是考古学家从时间历史冲积所堆叠而成的文化层遗址(亦如舞台设计为四处散落积累如厚土的板块),所挖掘出土的人类遗骸。《伟大驯服者》的联结亦是人类自诞生到死亡,从地球上沧海一粟、拔擢升高到化为宇宙行星的微尘,如此广袤而幽微地体现人类的景况,最后画面聚焦于摆放于一本开展扉页大书上的骷髅头。「死亡」的意旨也再次地被点题出来。
这亦是西洋绘画传统经常会出现的主题(注):骷髅头所象征代表「死亡」,时时提醒人类即使知识与技艺再如何高明超越,亦无法摆脱终须一死的命运。但死亡是要「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帕派约安努最后以一个表演者不间断地抵拒著地心引力的影响,鼓气吹起一片在空中飘浮的锡箔纸片,不让其掉落在地面上。
所给予的答案遗留于缄默中,直至灯暗。
注:可参照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画作《大使》The Ambassad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