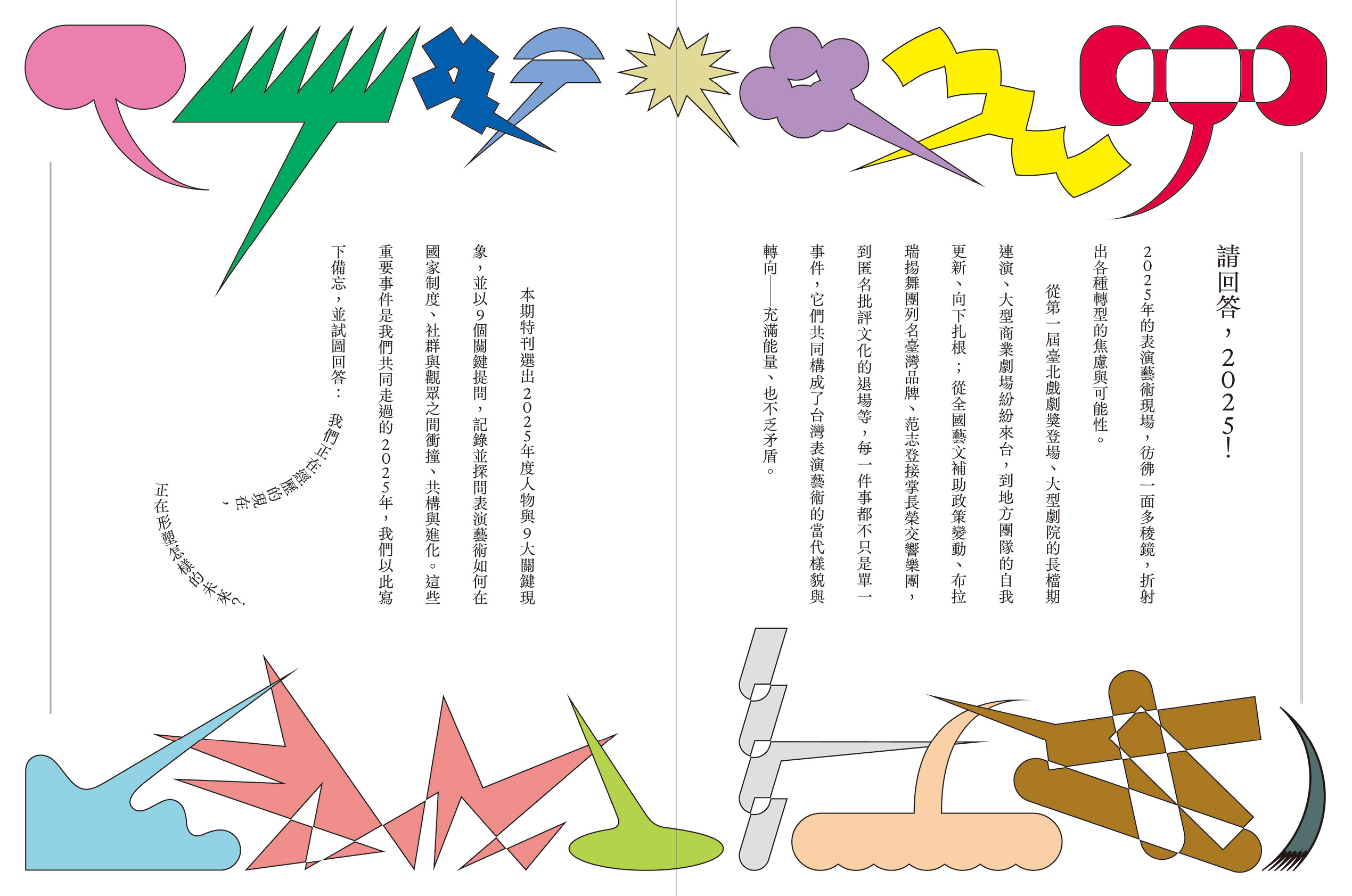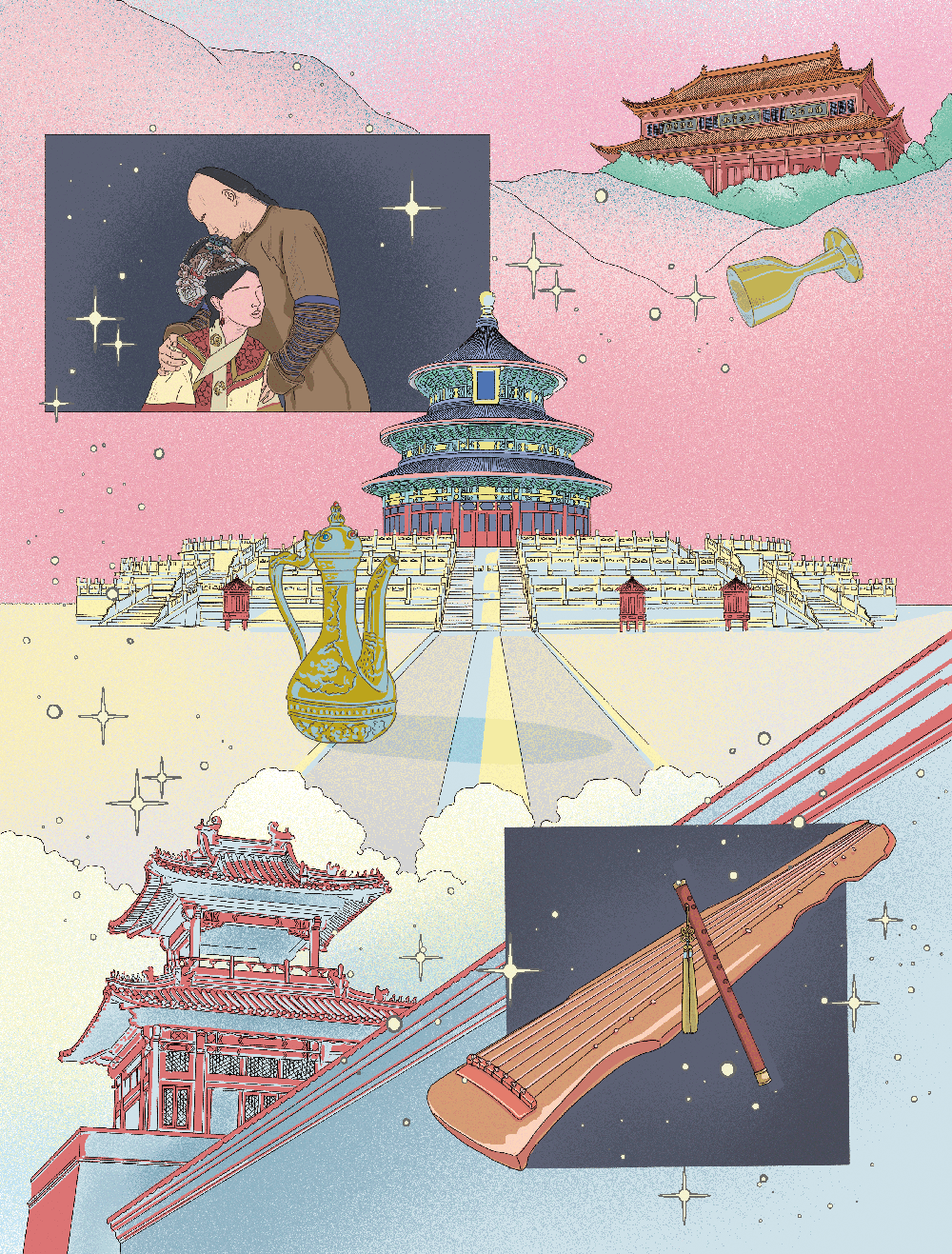從沒有禿子也沒有女高音的《禿頭女高音》開始,伊歐涅斯柯的戲劇創作始終擺盪在寫實與奇想、悲劇與喜劇、戲劇與反戲劇之間,在現代劇場裡創造不滅的火花。
伊歐涅斯柯生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羅馬尼亞,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逝於巴黎。父親是律師,母親是法國人,他一歲那年舉家遷往法國,十三歲之後回到當時已被法西斯主義蔓燒的羅馬尼亞,直至二十六歲(即1938年)才離開定居法國。伊氏對巴黎的第一印象,記憶最深刻的是「人們匆匆而過,如幻魅鬼影般……當想起他們均已作古,而每樣事物也幻化成影,一股令人暈眩的焦慮感便攫我而去。」(註①)他曾淸楚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在盧森堡公園看到英國著名的傀儡戲Punch and Judy,只覺劇中的對話及動作儼然替全世界代言,簡直比眞實還要眞;沒錯他們的確卡通化了般,但卻點出詭異又直截的眞理(註②)。當他十三歲回到羅馬尼亞時,馬上便能感受一個充滿「虛無、暴力、空浮、憤怒、可怖、令人憤恨」的世界(註③),與他童年在巴黎對人的觀察無異。一九三九年定居巴黎後,伊氏曾在日記中感慨自己的籍籍無名,年輕人想要嶄露頭角的雄心他也是有的。但談到他所心儀的文學形式,雖然自小對戲劇狂愛,但此時的他卻不以爲然了,因爲每回去看戲時,他總覺得有一群自以爲是的演員,在大庭廣衆下扭揑作態,不過只製造牽強的眞實感,但卻嚴重破壞觀衆的想像,著實令他替他們感到很窘。反之,小說則是他的最愛,因爲他覺得小說比較眞實(註④)。
誤唸而成的《禿頭女高音》
伊氏第一部劇作出現的過程極具戲劇性。遲至一九四八年他三十六歲時才開始學英文,過程中赫然發現他們用的英文敎科書裡盡收些陳腐的句子,如一週有七天,地板在下,屋頂在上等。接著課本引進一對夫婦,他們有最典型的英國姓──史密斯,史太太則盡講些他們已經知道的事給她先生聽,例如他們有幾個小孩,住在倫敦近郊,他們叫史密斯,先生是職員,他們的英國女傭叫瑪麗等。然後他們的朋友馬丁夫婦來訪,二對夫婦開始對談,此時的會話則介紹比前述更複雜的英文句子如「鄕村比都市安靜」等。這些陳腐但又荒謬的對話已渾然天成地等著被有心的劇作家寫入劇作中,這便是《禿頭女高音》。
《禿》劇本名爲《無痛學英文》及《英語時間》,在排演時,飾滅火員的演員吃螺絲,將金髮女老師誤唸成禿頭女高音,伊氏正巧在場,福至心靈地便將此劇定名爲《禿頭女高音》。伊氏堅稱此劇須以極度寫實的方式演出,一如易卜生的《海達.蓋伯樂》一般。然伊氏終究稱《禿》劇爲一種「反戲劇」,也就是戲劇的的諧擬,或一齣有關喜劇的喜劇(註⑤)。劇中二對夫婦互相証明他們已知道的事實,這種態度令人聯想到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也是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証明自我、上帝、及天地存在的態勢,顯見伊氏強烈地嘲諷理性邏輯的思維方式。此外,劇中呈現中產階級所使用的語言已如化石般地空洞,而語言裡動輒出現的陳腔濫調及似是而非的眞理,及其背後所代表中產階級價値觀,更是伊氏加以揶揄的對象。人們在操控此類空洞的語言、認同現成的價値標準時,他們已形同機器人,缺乏想像力及獨特性。於是史密斯與馬丁夫婦終將成爲任何一對無個性的中產階級的表徵。
伊氏的這部處女作已淸楚地揭示他日後的寫作技巧及關懷的主題:他洞悉人類語言背後空無的本質。言語溝通的過程本來就多舛且不可測,因此劇裡旣無女高音也無禿子出現。人類平腐的言語裡早已埋藏荒謬及錯誤的成份在內,伊氏自己說:「能感覺到這一點便能超越這種荒誕;而想要超越它,我們要深埋自己於其中。生活裡最低俗的一面才是最充滿驚奇的,最超現實的就存在於我們雙手能掌握的日常對話裡。」(註⑥)
《上課》中語言變成控御工具
對語言本質的探討持續至下一部劇作,伊氏寫於一九五〇年的《上課》The Lesson。劇中語言敎授試著敎學生同一詞彙在不同語言裡的用法,但他無法使學生了解它們的含意。語言在劇中變成控御的工具,因爲他可以獨斷地指派字的意思,所以他對女學生便有掌控權,最後甚至將她姦殺。這種「語言導致犯罪」的體認無疑爲後來英國荒謬劇作家哈洛.品特的風格埋下伏筆。他們先後體認到語言的使用最易流露人與人間所存在的宰制關係,也就是說,語言與權力的密切關係形成最基本的人際關係。即令是看似無大害的師生關係也不免充滿暴力、控御、佔有、及殘酷的成份──這些均是權力的象徵,也難怪劇末敎授手臂纏上了納粹的十字章。確有不少批評家認爲《上課》旨在探討獨裁的本質,特指三〇年代的羅馬尼亞。若說伊氏體驗到一種更宇宙性的暴力充斥於各種人際關係,可能會更接近此劇的眞意。
《椅子》刻劃理性的無力感和人的孤立感
一九五一年夏,伊氏完成其最有名且藝術成就最高的《椅子》。此劇饒富詩意,以抽象的方式製造椅子充斥台上及人群磨肩擦踵的印象,除了挑戰演員演技外,更重要的是,劇中許多意象更成爲荒謬劇場的正字標記。如一對耆老級的夫婦守著孤島上的燈塔;老先生年暮之際想向世人宣布其人生哲學,找來職業演說家替他代打,不料此人又啞又聾,喉嚨裡只能發出一陣嘎嘎亂響;想要在黑板上寫字輔助,卻只出現一堆無意義的字母。這些典型的佈置及安排使我們很容易地聯想到同時代另一位以法文寫作的愛爾蘭籍荒謬劇大師──貝克特。貝克特五〇年代的劇作如《等待果陀》、《終局遊戲》也充斥著怪誕的社會邊緣人,如流浪漢、瞎子、跛脚者。不過不同於《椅子》的演講者,他們均喋喋不休,只是命運與演講者相同,他們說話的內容也是無意義字的組合。可見當時法國文化界確對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失望,劇作家不約而同地以其具象的人物特質刻劃理性的無力感。
有趣的是,伊氏與貝克特均對笛卡爾所揭示樂觀的理性先驗思考模式頗爲反動,《椅子》描寫椅子與人們──即物與他者──氾濫的恐怖,不僅刻劃個人面對外在世界所感受的孤立感,也是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的產物。由於物的不可測,笛卡爾將心的先驗及準確性做爲對付神祕物體世界的利器,典型的笛卡爾式思維者會對物的世界特別敏感甚至畏懼,但笛卡爾終能証明「我思」的崇高,足以抵抗任何來自物界不可靠的資訊。然而伊氏與貝克特卻沒有承襲笛卡爾如此天眞樂觀的結論,而陷於萬劫不復的懷疑論裡,因此他們的劇中不斷傳達角色抵禦外在世界的過程及焦慮,舞台上的《椅子》看不到具象的椅子疊乎其上,但這種隱形、無所不在物的衍生反而製造更多的怖慄感。
此外,《椅子》裡聽與說有障礙的演講者是劇作家拿來反照自己硬要藉劇抒發自我的荒謬情景。藝術家們感受一股強烈的創作慾,但他們所要表達的意念卻頑強抵抗他們唯一賴以使用的語言或文字,這點也正是伊氏與貝克特作品裡的終極關懷。兩位劇作家確有不少共同點,也難怪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椅子》在巴黎首演出師不利,票房一塌塗地,劇評家也不靑睞,但有一批藝術家爲其簽署聲援,其中便包括貝克特。
與劇評家筆戰
一九五三年的《受害於責任的人》Victims of Duty劇情巧的是與貝克特成名小說《三部曲》(1949-51)頭一部十分相似,典型中產階級男主角被一偵探強迫去尋找以前一位房客,奇怪的是他不往外找,反而翻遍他的記憶、甚至潛意識,之後開始一連串的蛻變,最後自己便消失了。偵探爲怕他消失,不斷餵他吃麵包,好堵住他記憶的缺口。最後另一位叫尼古拉斯的人代替偵探繼續餵他麵包,好像在盡某種責任。此劇有後設戲劇的味道,因爲男主角及尼古拉斯在劇中對劇場有明顯的批評及預期,他們認爲現代劇應丟棄可辨及一致的角色刻劃、情節,及人物動機,喜悲劇界限也消弭,可能是伊氏的藉題發揮。
一九五四年巴黎著名的文學出版社Gall-mard替伊氏出版他第一部劇集,內容包括前述三劇外,尙有一部三幕劇《阿鎂第》Amédée(另名《怎樣擺脫它》)及《新房客》(1953年)。此二劇均承襲前述來自氾濫物體所製造的威脅感。從一九四八年的《禿頭女高音》至此第一部劇集出版,時經六年,但伊氏已走向成名之路。一九五六年已負盛名的伊氏頗有樹大招風之難,隔英吉利海峽與倫敦《觀察家》雜誌劇評家泰南打起筆仗,泰南批評伊氏的劇澈底反寫實、反劇場,甚至否定人類語言的溝通。伊氏則答辯批評家總說他的劇只注重形式的新奇,然而他強調尋找最好的表現方式便是他寫劇的原動力,他說:「我在舞台藉用一些道具或物體來外顯角色的焦慮,好讓這些東西都能說話似的,具體呈現害怕、懊悔、疏離等感覺,我也試圖玩弄文字遊戲……如此我等於延伸了劇場的語言……這麼做眞有那麼大不敬嗎?」(註⑦)當時文壇自成二派紛紛加入戰局,這場筆仗更提昇了伊氏的知名度。
貝杭傑貫穿於包括《犀牛》的四部劇作中
一九五七年伊氏完成第二部三幕劇《殺人犯》The Killer。主角貝杭傑是卓別林般的人物(此又與貝克特戲劇、小說中亦喜以此類甘草人物爲主角相映成趣),他來到一看似天堂的城市,但發現居民不是已搬走、就是將自己關在屋內,原來當地有殺人犯出沒。他在當地認識的女友被殺之後,他決定自己去尋凶手,無意中碰到眞凶手,試圖勸他放下屠刀,凶手只是儍笑,貝杭傑想要用槍殺他,但無法下手反而聽任凶手舉起刀子向他殺來。這齣劇呈現主角孤獨的存在和面對死亡的無力感,人們對其自身所處之危境卻像村民般渾然不覺。第二幕有村人大力鼓吹左派的極權主義的一景,是伊氏針對當時法國(更暗指羅馬尼亞)漸漸興起的左派思想的反動,他對布萊希特的政治劇及沙特的左傾思想更大加鞭斥。《殺人犯》融合伊氏慣有詩意表現手法及人的存在、社會政治的探討,所以首演時便博滿堂采。
一九五八年著名的《犀牛》上演了,仍以貝杭傑爲主角,他與女友有天聽說有一兩隻犀牛出現在城內,不久有愈來愈多的犀牛出現了。原來當地居名得了一種會變成犀牛的怪病,最後只剩貝杭傑及女友二人倖免於難,但不多久女友也成了犀牛,只剩貝杭傑獨力對抗這可怕的疾病。這部意象突出的劇很快被解釋爲反映一九三八年伊氏離開羅馬尼亞時的政局,當時他所識的人大量投入法西斯運動,使他眞切感到「當別人與你無法溝通時,你眞的會有面對怪物的感覺──比如犀牛好了,它們結合坦然與殘暴兩種特性,它們會在淸楚自己意識的狀況下殺了你」(註⑧)。廣言之,居民罹患會變成犀牛的病可解釋爲不管左派或右派的集權象徵、及會讓個人失去其獨特性的合群要求。《犀牛》不僅強調這種合群要求的荒謬,也同時傳達抵抗這種合群壓力的無力感,最後它甚至也一樣荒謬。所以《犀牛》也嘲諷個人主義英雄式對抗群體暴權所堅持的優越感,由於劇中這種模稜兩可的特性,使它免於淪爲粗淺的反共宣傳品,而能深入探討人類的存在根本糾葛不淸的荒謬處境,因此表演貝杭傑的演員、導戲的導演必須要能呈現這層曖昧的感覺,才算成功地傳達伊氏的原意。
名爲貝杭傑的角色又出現在以下二部劇中,分爲《國王將死》(1962年)及《空中漫步》(1963年)。前者描寫國王貝杭傑待死的過程,伊氏一向以公開批評羅馬尼亞的共產暴君西奧塞古聞名,此劇無異是他向奧君下的死刑帖。後者與《禿頭女高音》相呼應,也以英國爲背景,貝杭傑有飛上空中的能力,最後他重回人間傳述有關地獄的消息。一九六六年的《飢渴》則得到法國國家劇院的支助,使伊氏正式地受到法國文壇的認可。但此劇一般評價均不高,長得像貝杭傑的主角目睹二個被關在牢籠的人受刑的經過,他們明顯地代表二種生活型態,其一名爲Brechtoll,顯而易見地,伊氏又在針對布萊希特開砲了。
七〇年代的劇有《劊子手來了》(1970)、《馬克別》(爲莎劇的諧擬,1972年)、《一團亂》(1973年)及《拿袋子的人》(1975年)等。一九七一年伊氏獲頒法國國家硏究院院士頭銜,可說是這位出生於羅馬尼亞的作家,終於百分之百地受到法國文壇的肯定。
不滅的火花
綜觀伊氏全部作品,可發現共同的主題,屬於比較形而上討論的是個人由於無法與別人溝通所產生的孤寂感,個體一面受制於外在社會要求與群體認同的壓力,一面則受他本身性慾、罪惡感及面對死亡與不確定的自主性時產生的焦慮所箝制。觸及社會層面的主題則是批評當今中產階級文化缺乏眞正的價値觀及精神內涵。在探討這些主題時,伊氏採用幻想、非寫實、詩意的表現方式來傳達藏於人類理性語言背後、令人震懾且神祕的眞啓。他說「事情的眞理只能靠奇想來傳達,它比所有的寫實主義更寫實」(註⑨)。語言由於它制式及仿理性的錯覺,根本不能傳達生命經驗裡令人感觸深刻的部分,伊氏的戲劇則希望引起一種十分直接,甚至很具體的生理反應,就好像傀儡戲裡Punch痛打警察、馬戲團小丑從椅子摔下來、默片裡喜劇演員互相往對方臉上扔蛋糕的那種活生生的感官刺激。這種崇尙表達生存眞相的詩意手法,的確使伊氏的劇遠離受限於語言、概念才能表達的寫實主義,而趨向「反戲劇」的美學,無怪乎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伊氏訪台時,他的詩意劇《椅子》在中國傳統京劇的抽象表現手法中找到相對應的表現形式。
一九五八年七月號法國《壯觀》雜誌刊出伊氏寫給文友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數年前的作品《椅子》,及其如何處理生命裡荒謬的本質:「努力地去征服人生命情境的荒謬便等於宣稱反荒謬的可能……就像禪宗從不直接敎我們什麼道理,而是不斷地指引我們找到一種眞啓、啓示一樣。如果硬要我放棄表達悲觀的想法的話,我覺得這才是最悲觀的表現。沮喪的背後其實就隱含著每一個人想要從中解脫的訊息。」(註⑩)這一段話把他的作品與東方哲學相提並論,其實可說是其劇作的最佳註脚──他的戲劇永遠擺盪在寫實與奇想、悲劇與喜劇、戲劇與反戲劇之間,在現代劇場裡創造出不滅的火花。
註:
① Eugène Ionesco,〝Lorsque j'écris...,〞Cahiers des saisons, no. 15, Winter 1959.
②Ionesco,〝Expérience du théâtre,〞Nouvells Revue Française, Paris, 1 Feb. 1958.p.253.
③Ionesco,〝Lorsque j'ecris...〞
④Ionesco,〝Expérience du théâtre.〞
⑤Nicolas Bataille,〝La bataille de La Cantratrice,〞Cahiers des saisons, no. 15, Win-ter 1959.
⑥Ionesco,〝Le point du départ,〞Cahiers des saisons, no. l, Aug. 1955.
⑦Ionesco,〝Le coeur n'est pas sur la main,〞Cahiers des saisons, no.15, Winter1959.
⑧Ionesco, interview with Claude Sar-raute, Le Monde, 17 Jan. 1960.
⑨Ionesco,〝La démystification par I'humour noir,〞Avant-Scène, Paris, 15 Feb.1959.
⑩F. Towarnicki,〝Des Chaises Vides... à Broadway,〞Spectacles, Paris, no. 2, July1958.
文字|曾麗玲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