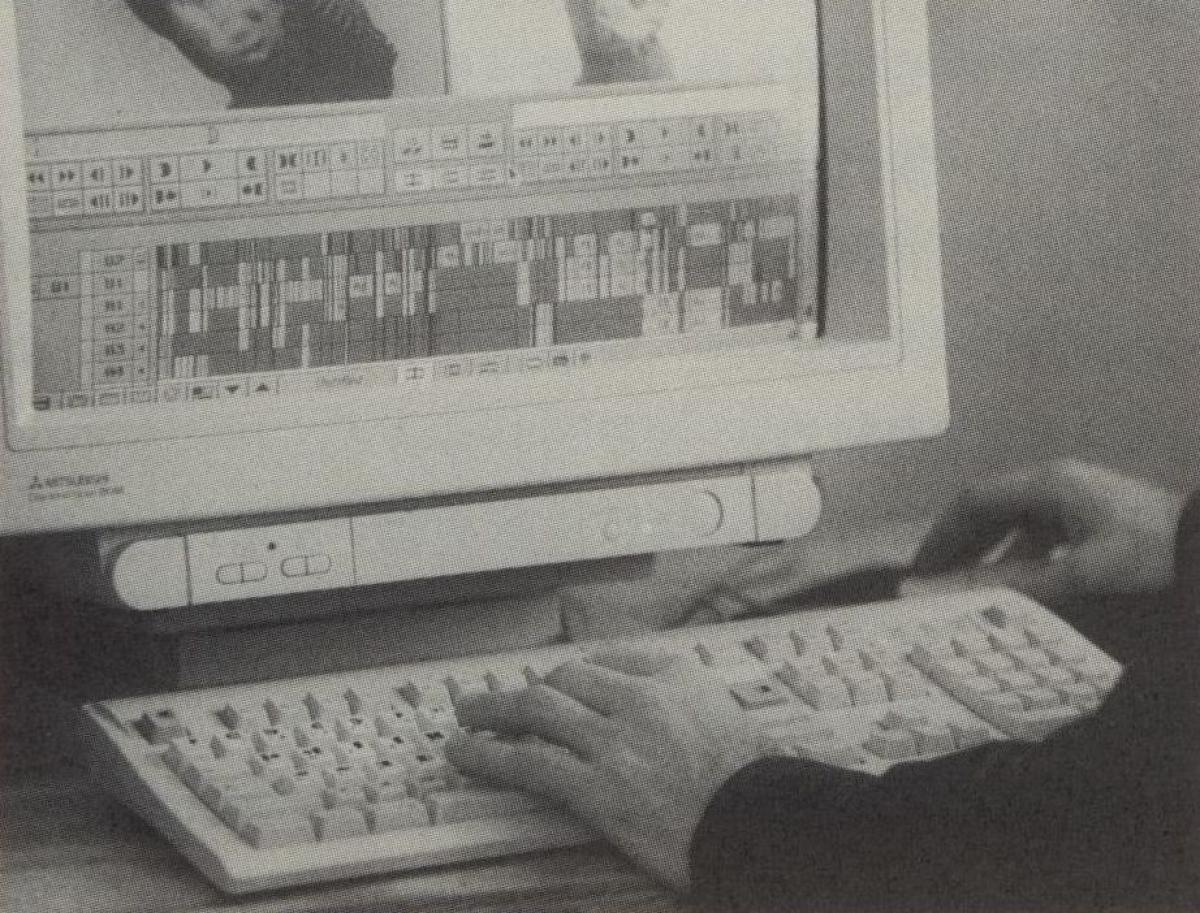錄像在舞蹈的應用是一種進步嗎?
舞蹈在錄像裡失去了什麼?
一九八二年,在紐約市一個有關舞蹈與錄像的硏討會上,傑夫.鄧肯(Jeff Duncan)力促衆人抵制錄影紀錄的惡性侵入。他勸吿我們,千萬別允許自己的作品爲這種難以掌控的媒介所評斷。依他之見,錄影紀錄不足以呈現舞蹈這種藝術形式。當時,我覺得他的想法太極端了,實在沒必要這樣。沒錯,我承認要把舞蹈作品放進錄像規格裡,確有不少限制存在。旣然錄像技術能使舞作被更多的遴選單位,如藝術委員(arts councils)、國家藝術資源會(NEA-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經紀公司與經紀人等來鑑賞與評估,我覺得這是無可避免的科技突破,應將其視爲某種進步。
抵制錄像的惡性入侵
泰半的與會者也多像我一樣,覺得傑夫.鄧肯的警吿過於偏激,且有守舊之嫌。再說,我們畢竟是所謂「現代」舞蹈的一份子,甚至有時還因爲被貼上「前衛」或「後現代」等標籤而沾沾自喜,我們又怎能拒絕「進步」呢?
然而,最近的一次經驗卻使我開始對這種媒介的適當性產生懷疑。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當時我爲天普大學校友會的表演評委會擔任主席,由於參選的作品來自各地,我們決定憑錄影帶作決選。
評委會眞的看了所有的帶子,雖然常常因不耐煩而用快轉瞄過。評選結果是,唯一一支專業拍攝的影帶獲得全體同意而保送入圍(即使裡面只秀了舞作的零星片段)。至於其他的帶子,則沒有人顯出絲毫的熱情。有位評審看過某個影帶的現場演出,替它說了幾句好話,它就中選了。有兩支帶子來不及寄到,但編舞家曾向我描述舞作,好讓我向評委會說明,結果這兩團也上了榜。最後爲了湊數,評委會勉強塞了些相當無聊,只因有現場伴奏而略顯不同的作品。我覺得,這種無奈的結局與影帶的觀看不無關係。評審們對能看到影帶全貌的作品倒足胃口,卻傾心於集體想像的產物。到頭來,影帶製作的專業程度竟超越舞蹈本身成爲評選的標準。
舞蹈的某些隱喩來自它稍縱即逝的短暫存在。比起其他的藝術形式,舞蹈很難產生任何有形產物。爲使舞作能如音樂般恆久留存而建構舞譜,這嘗試在舞蹈史上一直持續地進行著。廣受現代舞壇支持的紀錄系統──拉邦舞譜,近來確有被錄影科技凌駕的趨勢。影片(film)因所費不貲,影響不大,倒是開銷較小的錄影作業,的確比舞譜紀錄及人員重建快得多。
舞蹈學生及專業人員可以從錄影紀錄,更快、更容易地學習舊作。況且大部分的舞蹈作品都會爲了經費申請、資料紀錄、舞作保存、宣傳推廣、評論分析,與演出回應等種種理由作例行錄影。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要將動作中活生生的人體轉化爲錄像,其中肯定有許多缺損與不足。
編舞家喪失主導權
不妨就從「尺寸」(size)說起吧!曾有人就此議論,旣然觀衆能接受電視劇裡的人物尺寸,爲什麼換成舞蹈就不行呢?這問題可用電影作例子來回答,當電影放在電視螢幕時,原本氣勢盛大的群衆場面變得很無聊。
舞蹈錄像用在單一或少數舞者時效果較佳,反當有越多的個體想擠進這個長方形的空間,人變得更小,觀衆便覺無趣。這與現場演出的情形恰恰相反,台上的人數愈多觀衆愈覺震憾。
再者,電視螢幕的矩形尺寸與人體比例不符,即使整個畫面僅納一人,也得裁掉頭或腳,而焦點亦僅能在足部的舞動節奏與面部表情間兩者取一。至此,細部特寫所看到的不再是舞蹈,倒成了錄影師的個人表現手法。
舞蹈與動作息息相關,是動作之於身體與其他身體的動作,也是空間中的動作與動作穿流的空間。錄像完全不足以捕捉此種現象。在現場演出中,表演者身邊未被佔據的空間蘊含著可能性,但在錄像中,離開螢幕就是不存在。
舞蹈的部分即時性來自於「動能反應」(kinesthetic response),或可說是觀衆對表演者正從事之身體活動所生出的同感心。假使攝影師選擇緊隨某一人,以表現其動作,則不管此人往何處舞去,他還是在原處──螢幕的正中央。或者,攝影師可以選擇呈現某人從一端舞至另一端的畫面,但這將大大削減了此人的重要性,而其中所含足以喚起動能或情感反應的力量將消失殆盡。
另一個空間的層面是「框限布局」(framing),總地來說,這是指編舞家運用界定鏡框之後、地板之上的舞台空間,或是佈景與舞者位置的安排。框限布局可說是編舞家的構圖藝術之一。這些框線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只不過是編舞家在創作時的考量罷了,但當舞作轉移至錄像,它們卻被全盤抹煞了。在錄像中,錄影師擔起了框限布局的工作。動作設計或許與原作無異,但卻因與框限布局關係的變化使舞蹈產生劇烈改變,且編舞家完全喪失操控這項重要元素的主導權。
舞蹈在錄影裡的變形
編舞家的工作空間是舞台,所以總有些「規範」(conventions)可循。其中一項假設是,劇院正中央是最理想的座位,因此舞台的正中央具有非常大的力量。這項規範使得即使因受劇場建築之限沒坐在正中央座位、未能享有相同視野的觀衆,也能認可舞台中心的特殊意義。
當我觀看舞蹈錄像時,我會不自覺地去辨認方位,哪裡該是中心,哪裡該是翼幕等等,除非作品明顯地打破規範,專爲錄像的螢幕而編作。譬如,最近保羅.泰勒(Paul Taylor)所作《舌語》Speaking in Tongues的《舞在美國》Dance in America版,當這支舞從舞台版本轉化爲錄像時,其原與傳統規範的關係蕩然無存。
「景深」(depth)也因錄像而大受影響,實際上近乎消失。在鏡頭焦距不斷的改變之下,眼睛接收縮小尺寸的形體時,無法測出相對距離。比方在現場演出,當動作急速地由後向觀衆前進,使形體赫然聳現時,能營造出極爲戲劇化的效果,但在錄像中卻看不出這層變化,動作的影響力頓失。
從對角線拍攝能使舞蹈在螢幕上看來更有趣,且事實上,許多編舞家也覺得,這種取景角度在美學上的呈現較佳,也比死板的拍法更貼近原作意圖。但這卻讓初始的動作設計完全變形。觀看的角度也與原來完全不同!
「時間」(time)是另一個慘遭扭曲的元素。在錄像裡,慢的變得更慢,快的頓時顯得無趣,中板則令人厭煩。極緩的慢動作反而經得起細看,但其顯現的控制力卻超越了實際的人類體能極限。
或者是因爲上述時空感知的綜合曲解,在錄像中能展現的動作質地變化很少,導致舞作淪爲一連串姿勢的連續流動。
(待續)
原作|安‧娃向 Ann Vachon 紐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翻譯|黃琇瑜 倫敦城市大學藝術評論碩士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