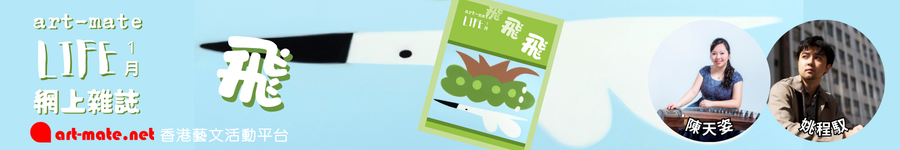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金烏藏嬌》的創新企圖,不只擺在角色重新詮釋,更大一部分如編導所言,是在於「金烏」的重新堆砌。然而這個堆砌,似乎偏離了重點,反倒弄巧成拙地堆砌了一場意向並不明顯的繁瑣。燈光的多重切割,甚至道具的裝飾堆積,不斷給予觀衆大量的文化符碼,但它們的意義,沒有超越填補空白的心理焦慮。
當代傳奇劇場《金烏藏嬌》
8月15〜18日
國家戲劇院
十六年前當代傳奇推出「捨忠孝而就不義」的戲碼,爲台灣傳統戲曲的再生,斬荊劈棘;自此「傳統」該不該創新,根本不是問題,大家更期待的是創新的手法。格外有意義的是,從國家主導的京劇團出走而自創民間劇團,當代傳奇將京劇的思考,帶離六〇年代以降京劇國家化的夢魘,義正辭嚴地邁向傳統戲曲現代化的路徑,甚至走向戲劇國際化的藝術市場思維。然而,這條由現代化而國際化的傳奇道路,歷經十六年的累積,儘管有著開疆闢地的豐功偉業,但似乎也走入了另一種市場的迷思,甚至走進了美學的死角。
綜觀當代傳奇所累積的作品,戲曲演員面對傳統陳疴的現代悲憤,像一股永不止歇的情愫,澎湃蕩漾於各種文本詮釋與角色關係之間;這一點曾經讓八〇年代戒嚴晚期最後的狂飆青年爲之動容,也成爲當代傳奇的不老動力。在創作手法上,無論是改編外國名著、或新編劇目、甚至舊戲新編,當代的作品累積出一種共同的模式:利用國際世界的元素(如著名文本),推介演員身上承載的表演功力,並在整體視覺設計上,力求在這兩者間保持平衡。當代的風格,因此很有多文化拼貼的效益,這點無疑協助他們順利打入國際市場。有趣的是,在國際藝術市場的正面支持之餘,總也斷斷續續聽到國內兩極化的負面言說:或有非議他們任性濫用傳統元素,更有責難他們革命不夠徹底,在顚覆傳統之餘,卻是藉口現代化而販賣東方情調。然而,究竟何謂創新?向西方市場販賣東方主義罪在何處?禍首哪裡找?《金烏藏嬌》的《烏龍院》嘗試,或可以讓我們共同反思一些關於「創新」與「東方主義」的求全與非難。
難展現出人意表的新觀點
要說《烏龍院》是所有熟習傳統劇目的現代人的共同喜愛,也許並不誇張,原因可能正在於它不純粹的傳統:宋江一本正經地豢養名妓,不僅傳統而且庸俗;張文遠越禮玩師娘,更是典型的「小白臉」負面形象;理直氣壯見異思遷的閻惜姣卻徹底顚覆了既有的傳統,整齣戲有了不尋常的現代意味。面對這樣有趣的老本,《金烏藏嬌》首先將宋江詮釋出一種新意:他不僅一本正經,而且還明顯地窩囊可笑;吳興國的表演本來不受傳統行當的局限,這個特色在此更能賦予宋江新的解讀。至於《金》劇對閻惜姣的演繹,一則因爲全劇開始新添了她賣唱身世的交代,便有些畫蛇添足地渲染了她的哀婉,再則夏褘的表演,也將這個角色詮釋成爲一個不諳人事、任性闖禍的年輕女孩。
是以,《金》劇不能說沒有新意,它實訴說了一個新的宋閻關係:男人的虛僞顢頇,加上女孩的不甚世故,擦槍走火地招來殺身悲劇;原本一個一廂情願的男人與一個潑辣不義的女人的關係,也被改寫爲成一個平庸顢頇的男人與一個天眞不畏的少女的故事。只是這樣的企圖削減了老本裡面女主角讓人招架不住的火辣與不尋常的霸道,而男女主角關係的轉變,也難以和後段「活捉三郎」女主角由激烈而凌厲的訴求銜接起來。原本有點超現實趣味結尾上,也因此難以展現什麼出人意表的新觀點。創新,除了更動原劇,難道不可以讓原本存而不論的特殊觀點,重新出土,再透過調度手法,讓它幻化蛻變?
視覺營造與戲劇内涵缺乏溝通
《金烏藏嬌》的創新企圖,不只擺在角色重新詮釋,更大一部分如編導所言,是在於「金烏」的重新堆砌。然而這個堆砌,似乎偏離了重點,反倒弄巧成拙地堆砌了一場意向並不明顯的繁瑣。諸如舞台的空間建構,從紗幕的意象、竹簾的披掛、到室內室外的移動、乃至烏龍院上上下下的搭建,不見華麗,卻見綴飾。燈光的多重切割,甚至道具的裝飾堆積,不斷給予觀衆大量的文化符碼,但它們的意義,並沒有超越「塡補空白」的心理焦慮。可是,有什麼需要塡補的呢?主要演員的能力,適足以將空無幻化爲虛華,哪裡還需要塡補?或者,想要塡補的,是創作者對於觀衆的擔慮,怕年輕觀衆不能欣賞老戲?怕外國觀衆無法專注戲曲的表演?原來茶館、竹簾、閣樓、屛風、皮影戲與鬼步,是充滿新意的?原來他們暗示從顚覆傳統起家的當代傳奇,也逐漸「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自覺地迎合西方市場並販賣東方主義的異國情調?
要說以再創傳統起家的當代傳奇,在《金》劇裡過多且沒有必要的文化綴飾,堆砌一場東方主義風尙的符號展示,眞是莫大的反諷,也可能是一場極爲嚴重的誤解。畢竟從他們最早的作品裡,當代便刻意追求新的服裝與場景,其中展示創作者對於京劇表演程式重新思考的高度自覺:諸如桌椅的變形,抑或水袖的重剪,觀衆總能看到擔待的演員身體,靈活地在傳統身段與新的身體空間之間探索新的可能性。因此,苛責他們回到一桌二椅的格局,絕對是不解風情的老古董心態。然而,在《金》劇裡面,我們看到的卻是空間與表演之間缺乏創見的凌亂與失序。視覺營造與戲劇內涵不再溝通;販賣文化符號的意圖顯得過於明顯甚至焦慮不安。
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這裡未必斷言迎合東方主義是當代傳奇的刻意營造;傳統是他們想要成爲現代人的缺憾與宿命,又是他們賴以立命的支柱。然而,開始進入國際市場後,傳統逐漸浮出新意,不僅必然,而且重要。即便是針對國際市場思考而凸顯傳統,也不見得就是不堪,當代傳奇更不是只能創新不能敘舊。筆者想要提醒的是,體認傳統的精粹,與販賣傳統符號之間,是有區別的。同樣地,與其以「民族主義」的新八股去責求一個民間團體自求生存的搏鬥,不如檢討什麼樣的環境生態,營造鼓舞了這樣的「自我東方化」的選擇?
誰敢與東方主義唱反調
是以,若眞要追究這場不知不覺形成的東方文化符碼的堆砌與賣弄,我們不得不又上溯台灣早期擺脫不掉的認同包袱,並追究近年文化政策缺乏作爲、徒然虛與委蛇的鄕愿與保守。究竟爲什麼販賣傳統與東方神秘,至今仍是表演藝術進軍國際的必然策略?爲什麼台灣視覺藝術的對外策展早已不再向國際市場販賣國畫與書法時,表演藝術界卻還擺脫不掉重複操演「中西融合」的思維窠臼?爲什麼獨獨是表演藝術界不能擺脫對西方市場的「東方主義」迷思?這究竟是西方市場過度耽溺在東方主義的想像裡,還是藝術家無法擺脫將自己東方化的預設立場?這眞的是因爲國際表演藝術市場的保守宿命,以及國內現代表演藝術的乏善可陳使然?然而,全面責難西方市場的東方主義,以及非議國內現代劇場的不成氣候,是否眞的公平?藝術家又豈是唯一必須承擔此責難的對象?
換言之,文化官僚的勇氣與嫻熟度,是否也急需被檢視?當我們責難一群藝術工作者時,是否也應該檢討那些仲介他們進入國際藝術市場的文化官僚與菁英領袖?例如,當我們的文化官僚在向國外藝術經紀仲介台灣表演藝術時,是否敢於開創市場既有口味,推薦沒有東方元素的作品?當我們的輿論菁英爲創作者運籌帷幄規劃未來時,是否能夠辨識新的創作能量,累積美學論述的系統,給予年輕的創作足夠空間與時間,讓新的表演藝術美學成長茁壯?還有,時下所謂藝術產業化,爲什麼只是一味卑微地追隨鑽營既有的市場口味,而不敢開創新的產品品牌?換言之,爲什麼表演藝術界從美學論述到市場言說,都只能採取最保守的思維與策略?這對於強調創新的藝術而言,豈不是最大也最深刻的反諷與嘲弄?生態如此,環境如此,浸淫在這樣的文化作爲與言說之中,剛闖入國際市場的台灣表演藝術工作者,又豈敢與既有的東方主義唱反調,另闢蹊徑呢?
面對國際藝術市場,台灣劇場也許眞的處於自主與銷售的兩難處境,但意欲突破的創作者,在國際市場與國內票房之間尋找平衡點的時候,該如何避免被醬缸的政策作爲與保守的市場想像牽著鼻子走?還有,在國內觀點與國外意見之間搭建可雙向來往的橋樑,是否仍然値得努力?這絕不只是當代傳奇獨立面對的問題,更恐怕是所有刻正思考打入國際市場的文化官員、藝術評論者、以及創作者和經營者所需共同面對的課題。
文字|周慧玲 中央大學英文系/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