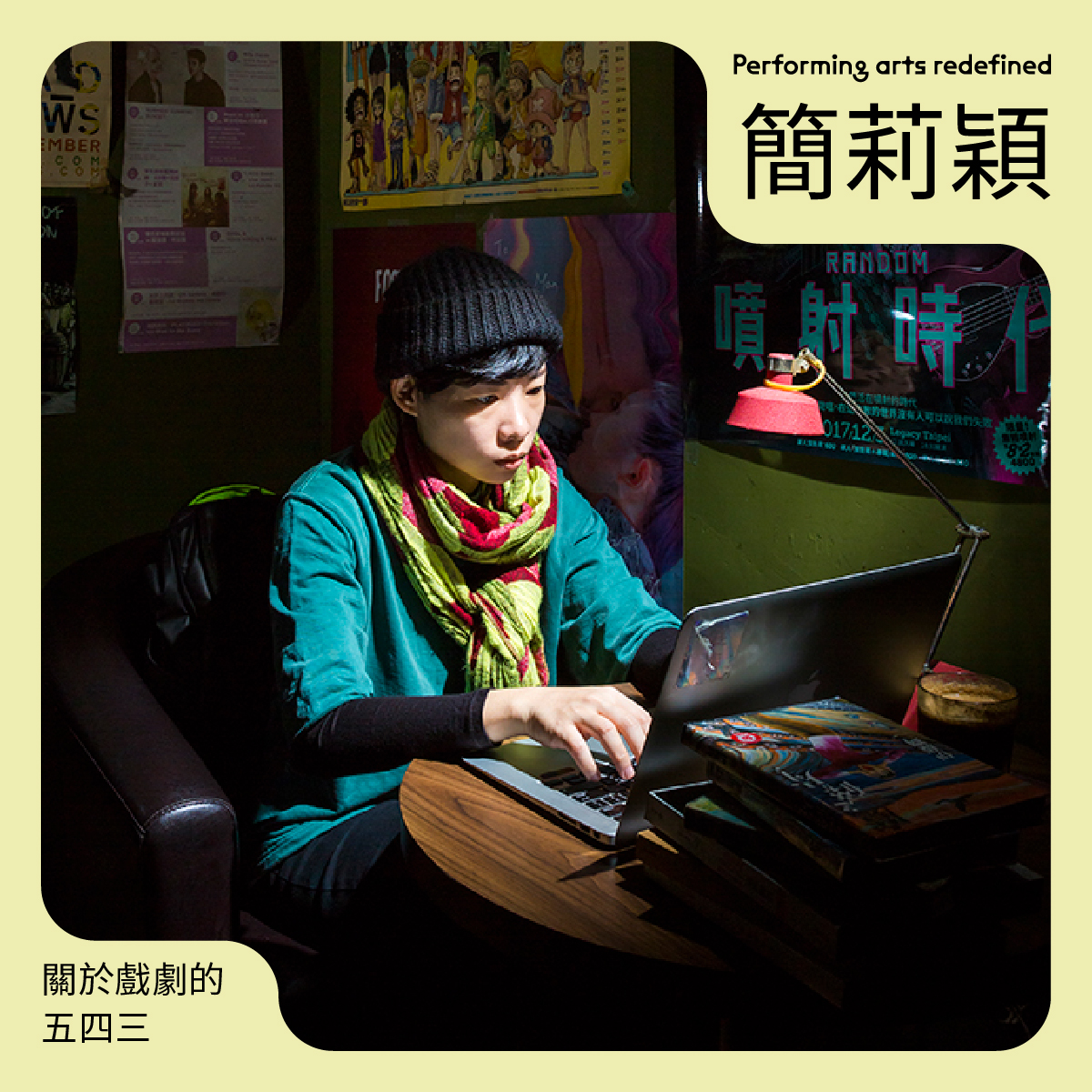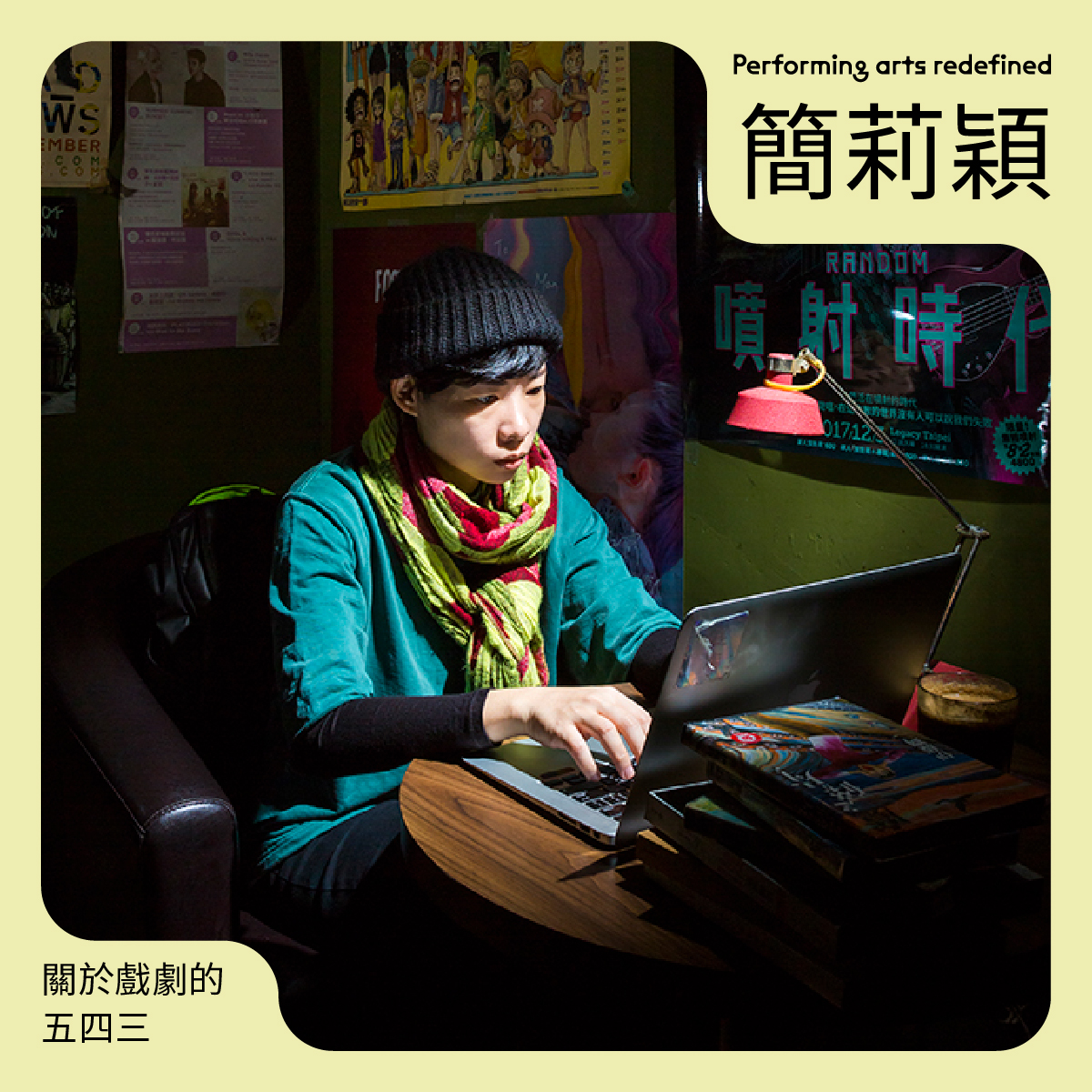本文將以楊孟軒教授描述台灣外省人離散研究的《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為引,從離散「外省人」視角,到台灣本土認同的多族群語言、地方書寫;透過分享楊教授這本2023年出版的研究,鼓勵擁有外省記憶的後代,重述自己的記憶與歷史,除了否拒本土族群(閩、客、原、新)的自我追尋,或許值得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楊孟軒在《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的創傷、記憶與認同》這本研究,丟出一個提問:為什麼第一代移民很少有回憶逃難的經驗?為什麼2000年後開始,陸續有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齊邦媛《巨流河》、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等外省後代以家族為座標,爬梳集體記憶的著作出版?
楊孟軒透過口述訪談、文獻資料,以「創傷」、「記憶」、「離散」三大理論支柱,試圖剖析1945-1950年在國、共兩個殘暴的軍事集團對峙中(比如湖南饑荒、長春圍困戰餓死了大量平民),這群跟著國民黨來台的戰爭移民,如何處理他們的創傷,與怎樣形塑自己的文化與身分認同。
楊孟軒提出一個學術上的討論:外省人的雙重性,認為他們既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民,抵台後又握有政治分配的權力,楊提出了外省人經歷的4個社會創傷:一、1949年的大出走;二、1950年代末的返鄉夢碎;三、80年代末期的探親夢碎;四、1990年代後面對「台灣本位」的焦慮。
每一次社會創傷,外省人就會從記憶資料庫中,提取一段記憶來療癒傷口:1949年後,有大量回憶對日抗戰勝利的書寫,特別是通俗旅遊文獻,許多人將台灣的經驗與過去在中國的逃難,特別是重慶的經驗相比,也深信最後的勝利返鄉必定到來,「戰時過客」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成為中影拍攝優秀抗日電影的重要基礎。到了1958年,蔣被迫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知道回不去了,外省人的重要記憶又開始改變,「文化鄉愁」取而代之,他們開始大量組織同鄉會,出版湖南文獻、貴州文獻等,此時卻面臨第2代子輩對此興趣缺缺。1980年代,解嚴後開放探親,有成千上萬的外省人返鄉,這是第3個創傷,也就是返鄉後人事已非的風景,在外省人的返鄉文學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日思夜想的親人,變成唯利是圖的陌生人,此時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成為他者」作為「外省人」的恐懼,年輕一輩「外省人」關懷長輩、懷念家鄉,「老兵文學」及「眷村文學」開始興起,劇場界當以賴聲川為首的創作為代表,也為後來第3波的文化記憶「講述大出走」(narrating the Exodus)奠下重要基礎。
是以,這就回到了楊一開始丟出的問題,「為什麼外省人二代,開始產出大出走的記憶?」作者認為,這是為了證明:「為了構築以在地為基礎的『外省臺灣人』認同。……他們為父母及祖父母在1949年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與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
楊孟軒的爺爺、外公家族皆是二二八的受難者,父母在他10幾歲時帶他移民加拿大,絕口不提上一輩的遭遇,一直到回台灣做研究之後楊才認識家族的歷史,但在訪談外省二代的過程中,楊從咎責的憤慨到理解了當中的複雜。
除了社會意識的變化,自己就讀戲劇系以來,從翻譯戲劇、戲曲改編與賴聲川為首的戲劇作為代表,再到如今以台灣社會為創作主題,華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言作為演出語言,從業10幾年來有極大的變化,我認為,白恐主題的戲劇,並不僅僅只是如王墨林在之前PAR的劇評所言,是「執政當局的轉型正義政策的宣導」,群體身分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構成自身的重要元素,遠在自己出生之前的事,建構了一個族群的身分認同。任何歷史類型的戲劇,都需要更多元的圖像,當然,也包括「外省人」圖像,是以,與其否定重述過去的戲劇之必要性,不如去探問,擁有不同身分記憶的創作者對記憶的怠惰:白色恐怖並非單單本省福佬人所有,根據楊書中的資料,1950年代初期,外省人占台灣人口約10~15%,但被檢肅為匪諜的,外省人占了一半的比例,這代表外省人受國民黨迫害的比例,是本省人的6到7倍。而許多本省作家、政治人物在70至80年代對外省老兵的關心,也在當代族群政治的嚴重分歧中被遺忘。
這本書引述的訪談跟文獻都有血有肉,有人情緒激動,有人掉頭就走,有人不滿「外省人」一詞,在戲劇中,「細節」就是讓人產生同理的要素。我也是念了原住民系因而了解自己作為都市漢人,資源比原住民豐厚許多。作者指出,「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不會因此就特別神聖,與加害者的關聯並不構成原罪」。如何進一步去理解彼此的記憶,試著說出自己的記憶,或許會是進一步凝聚身分與文化共識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