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莉穎
劇場工作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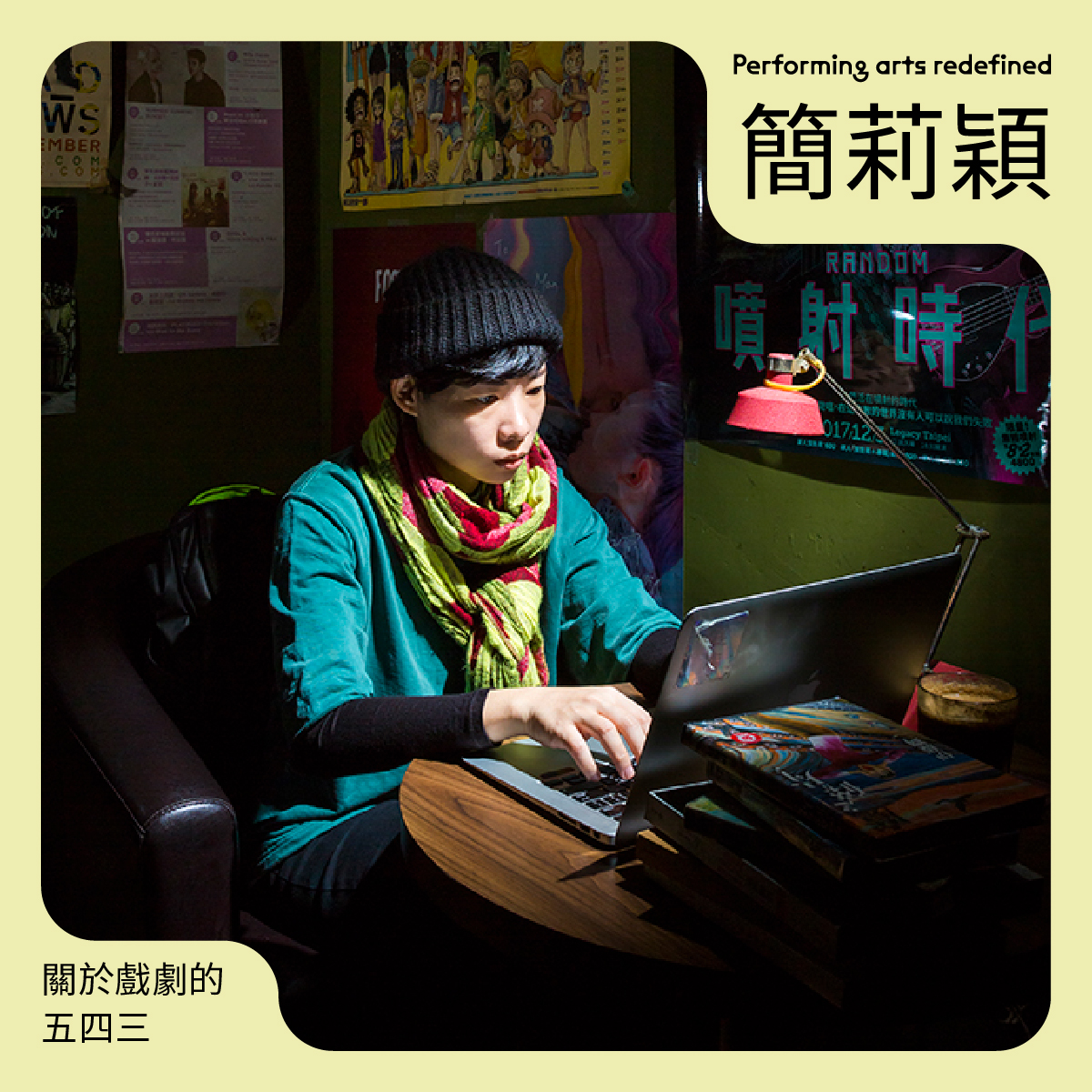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喜劇與恐怖一線之隔
(黑畫面)「這是個真實故事,兩年前就發生在我的小鎮,很多人以奇怪的方式死掉這個故事從我的學校開始。」(學校畫面)「梅布魯克小學從幼稚園唸到5年級,一個平常的禮拜三,有一位新來的老師。」(主角跟拍畫面)「她的名字是潔斯汀.甘迪,她在那一天走進她的教室,就像每個早上一樣,但今天不一樣。」 「別班的孩子都到了,就連貝爾老師教的另一個3年級班都坐滿學生,但甘迪老師的班級空無一人,除了一個男孩,他的名字是艾力克斯.利里,他是班上18個孩子中,唯一去上學的小孩,知道為什麼嗎?」 (家中畫面)「因為前一晚,凌晨2點17分,每個小孩都醒過來,」 「下床,走下樓,打開前門,走出前院,走進黑暗,再也沒有回來。」 伴隨著小孩說故事的童音,音樂進,暗夜籠罩的美國郊區住宅,一群孩子以類火影跑(漫畫火影忍者的跑姿)之姿,衝出前門,在空蕩蕩的大馬路上狂奔。 恐怖電影《凶器》(Weapons)的開場,今年看的新片中,最喜歡的開場,沒有之一。 整部片從學生失蹤的那個早晨開始,以人名字卡切換,第二段跳到尋找孩子的父親、接著是偵辦此案的警察、商店門口無所事事的毒蟲、校長、男孩艾力克斯,帶出一個看似老掉牙的吹笛人故事。在看完全片後,讓人驚覺原來整個失蹤案的兇手早就出現了,是一部值得回頭二刷發現細節的電影。 順敘會讓這個故事普通,但敘事的形式即是內容,伊底帕斯王的故事若從頭開始講易流於流水帳,且犧牲了最懸疑的部分,正是這種敘事的巧思,視角的跳躍使得《凶器》免於大多數恐怖片會有的問題:主角降智,看起來詭異的地方硬要進去,無止盡的嚇人鏡頭(Jump Scare),《凶器》展示出真正恐怖的事情 「當人們平靜日常被破壞的瞬間」。 看完《凶器》,立刻找了編導的首作《宿劫》(Barbarian)來看,驚為天人,用3個主要角色,把「地窖裡有怪物」這類經典的恐怖片類型做出新意,一棟普通的民宿,有多少暗黑的過去,編導Zach Cregger非常擅長沉浸的鏡頭、恰到好處的劇情斷點,透過鏡頭外的聲音,想像力營造出巨大張力,透過多線,怪物出現就卡掉鏡頭,跳到下個角色,完美避免角色如何逃過怪物攻擊的疑惑,掛心角色之後的命運。本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八寶粥與數字
近期因工作接觸到的內容與金融有關,稍稍研究總體經濟,深感興趣。 從「AI爆發」「為什麼台灣半導體這麼有優勢?」「什麼是通膨?」「什麼是降息?」「台積電還可買嗎?」這些基礎問題,到總體經濟、經營權之爭、到金融制度,加密貨幣,只要有興趣,一點都不無聊,並且可以使自己稍稍對陰謀論免疫。 發現自己完全是金融與產業小白,但隨著產業鏈遷移、AI爆發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台積電成為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赴美設廠更是輿論角力的戰場。電子科技業的發展,將徹底影響整個世代的台灣人。從漲也不知道在漲什麼,跌也不知道跌什麼,川普一關稅就跟著恐慌,開始去了解產業數據,當台灣的命運與半導體緊密相繫在一起,而這背後承載數代台灣人的努力,覺得自己至少要能稍稍看懂財報、聽得懂法說會,畢竟台灣是靠著向外走才有辦法生存的地方。製造業人口占3成,科技業30多萬人,出口占超過六成的GDP,什麼時候能有一部工商題材或者半導體題材的劇呢,期待有一天能出現,並且自己也不畏挑戰吧。 「經濟學就是事與願違的科學。」「經濟學是關於選擇。」「經濟學是理解人類與社會行為的底層邏輯。」一邊在筆記本上寫下這些摘錄,一邊看著各種精采的金融案件、產業奇蹟,理解不同行業制度當然困難,從自己身邊的物件入手入眼,很能引起興趣。 像是八寶粥。 前幾年在做韓劇改編時,沉迷泰山與龍邦建設的經營權角力,堂弟詹皓鈞發文質疑堂哥使家族之爭浮上檯面,他直指前董事長詹岳霖在任時有6年發不出股利,虧損連連,下台後還攜手龍邦建設步步逼近,一時之間因對幼時食品的感情,對龍邦董事長劉偉龍「黑道」、「殯葬業」、「股市圈地仔」的負面標籤滿天飛,群眾一片霧裡看花,一度以為再也吃不到八寶粥跟仙草蜜。隨著事件變化,了解起初泰山是避免2018年保力達買下三成股份爭奪經營權,擴增股本引入龍邦稀釋保力達股份,起初龍邦與泰山共治公司,孰料保力達處分泰山股票,龍邦不知是加碼攤平還是低價收購,快持有超過一半股份,加上得到前董事長、被逼退的詹岳霖等家族成員支持,才讓泰山之爭浮上檯面。 2022年11月市場派劉偉龍宣布年底召開股東臨時會,12月公司派董事長詹景超出脫原本持有的金雞母全家超商,開盤兩分鐘內賣掉4萬3千張股票,占全家超商股份達19%,劉偉龍受訪時大罵公司派是「強盜」、「一定有與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小粒訪RAY—關於百老匯的五四三(4)
在觀眾眼底滾動式調整 全員戒備「試演」一個月
「小粒」是台灣編劇簡莉穎,「RAY」是旅美影像設計孫瑞鴻,兩人透過一場老友間的專業閒聊,有問有答心得滿滿地解密百老匯除了有RAY今年「初登場」就榮獲東尼獎、戲劇桌獎入圍肯定的驚奇過程,還有這個劇場之都商業經營與運作的幕後種種藉著文字,也讓讀者沉浸感受「劇場產業」是怎麼一回事。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小粒訪RAY—關於百老匯的五四三(3)
商業票房決定作品存續 好萊塢明星也齊聚百老匯
「小粒」是台灣編劇簡莉穎,「RAY」是旅美影像設計孫瑞鴻,兩人透過一場老友間的專業閒聊,有問有答心得滿滿地解密百老匯除了有RAY今年「初登場」就榮獲東尼獎、戲劇桌獎入圍肯定的驚奇過程,還有這個劇場之都商業經營與運作的幕後種種藉著文字,也讓讀者沉浸感受「劇場產業」是怎麼一回事。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小粒訪RAY—關於百老匯的五四三(2)
登上戲劇桌獎與東尼獎典禮舞台 近身體驗紐約劇場盛事
「小粒」是台灣編劇簡莉穎,「RAY」是旅美影像設計孫瑞鴻,兩人透過一場老友間的專業閒聊,有問有答心得滿滿地解密百老匯除了有RAY今年「初登場」就榮獲東尼獎、戲劇桌獎入圍肯定的驚奇過程,還有這個劇場之都商業經營與運作的幕後種種藉著文字,也讓讀者沉浸感受「劇場產業」是怎麼一回事。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小粒訪RAY—關於百老匯的五四三(1)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小粒訪RAY—關於百老匯的五四三(1)東尼獎、戲劇桌獎雙入圍 孫瑞鴻的百老匯驚奇之旅
「小粒」是台灣編劇簡莉穎,「RAY」是旅美影像設計孫瑞鴻,兩人透過一場老友間的專業閒聊,有問有答心得滿滿地解密百老匯除了有RAY今年「初登場」就榮獲東尼獎、戲劇桌獎入圍肯定的驚奇過程,還有這個劇場之都商業經營與運作的幕後種種藉著文字,也讓讀者沉浸感受「劇場產業」是怎麼一回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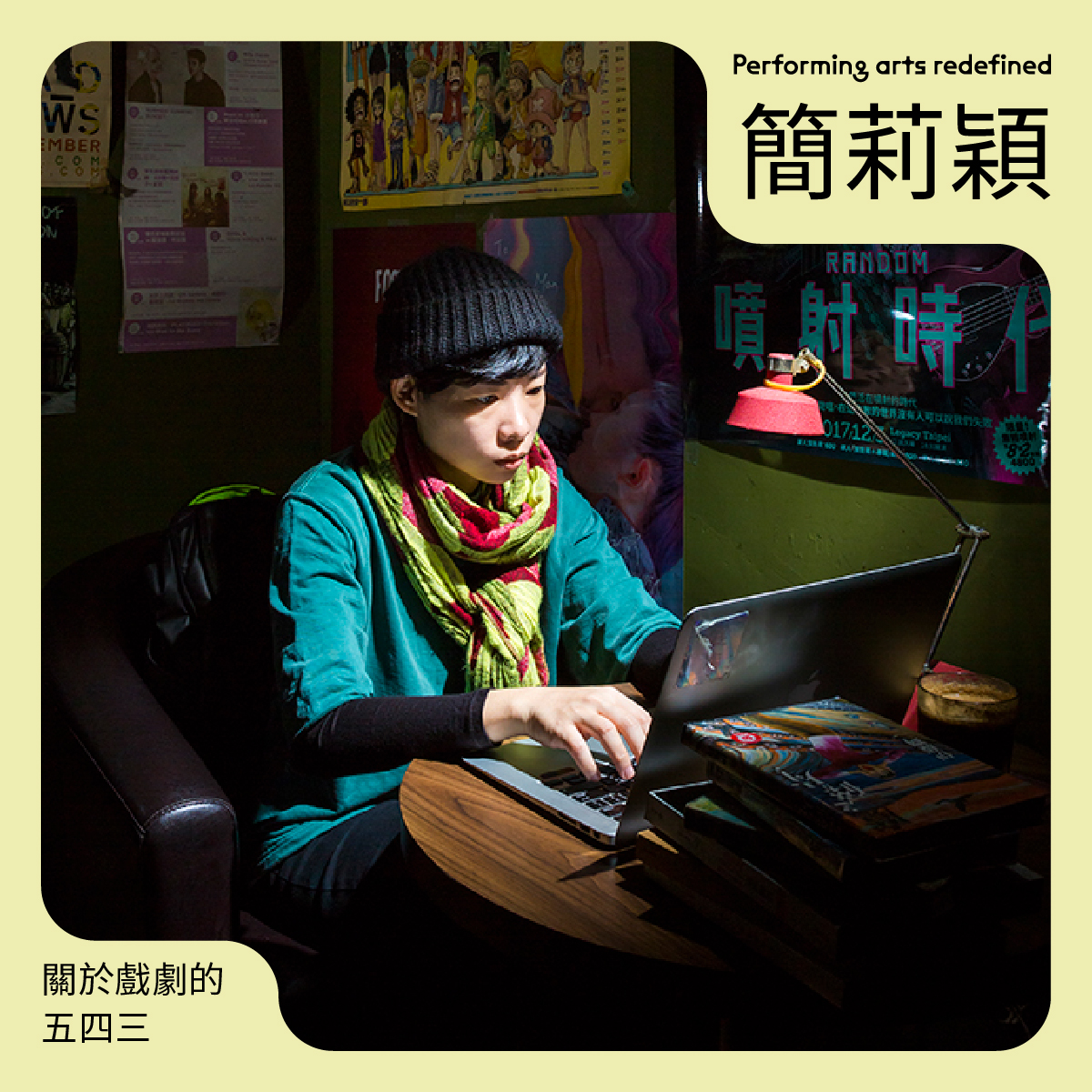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片廠風雲》、《日落大道》、《Sunset Blvd.》的選角
一向喜歡塞斯.羅根(Seth Rogan)的喜劇,今年終於有他的新作了,Apple TV獨家,塞斯.羅根擔任聯合編導與主演的影集《片廠風雲》(the Studio, Apple TV)節奏緊湊、諷刺連發,一鏡到底的喜劇設計機智幽默,找真實世界的好萊塢編導扮演他們自己,更是內行外行的門道熱鬧都顧到了,塞斯飾演的一間片廠的CEO(Studio Head),熱愛電影,卻同時要解決片廠存續的現實壓力,雖然經過誇大,但細節與出發點的事件真實到不行。我一個在皮克斯畫分鏡故事板(Story Board)的強者朋友,也說一切都太真實了,試片、買斷劇本、頒獎典禮、選角、串流收購等等,想起那些看過的好萊塢併購故事:迪士尼買下皮克斯買下福斯、亞馬遜收購米高梅、HBO MAX到底要叫MAX還是HBO;第一集就請出馬丁.史柯西斯,看著看著,令人寬慰,連馬丁的劇本都可以被買下不拍了,其他人還有什麼好擔心?飾演Netflix執行長的還真的就是聯合執行長泰德.薩蘭多斯(Ted Sarandos),甚至還有朗.霍華、莎莉.賽隆、《絕命毒師》布萊恩.克萊斯頓、艾倫.索金等人,觀賞時完全可以感受到塞斯那種「嘿來做這件事!一定超好玩!」的瘋狂熱情。訪談中,塞斯被問到如何說服Netflix執行長來演一個Apple TV的影集,還是一位規定「演員得獎要在頒獎致詞中感謝Netflix」的串流高層完全不用說服,泰德很快回信,表示只要能喬得出行程就參與;塞斯強調,泰德就是一個熱愛電影的人。可以協調出這麼多大咖的時間、意願,佩服塞斯的協調能力跟精采犀利的觀察,要嘲諷內容產業的人,也要先開一個所有內容從業者都會覺得有趣的玩笑,以這些人的挑剔程度,肯定艱難,但這部做到了。 在這樣描述產業、演員真實與故事映照的作品中,想起了看《日落大道》、迷《日落大道》,搜查其中各種梗概的熱情。 《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erd,1950)是比利.懷德(Billy Wilder)編導的世紀經典,任何時刻點開比利.懷德的電影,都可以深深沉浸在他精采的故事裡,作家編劇出身的比利.懷德台詞精妙,完美運用黑色電影跟喜劇元素,角色紮實結構強大。 屍體在游泳池漂浮著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他是Joe,一個年輕失憶的編劇,因欠債闖入昔日默片巨星、好萊塢的標誌門面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戲長怎麼算?
剛開始創作的時候,並不會有「戲長應該要多久」的思考,只能從一次次課堂作業的時間要求,漸漸累積對戲長的掌握,隨著同時作為觀眾與創作者的經驗逐漸累積,理解到情感與核心還是得仰賴技術的輔助才能呈現,而思考「長度」的同時,也同時引領思考整體的架構布局。 都是先去做了,才去看技巧類的專書,編劇也好導演也好剪接也好,做中學,畢竟沒有自己走過一遭,光看技術書難以理解具體的流程,看完也可整體出符合自己習慣的方法,按照書上的方法不一定能做出成品,但得經歷了一定的實務經驗,才整理得出方法。 去年拍了短片,找了信任又仰賴的徐漢強導演擔任剪接,剪接時我還無法決定最終時長,在監製宗翰跟漢強的指引下,了解了國際影展上,最嚴格的短片長度要求不超過15分鐘(含演職人員表),金馬影展往年都是60分鐘,今年改成40分鐘。15分鐘是一個神奇的單位,《超棒影集這樣寫》提到,在20世紀初期,電影放映師每過 15 分鐘,便必須起身更換一盤膠卷。某些編劇理論學家則根據過去此一做法,將電影詮釋為8個 15 分鐘的片段。有線電視時代,每一段戲有很明確的分隔,那就是廣告破口,像是舞台劇分4幕,影集也有,依循著每13到15分鐘由廣告破口,將1集分為4幕,有時到5幕,或者4幕加上序場,劇本最重要的就是結構,時間如何被分配影響著結構。 與翠貝卡、日舞影展等美國指標性大影展有合作的「The Film Fund」電影發展基金,其網站簡介了短片的時長,以及須包含的:一、先簡單決定一個可以努力實現的預設短片長度,約為10分鐘,10分鐘剛好足以讓觀眾了解角色個性、角色發展、故事情節。二、創作劇本時要了解電影最後透過剪接來呈現,原本計畫的10分鐘可能變成5分鐘或15分鐘,當下唯一要專注的是寫出精采的故事。三、1頁劇本1分鐘(指的是美式劇本格式)。四、刪減不必要的對話,短片篇幅有限,與核心無關的對話都得刪除,如果自己做不到,請客觀的第三方來協助你。五、比起對話,短片更不能容納一些缺乏明確目的、沒有辦法推動情節的場次,1場大約1到3分鐘,是以短片不要超過15場。六、短片可以以一個神秘性或戲劇性的結尾結束。 帶著實際操作過的體感,回看之前的短片劇本,總共寫了13場,在範圍內,剪接時因對話與龐雜資訊較多,拿掉了一場,對話也經過裁剪拿掉重複資訊;不必要的場次不只後製,拍攝期也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與家人看戲
還是圍繞著吃食討論更無傷大雅些:「要在台中吃?」「回員林吃?叫外送?或者直接在家熱菜好了喔對了舞台很漂亮耶」。 或者聊聊交通方式吧:「騎腳踏車?」「台中捷運通車了呢我們都沒搭過」「會搭台鐵區間車回員林」「啊對,歌劇院之前有一家新加坡菜,倒了嗎」「黑天鵝那個舞者跳得很有力一點也不娘,很帥。」 這時候我聆聽。 不擅長聊天的家庭多半會為了食衣住行以外的話題困窘,離開臺中國家歌劇院《天鵝湖》的播映現場,多少普通日常的台中家庭這樣閒聊著,我也是其一。 過年期間,台中歌劇院的「NTT放映室」做了一系列春節特映:《灰姑娘》、《天鵝湖》、《睡美人》、《奧菲斯與尤麗蒂切》、《巴黎生活》等。免費放映,適合過年期間扶老攜幼前往,挑選適合家人一起看的劇目太艱難了,猜測兩個姪子可能的喜好,先排除歌劇,最後因應家人們的時間,挑中了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版的《天鵝湖》(Swan Lake)。 1995年的作品,2019年於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錄製,東尼獎得獎作品,美學較現代,又不至於去掉故事線到讓青少年看不懂,黑天鵝改由男舞者飾演,我不認為做任何事都需要帶來啟發,但至少分享給孩子們更多不同的人的樣子。 芭蕾舞劇開演,王子在床上掙扎惡夢,醒來後日常的行禮如儀,明顯取材自英國皇室,皇家不自由的生活與皇后的混亂情感成為王子的日常困境,王子一躍而起燈光轉換打在家人的眼鏡有反光呢。自覺陪家人看舞劇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在男女舞者跳舞時那芭蕾的抱、靠、張力,我都些微緊張,何況劇情推演到王子在湖畔遇到黑天鵝,展開一連串的雙人舞,那些親密、依偎與拉扯,感受到曖昧,我的腳趾不由自主緊抓地板,有點害羞與赤裸,畢竟在老家完全不可能看各種男性與男性、如此親密又汗水密合的貼身舞蹈,尚未劇終,已思考著如何自然開啟話題。 後方一直傳來小孩的聲音跟大笑,「王子怎麼這麼難過?」「王子要去哪裡?」,穿著豬肝紅羽絨衣的中老年人在某些時刻離去,開門、腳步聲、滑手機的人群,我從「看戲」,漸漸轉而注視著「看著群眾穿梭觀眾席的劇場」。 演出結束後,與親戚走出劇院,各自去上廁所,陷入短暫沉默。 親戚先反應:那個佛朗明哥跳得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本文將以楊孟軒教授描述台灣外省人離散研究的《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為引,從離散「外省人」視角,到台灣本土認同的多族群語言、地方書寫;透過分享楊教授這本2023年出版的研究,鼓勵擁有外省記憶的後代,重述自己的記憶與歷史,除了否拒本土族群(閩、客、原、新)的自我追尋,或許值得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楊孟軒在《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的創傷、記憶與認同》這本研究,丟出一個提問:為什麼第一代移民很少有回憶逃難的經驗?為什麼2000年後開始,陸續有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齊邦媛《巨流河》、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等外省後代以家族為座標,爬梳集體記憶的著作出版? 楊孟軒透過口述訪談、文獻資料,以「創傷」、「記憶」、「離散」三大理論支柱,試圖剖析1945-1950年在國、共兩個殘暴的軍事集團對峙中(比如湖南饑荒、長春圍困戰餓死了大量平民),這群跟著國民黨來台的戰爭移民,如何處理他們的創傷,與怎樣形塑自己的文化與身分認同。 楊孟軒提出一個學術上的討論:外省人的雙重性,認為他們既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民,抵台後又握有政治分配的權力,楊提出了外省人經歷的4個社會創傷:一、1949年的大出走;二、1950年代末的返鄉夢碎;三、80年代末期的探親夢碎;四、1990年代後面對「台灣本位」的焦慮。 每一次社會創傷,外省人就會從記憶資料庫中,提取一段記憶來療癒傷口:1949年後,有大量回憶對日抗戰勝利的書寫,特別是通俗旅遊文獻,許多人將台灣的經驗與過去在中國的逃難,特別是重慶的經驗相比,也深信最後的勝利返鄉必定到來,「戰時過客」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成為中影拍攝優秀抗日電影的重要基礎。到了1958年,蔣被迫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知道回不去了,外省人的重要記憶又開始改變,「文化鄉愁」取而代之,他們開始大量組織同鄉會,出版湖南文獻、貴州文獻等,此時卻面臨第2代子輩對此興趣缺缺。1980年代,解嚴後開放探親,有成千上萬的外省人返鄉,這是第3個創傷,也就是返鄉後人事已非的風景,在外省人的返鄉文學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日思夜想的親人,變成唯利是圖的陌生人,此時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成為他者」作為「外省人」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內容過剩
一個蘋果放在高山上,如果沒有人說,那裡有一顆蘋果,蘋果就不存在。 就像《PAR表演藝術》雜誌跟我邀稿,而且得是放線上,如果只是存在紙本,我敢打賭絕對不會有人看到這篇文章,我也不可能在忙碌的行程中記錄下自己點點滴滴對內容產業的觀察。 內容太多了,市場太小了,這是廣泛內容從業者正在面臨的問題。 2010年,Google的執行長施密特就說過,過去兩年人類生產出的資訊量,超過過去兩百年的總和。到了2024年,已成為前執行長的施密特,在一場史丹佛大學的演講(已被YouTube下架),提出了,TikTok並不是一個社交媒體,而是一種電視形式,美國用戶平均「每天」使用該應用程式90分鐘,製作200個短影音。現在人人都能生產內容、資訊,取得的成本還極為低廉。 學生時代,週末排滿就差不多看完該週的演出、上映的藝術片,買到一張專輯,就好好地從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還要攤開歌詞本努力鑽研它的設計跟每首歌串連在一起要傳達的意義。但現在,選擇太多以致難以選擇,有些以為有意義的事情,會否根本就沒有意義?現在,一首歌的時間愈來愈短,「出專輯」早就不是一個回收成本的商業模式,實體演出才是。所謂「影集」,也進一步出現更短的形式,不只集數更短,很難再見過去動輒60、70集的大長篇連續劇,在廣泛的平台上也出現了把角色動機說得非常清楚,5分鐘、3分鐘甚至1分鐘的豎屏劇;漫畫媒材,手機方便閱讀的條漫崛起,與頁漫分庭抗禮,成功的條漫每回解鎖的金額可以帶來比頁漫更多的收入。條漫在韓國,成為一種內容的載體獲得許多巨大的改編成功,某些分鏡與畫面的細膩作為傳統頁漫讀者在意,但對僅僅只是想在通勤的路上得到撫慰的許多人(這一切並沒有對錯),可以很快地沉浸到另一個世界,了解一下主角的歷程,就夠了。而不同形式的漫畫也發展出不同美學,只是評論體系來不及跟上。至於「看電影」,過去對我們來說電影院是看電影的唯一途徑跟體驗,但現在家中可裝的巨大螢幕早就替代原本電影院的功能,就像線上會議,我們都知道實體肯定會更有效率,但線上的便利讓我們早已回不去。要付出的時間成本、移動成本難以估量;今年日本出現了58分鐘的電影《暮然回首》,創造了超過10億日圓的票房,1小時不到的電影,以前難以想像,但當我自己走進電影院買票的那刻,想到電影只有1小時,鬆了一口氣,得到的體驗也非常滿足。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性格決定命運囉
此刻我要直白,需要直接破題,需要大叫! 對沒錯,性格決定命運,管你多有才華,做表演藝術戲劇電影影集這類團體性工作,如果你很難相處,很玻璃心,寬以律己嚴以待人,抱怨東抱怨西,沒禮貌當成藝術家氣息,有點名氣了或甚至只是有年紀了就對別人大小聲大小眼,完全沒在聽人講話,溝通能力低落,一點壓力就受不了,常常覺得自己懷才不遇,看到誰拿補助你沒拿到在那邊酸葡萄,看到誰票房好誰拿獎就踩到檸檬,看到一點負評就森氣氣到處情勒朋友讚美你給你拍拍,沒有主觀意識上的核心熱情白話文就是你到底對什麼東西好奇?你到底是想紅還是真的有很想探究的事物?到底什麼讓你燃燒?你可不可以問出一個沒有人問過又值得回答的問題?再來,如果又沒有對自己的客觀認知白話文就是你知道這次想嘗試什麼、想說什麼,但可以在冷靜後,客觀認知有沒有做到,有做到是因為什麼,沒做到是因為什麼,不管是能力、知識、溝通妥協結果、現實條件的限制總之不是怪在別人身上,還有你有沒有同等付出友情,擁有一群你願意傾聽也相信其判斷的核心夥伴如果以上你都沒有,那真的,找工作永遠不嫌晚,你被關了一扇窗,相信你在別的地方有一片天空(為了安撫玻璃心需要從飲料封膜上抄一些雞湯語錄,用在這剛好)。 更有可能的是,如果你個性很差,通常也不具備團體性創作的條件。但以我認識的當代藝術圈畢竟也是認識不少從業者與畫廊經營者,即便最不需要理睬大眾、只需服務少數菁英客人的藝術行業,你終究、逃不了、人、人際關係、溝通。 做一齣戲,你要面對場館、申請補助,還要會表達,做presentation,要跟團隊溝通,宣傳。如果是原創題材,你光田調就要聯繫、訪問、徵求同意,如果改編,也要面對授權窗口,讀劇、排練、演出更是會遇到第一線的回饋檢視,影視,就是把這些事情再放大一千倍,再加上更多資本市場的殘忍無情、不確定性與社群效應,而且可能還會上新聞。 這個行業最終都是要合作,僅只談論作品本身與技藝,卻完全不談如何待人處事、溝通、自省,非常虛偽,而且對創作該保有怎樣的心態也沒有實質的幫助。 很難想像需要被呵護備至、捧在手掌心的人要如何讓自己的創作愈來愈好,但,寬厚不代表隨便對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盡頭在哪裡
你想要幾歲退休?開證券戶很常被問的問題。 隨著父母年事漸高,家中有些經濟變動,兄姊也因育兒各自有些經濟難題,各自有不同被錢逼瘋的部分,這幾年開始認真研究理財,研究後開始對總體經濟產生興趣,有興趣到認識了基金經理人、全職投資者再甚至想開發金融劇我不是技術流看K線看籌碼上下廝殺,最有衝勁的還是創作,只是也認知到創作頂多溫飽,跟健身是為了創作一樣,適度地把現金做資產配置,也是一種讓創作生涯有後盾的方法,畢竟文藝復興時代都是富豪養藝術家,純藝術可以透過少數高端客層維生,但做戲劇工作,要面對重重市場(不管大眾市場還是影展市場都是市場)的考驗。跟著認識泰國、印尼、韓國、日本的影視公司,也打開了視野。 上半年殺青了自己編導的第一部輔導金短片,更加體認做創作,特別你是那個頭、那個發動者+執行者,方方面面牽涉到時間、金錢、創意與人的管理,非常高壓也非常刺激,第一關是想出一個自己有衝勁、評審或平台買單的點子,第二關是把點子執行成工作藍圖(劇本)、企劃,得到資金後,第三關就來到各種管理,精力、金錢、人跟自我的管理,透過一次次開會排戲看影片畫分鏡自我質疑確認自己要什麼,激發並相信團隊讓他們的能力得以發揮,第四關就是現場保持情緒穩定跟有效解決問題,工時12小時(含交通妝髮現場),超時不能超太久,超時費不說,第二天得要凌晨5點開始上工,由於是自己的案子=圓夢計畫=自己不拿錢,所以籌備期間同時進行例行工作,評審、投資判斷、給意見,進行不同音樂舞台劇的劇本修整討論,再加上正在寫的影集,開會6、7個小時起跳,做大量田調以及工作分配,編劇統籌也需要人事與創意管理,考量劇情角色時,同時也得判斷跟把控之後的拍攝預算,比方說哪裡有大場面,那後續集數就集中在室內場景等等。要思考的事情非常多,愈困難的事情愈讓人腎上腺素噴發,當然同時也在澆灌發想新的idea,當覺得工作好難,看一下柯波拉拍《現代啟示錄》、荷索拍《陸上行舟》、皮克斯怎麼經營的苦難,團隊創意工作本身就是戰鬥啊,沒有熱愛到讓你痛苦的就不算工作吧。 所以繞回開頭,開證券戶的時候會被營業員推銷高額退休保單,固定起手式就是「你希望工作到幾歲退休?」「希望退休後月入多少?」如此這般開場,認真想想,我從來沒有想過退休的問題,即便往後覺得想說的都說完了,也希望可以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務實且有想像力的創作
藝術學校跟電影學校不會教的就是資源管理。 正在籌備短片開拍、同時開發數部長劇集、數部音樂劇的此刻,有深刻體認。 所有的學製畢製完全不會碰觸到預算部分,畢竟是個學習歷程,換算成業界工時都是不合理的。 但在工時既要符合勞基法、成本又節節上升之下,所有製作頭都必然面對成本預算市場評估等務實問題。 朗.霍華(Ron Howard)說:導演是懂得調度資源分配的人。他也說,他的導師是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喬治跟他說,只要你的劇本跟演員夠好,並不會因為沒有按照你最理想的場景跟複雜鏡頭拍攝,就失去了這場戲該有的力量。 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說:你要習慣被拒絕。他也說,他看過最棒的電影之一,是尚.胡許(Jean Rouch)在1950年代拍攝的紀錄片《瘋癲大師》(Les Maitres fous),而他甚至沒有一般的攝影機,是手搖的,一次只能拍24秒。 一桌二椅,更是最早就有的戲曲形式,有上百齣可以這樣演完的作品。 配合勞基法跟節節上升的人事成本、製作成本,任何人想從事這個行業,都要知道你永遠都是在一定的限制下創作的,連好萊塢都會抱怨預算不夠,更何況。 然後這件事學校不會教,也不可能教,如何判斷你的創作可能所需的經費、可能面對的市場、可能國際的連結,才不會老是有懷才不遇的怨氣。「我的作品很棒!為什麼不加演!」有可能是它夠不棒,也有可能是它本身就很小眾。「我的作品很棒!為什麼不能前進國際!」有可能沒有國際的連結(我們都知道韓國如何經營它的文化外交)、也有可能這不是目前國際要的東西。「我的作品很棒!為什麼沒有票房大賣!」是否要思考電影院╱劇院的本質已改變了,美國的電影市場證明電影是社交行為,愈沒有娛樂性的作品會選擇在串流上觀賞的機會更多。「為什麼不能做短影集!短片才是創意之源!」因為平台有留住觀眾數的KPI壓力。而就算思考以上種種,你也不見得可以讓作品好,如何在創意、核心、品質與現實資源中不斷取得平衡,這才是每天都在面對資源管理的創作者,所必經的考驗。 劇集上,考慮除了超花錢的大戲大戲真的非常疲累、成本高昂,製作過程極為耗時耗力有沒有開發場景單純、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串流、短影音與實體演出
根據臉書粉專「葉郎:異聞筆記」指出:「Netflix大力道投資韓劇雖然即時解除了韓國內容業者在中國政府禁韓令後的市場危機,卻帶來了新的製作成本通膨問題。出手大方的Netflix動輒給予韓國明星兩三倍的演出費用,讓本地業者只能咬牙提高製作費用,並被迫減少製作案的投資數量來因應。如今有些韓國明星的開價已飆到1集10億韓元的天文數字,而一檔韓劇的平均預算也因此突破400億韓元的水準。反應在產量上,Tving(編按:韓國的串流平台)在2022年推了13部新電視劇,而到2023年的數量攔腰減至6個。Wavve(韓國本土串流)則是從 4部新電視劇,縮水至2023年的2部新節目。」 最近大舉進軍台灣,透過補貼大撒幣一舉成為Momo 與蝦皮競爭對手的韓國電商巨人「酷澎」,正仿效著Amazon的會員機制,將可能一舉成為最大的串流服務。而國際平台進入後拉高整體製作規模、造成預算緊繃,也早已在台灣發生,市面上起碼三、四十部賣不掉的劇不掉多少是因價碼不夠好無法cover成本,以及如果不是賣給國際平台,幾乎沒有能見度。而短影音或者社群,會成為推升觀看某部電影、書籍或者劇集的推手,「芭比海默」現象,或者日本書店出現的「#Booktok」(指在TikTok上以短影音推廣閱讀引起讀者興趣成立的實體銷售區)專區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不以「抖音一響父母白養」的角度來討論,TikTok的確可以帶起群眾參與的熱潮。幾乎可以等於說,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如果沒有在社群上成為一個話題,幾乎就很難帶來相對應的報酬,而成本極為高昂的影視產業,如果沒有報酬幾乎無以為繼,至少目前為止,也只有串流的龍頭Netflix有賺錢,但它已不需要再增加那麼多內容,就已確定得到足夠多的用戶。而對於劇場的演出,會有什麼影響呢?首先,你可以在Disney+上面看到《漢彌爾頓》的正版,也可以在 N 上面看到《倒數時刻》,一部改編自《吉屋出租》(Rent)劇作╱作曲強納生.拉森(Jonathan Larson)的音樂劇電影,甚至,你可以在專注於同志影音的Gagaoolala上面看到我與前叛逆男子劇團合作的 2019年版本《新社員》,串流要打開群眾,當然就得在多元與主流中取得平衡。當然,關於二倍速觀看是否已成常態、比起追劇更在乎自己的時間成本,甚至不怕被暴雷,暴雷反而更增加觀看意願等等,已經有非常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來訪的遠方
總統大選前,有兩位特別的朋友來訪問我,特別來觀選,為了保護她們,個資會模糊處理。 她們是來自對岸的朋友,《人選之人》的觀眾,其中一位喜歡閱讀,很早就讀過我的戲劇劇本。另一位,對政治跟社會改革非常有興趣。 她們在歐美留學,兩人背景不同,一個家中靠近公務體系,一個靠近市場,但都不約而同地,或因為霸凌、或因為性向,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幻滅,不管是身為女性、身為性少數,或面對審查,而再怎麼家底高於他人的人,都特別在疫情期間感到幻滅,「我20歲的時候感受到了一個存在主義的危機。」來訪的友人說。直接把你鎖在家中數個月,甚至用鐵鍊把你鎖在家中,像動物一樣地搶著物資,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求助無門。 我想起我在北京做小劇場跟寫小說的好友,前幾年跟他通信時,他說,審查愈來愈嚴格了,一開始是交劇本,後來是交排練錄影,再來是現場,要一字不差。 這樣要怎麼創作?有好多戲就不能演了,那得怎麼辦?不曉得,不知道,這樣還能創作的,我都深深敬佩。 還有曾經在深圳駐校教戲劇,遇到一位學生,我會一直記得,他來找我的那個下午,支吾再三,說有一件事想跟我說,但又起身,逡巡一週,到處檢查頭上有沒有監視器,確定整個教室都沒有,才開口跟我出櫃,如今,他也在國外,正在學習表演,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 以上幾位友人,都想盡辦法要留在國外,只有北京的朋友,說,雖然想走,但也不知道要去哪,創作與表達,如果跟所在之地斷了連結,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台北的書店是天堂。」來訪的友人說,她們買了好多好多書。 「我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但我們參加支持巴解的活動,都要戴帽子口罩,因為大使館會派人來看,會參加這類活動的通常都會特別被注意。」互相提醒、參加這類活動要蒙面、隱蔽身分已是常態。 「家裡以為我學的是一個有用的科目,但我其實唸的是政治。你知道嗎,辛亥革命前有個女性政治家,很早就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理想的世界,跟一百多年前她提出來的居然差不多,很可惜的是並沒有發生。」 那為什麼特別來找我呢?她們說,這是政治代餐,常常透過韓國或台灣的作品來「代餐」,但聽到中文講出來,衝擊力又更強,她們感受到政治是一種日常,感受到戲劇可以跟自己有關。 「你們那邊還是有很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去看了喜劇表演
11月24日在朋友的邀請下去看了卡米地站立喜劇爭霸戰台北場初賽,看了12名演員的演出,意外還蠻有趣的。特別是編劇友人Birdy(編按:馮勃棣)的演出又喪又好笑,難怪憂鬱症,比他的劇本好笑(這是開玩笑)。 站立喜劇╱脫口秀並沒有被納入表演藝術的討論中,的確很難納入,發展脈絡與表演邏輯都不大一樣,我從自己體感來定義,可能可以拉出這個光譜(幾乎沒在看音樂演出就不列入): 專家 觀眾 舞蹈 戲曲 舞台劇 音樂劇 喜劇 </tabl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減低生活負擔
最近工作耍廢的時候很喜歡看一個IG,叫「outstanding.screenplays」,節錄了如艾倫.索金(Aaron Sorkin)、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奉俊昊、黑澤明、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等優秀Writer的名言佳句,此刻的我就是喜歡IG金句來告訴我創作是什麼!腦袋塞爆看不下太長的文章,只想看迷因跟人生指引!我想他們一定也是在許多許多許多許多次媒體跟教學的詢問下,一次一次擠出到底Writing是什麼?雖然貼文的重複率很高,算起來大概10要掰幾則新的也不是不行但他就不要你一點開,就好像那些重複但又踏實的提醒:「天氣熱要多喝水」「天冷要穿外套」「見面三分情」「個性決定命運」,而且用大寫英文寫,內容又讓人會心一笑,可信度更高。 今天很悶,看看菲比說了什麼英國劇場╱影視演員、製作人、編劇菲比.沃勒-布里奇,我們粉絲都暱稱菲比,她說:AS A SCREENWRITER,YOU NE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ALONE.WRITERS IS NINETY PERCENT PROCRASTINATION. 看到我笑出來,當然是先去查Procrastination這個單字的意思才笑嗯原來是拖延。 對!90%在拖延,超有共鳴。 以前受訪常常會擺拍用電腦、在筆記本上創作的樣子,那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時間可能是打開冰箱,打開廚房櫃子,打開line群,打開行事曆,焦慮我為什麼要答應這個答應那個,開始查資料,Google「台灣稻米 最受歡迎」,台梗9號?還有什麼?8號16號,怎麼命名的?為什麼不取個像日本那樣很美很好行銷的名字?然後就花了一個上午在看稻米的資料跟影片,更多時候就是,你也不知道為何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可能只是執行了一個「刪掉手機裡面用不到的app」的動作 所以,長期下來,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生活負擔減到最低,畢竟工作就要花很多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主旨…大綱…分場?
最近在準備一個小說與漫畫的創作工作坊,教一些編劇方面的技巧,但每到準備的環節就覺得頗煩惱,因為實在很難說出什麼一以貫之的技巧,翻來覆去看書講的也是大同小異,可以比較被系統化的談就是三幕劇、平田的獨幕劇、角色就是「目標跟阻礙」,但我自己遇到的工作模式常常也不是來來來先想好你要探討什麼,接著就會順利進行,主旨會是「一見鍾情的年輕男女因家族世仇而無法在一起最終殉情」嗎?還是「多愁善感的王子發現父親過世的真相而裝瘋賣傻發現真兇是叔父最終復仇成功?」,在可以心無旁騖地只討論主旨之前,有太多東西要處理了,主旨常常都是最後才被整理出來的東西,與其說技巧呢,不如說是「把關東煮做好了但發現手上的材料只能做咖哩,那就做成咖哩而且不要把咖哩視為阻礙」的能力。 比方說最近要收尾的韓劇改編,因為台灣的預算怎麼樣都不可能追上韓國,所以可能無法那麼耍帥、那麼炫、那麼潮,那就「稍微寫實一點吧」,「稍微寫實」簡直搞死人了,太痛苦了地獄人生,隔行如隔山有夠難;又比如,《人選之人》一開始是設定主角們是同學、大學異議性社團,過不多久確定謝盈萱加入,得因應她的年紀去調整設定,所以從27歲提到快40歲,所以政二代、所以當選過一次議員,因為某個原因而落選,但政二代嚴格來說不太可能落選只是議員耶,是以她跟樁腳究竟起了什麼衝突?打樁腳會不會太誇張?要給她一個合理的動機沙盤推演了許久;也如同跟謝的另個合作《服妖之鑑》,一開始收到製作人的邀請是改編《杏仁豆腐心》,但我沒有很喜歡這個劇本,說實在不大明白前幾年為什麼一直演不喜歡的點是覺得「避而不談的點原來是小孩流掉無法做愛」鋪陳太搧情又太往一個想當然耳的方向去推,畢竟是2000年的劇本,很推薦烏烏醫生討論流產的觀點,不管討論什麼總是要加入點當代觀點吧,當時覺得關係的狀態很死,改編上沒有什麼空間,後來就想,從盈萱身上出發,讓她反串,只反串又太簡單,就演一個有扮裝慾望的男性,怎樣可以更有衝突?設定成警察,現代社會警察扮裝也還好吧,那放到以前,白色恐怖時代,這樣衝突可以達到最大!現在寫起來一兩行字而已,但當時是層層推演跟燒腦的過程。又比如《新社員》,一開始是漫畫《同級生》,但漫畫太散文了,衝突太少,很難做成戲劇跟音樂劇,當時就參考了《仲夏夜之夢》,如果不是「倒敘」類的結構(如《伊底帕斯王》),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最近走路去洗頭
影集4月28日上架後幾天,剛好去動了一個不大不小中手術,後續一週都得在家中靜養。 因為我不能洗澡只能擦澡,自然也不能洗頭,我會走路去洗頭,5上旬的陽光很好,氣溫宜人,有風吹在身上,大概維持三天洗一次頭。附近的小林髮廊,白天他們冷冷清清沒啥生意,洗一次兩百五,雖然想找更便宜的,但生理上也無法走更遠,反正想說洗頭附贈按摩。平常就試圖在家裡工作,對,試圖,實際上我根本做不到,畢竟在戲上架Netflix的連假,不關心根本不可能。 剛好也是在這週,《人選之人》開始各種社群洗版,本來就會看觀眾心得回饋,開始刷各種平台的心得文,豈料迎來跟劇場截然不同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了,串流平台可以觸及的觀眾好廣。 臉書、IG、PTT、Twitter、微博、YT,要刷完真的不可能,一方面看著各種熱評,一方面因為消炎止痛藥而一天得拉好幾次肚子,真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想起之前看過《麥蒂為何而跑》,討論在IG上展現完美的運動明星孩子,然後自殺了。我們有討論青少年面對網路壓力的書,但應該沒有講成名後怎麼面對網路壓力的書吧。 不過幕後的壓力永遠不及幕前。 想起之前跟一位演員朋友吃飯,收到一些很煩人的IG訊息時她會一邊點開,一邊murmur世上怎麼有這樣的人,我很訝異她會看私訊喔,她說有時候就點開,但還是會好奇想了解一下別人要跟自己說什麼。 有時候我也會蠻好奇其他人怎麼看待自己的作品,你在創作它時的那種珍貴跟私密的感覺,讓你覺得自己跟某些事物有很深的連結,特別是在劇場,你看到一些場景,一些動作,一些人跟人之間微妙的流動,你跟團隊們非常靠近,也會在演出後跟許多互相信賴品味的朋友們聊戲,持續跟夥伴們聊戲,好好把這齣戲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部分收在心中;但影集播出時,距離拍攝完成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大家都各自四散去做不同案子,然後在短時間內得到大量關注,當它被評論,被摘錄金句,被做成圖卡時,你又覺得這些跟自己好像無關。 不過想想自己有時也會被網路上看到摘錄的電影金句圖卡觸動。一塊好的牛肉不管做成煎牛排還是漢堡,都是好吃的吧。 你需要有類似經驗的朋友,你需要有可以分享這些事的人,「你怎麼看待短時間內對你作品的關注?」我常常看到報導上有人問一些爆紅新生代歌手演員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