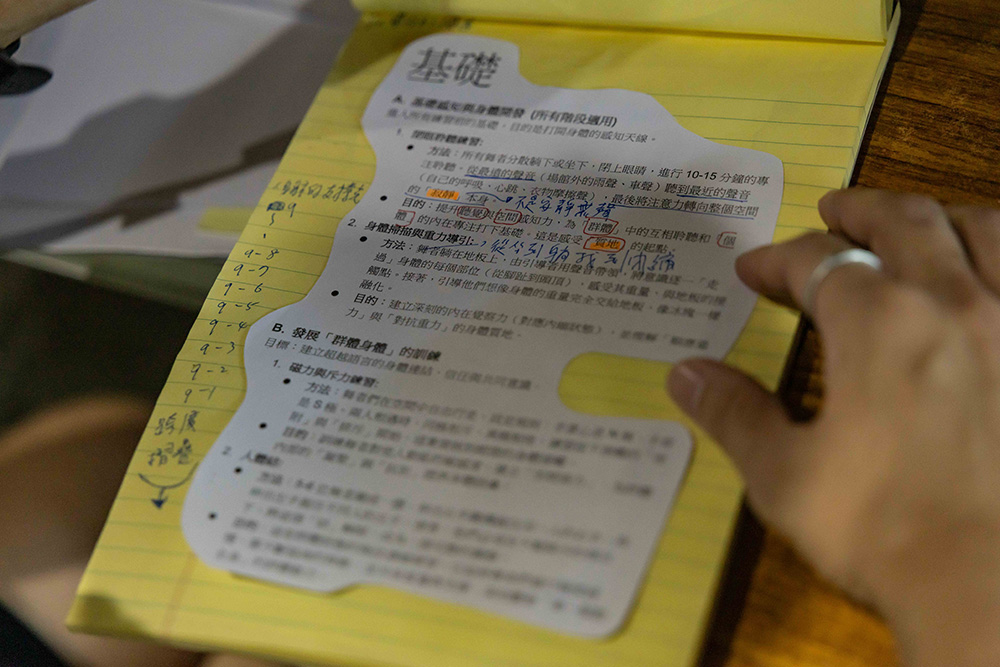8月底,TAI身體劇場位在花蓮新城保安宮旁的鐵皮工寮,一股騰騰熱氣盤桓不去,儘管稍一動作,汗水就會爭先恐後噴發,舞者們仍一臉平靜和煦,把身體往黑膠地板挪去。
Piya Talaliman李偉雄、Qaulai Tjivuljavus奧萊.吉芙菈芙斯、lrimilrimi Kupangasane巴鵬瑋、lsing Suaiyung朱以新,以及新加入的舞者王秋茹,以各自的節奏和方法,在濕熱的空氣中暖身。不多時,負責今天排練指導的Piya往右下角落移動,以「腳譜」練習開始第一階段的排練。
看著舞者身上晶亮的汗珠很快將他們背部浸潤為一道光滑平面,黑膠地板上也流淌一道道水漬,我不禁發出一聲小小的驚嘆。編舞家瓦旦.督喜轉過頭來,安撫一般說道:「現在很熱,可是只要一過4點就會開始有風吹進來,傍晚還會變冷呢!」儘管氣候變遷讓夏季一年長過一年,工寮裡的他們依舊能鮮明察覺季節。
我的驚嘆倒不是疼惜舞者溽熱中大量勞動,以致汗水奔騰如瀑,而是一個念頭豁然浮現:在這個追逐效率愈發高速的世界裡,舞者恐怕愈來愈接近瀕危的存在。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瘋狂加速的世界中,身體能嫻熟穿梭於現實和想像之境的舞者,或許會成為未來人類的關鍵物種——當多數人類被城市文明所馴化,慣於待在乾淨明亮、無臭無味、清爽整潔的空調場所,且為了確保這種潔淨無菌,身體與身體最好不斷延長社交距離,確保廓清身心界線;與此同時,不畏濕黏肉身交纏,無懼彼此汗水交融,膽敢把身體拋進濃郁、稠密、潮溼、陰暗、搔癢、疼痛,勇於嘗試多樣的感官經驗,因而有倍於常人的身體和環境適應性……這樣的舞者,面對未來變數難測的地球,豈不比我們更多生存勝算?
100公里俱樂部歷年里程
2018 花蓮市—花蓮富里
2019 花蓮富里—臺東土坂
2020 臺東土坂部落—屏東來義部落
2021 屏東來義部落—台南吉貝耍部落
2022 台南吉貝耍部落—臺中市
2023 臺中市—桃園楊梅
2024 桃園楊梅—基隆市
2025 基隆市—宜蘭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