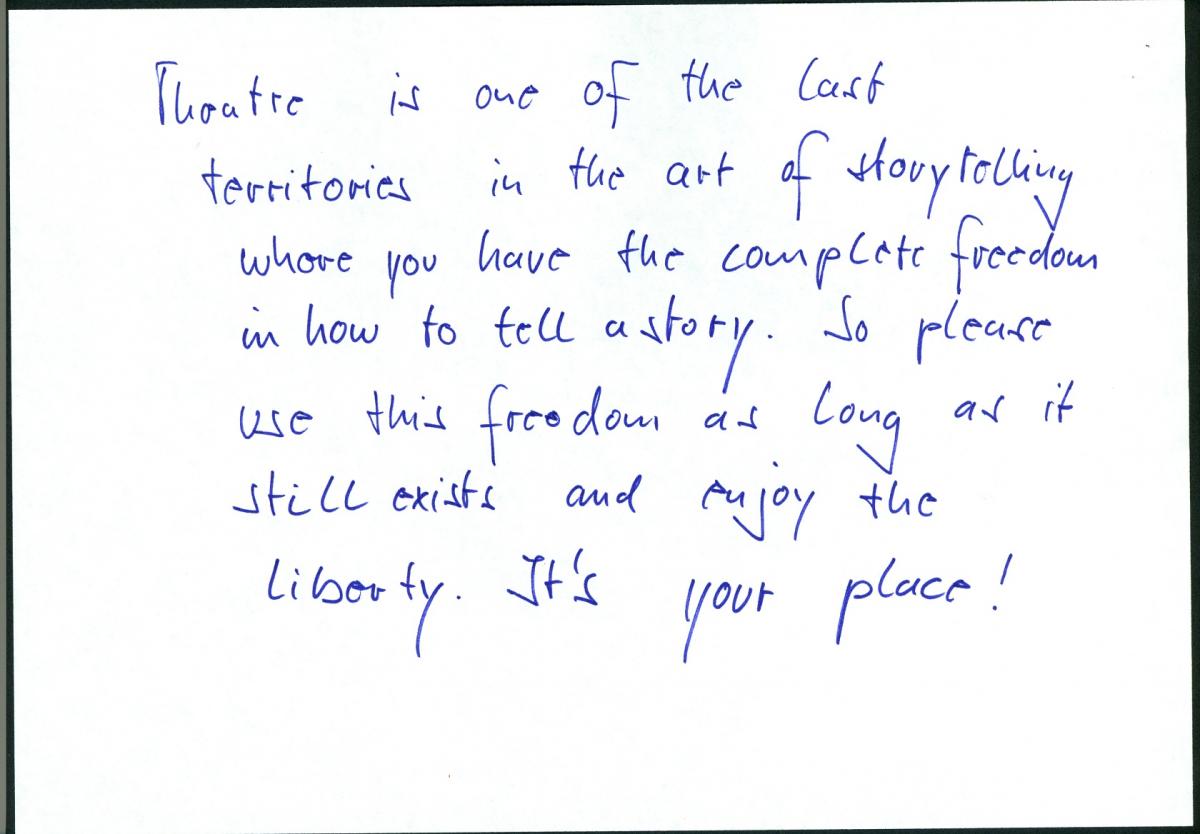歐斯特麥耶
-
 戲劇 我為人人,人人覺得我瘋了
戲劇 我為人人,人人覺得我瘋了《人民公敵》 在後民主時代演練公眾討論
當今劇場形式多變、題材紛雜,有誰能讓世界各地劇團不斷回頭搬演?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絕對名列前茅,在德語劇場也不例外。 以選出德語圈年度十大作品的柏林「戲劇盛會」(Theatertreffen)為指標,60年來累計搬演易卜生的節目高達29齣,且數度同年有兩部不同劇院製作的作品入圍。能超越此紀錄的,目前只有莎士比亞和契訶夫。 易卜生被視為「現代戲劇之父」,不僅因為其作品開啟口語劇場的新頁,也來自普遍認為他對角色心理刻畫的深度。然而,這般深度也彷彿設下一道道謎題。 在德語圈,搬演易卜生榜上有名的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就表示,德國的導演劇場在1970到90年代興起時,搬演易卜生往往變成在「揭露靈魂的秘密」,卻因而讓角色失去了行動。當歐斯特麥耶踏入易卜生的世界時,他發現人物靈魂不是故事源頭,錢才是,「這些角色都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易卜生總是用經濟壓力當作劇本的動力來源。」(註1) 也就是說,劇情不是單純因「角色怎麼想」而發展,而是建立或限制了他們物質生活的家庭關係和社會網絡,影響了「角色怎麼做」。換句話說,在歐斯特麥耶看來,大家對經濟成長有多著迷、對衰退有多害怕,易卜生就多「當代」。他2012年帶領柏林雷寧廣場劇院(Schaubhne am Lehniner Platz,亦譯為列寧廣場劇院)於亞維儂藝術節首演的《人民公敵》,就緊扣這個觀點。
-

北京禁演的易卜生經典 《人民公敵》辯證「圖利」之罪
臺中國家歌劇院2024「遇見巨人」系列開幕大戲、柏林雷寧廣場劇院《人民公敵》即將於10月25日至27日在中劇院全台獨家登場。由國際劇場金奬導演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改編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Henrik Ibsen)同名劇作,2012年於亞維儂藝術節首演後好評不斷,後續在德、法、英等30多國巡演。2018年在中國北京演出時疑因與觀眾互動橋段觸碰政治敏感神經,後續演出遭刪改甚至取消,真成了「人民公敵」。
-
巴黎
作家親自登台微觀自我 歐斯特麥耶新作逼視社會矛盾
法國全新表演季在疫情肆虐下展開,每個劇院都戰戰競競。許多劇組只要有一人疑似感染,就馬上中止演出(註1)。觀眾看戲也全程戴口罩,避免咳嗽,以免成為眾矢之的。儘管諸多限制,但觀眾依舊熱情不減,讓多部製作一票難求。德國導演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與法國作家路易(douard Louis)合作的《誰殺了我父親》Qui a tu mon pre便是本季開幕叫好叫座的演出之一。
-
A Bigger Picture
戲劇,是放大鏡,還是顯微鏡?
歐斯特麥耶的《義大利之夜》在我看來很有意思的,是四個女性角色所反映出的一個共通點:男性和他們想像中的自己,與女性在跟他們相處之後所認識的他,可以不是同一人。而「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不止存在於兩性之間,也是政治常常面對的無解,甚至虛偽所在。
-
巴黎
與法蘭西戲劇院合作 歐斯特麥耶《第十二夜》狂歡搬演
受到近年來保守勢力在歐洲崛起所影響,德國知名劇場導演歐斯特麥耶想要重探《第十二夜》,呈現莎翁怎麼透過風趣的筆觸,突顯超越性別框架的慾望。這三年來,他在巴西、羅馬和柏林的導演工作坊中與大學生一起探索此劇情節,近期並與法蘭西戲劇院新生代演員合作搬演,透過符號的拼貼與錯置,不僅突顯劇中的扮裝橋段,也顛覆了大家對於性別和身分的既定認知。
-
北京
《人民公敵》事件 政治戲的政治後果
九月上旬,德國柏林邵賓納劇院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歐斯特麥耶執導的易卜生經典《人民公敵》,其中一場與台下觀眾互動的橋段,因為觀眾的發言觸動了政治敏感神經,引發後來幾場刪戲、接著南京演出取消的狀況。這個事件也引起德國駐華使館和歌德學院的關切,不過,很多人的疑問則是,在國家大劇院發生這麼敏感的事,是審批出了什麼問題嗎?
-
焦點專題 Focus
讓人又愛又恨的主角 一場慶祝邪惡的派對
由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製作,藝術總監歐斯特麥耶執導的《理查三世》首演於二○一五年,由該劇院當紅演員艾丁格擔綱主角理查三世。相信人性本惡的歐斯特麥耶,以「理查之惡,人人有之」為創作出發點,「塑造一個人物,他的壞居然帥到讓我高興、愉悅」,更在劇場中透過與觀眾的近距離互動,讓觀眾成為理查奪權的「同謀」,如同共同參與一場慶祝邪惡的派對。
-
藝活誌 Behind Curtain
那有王子不照鏡
正是在他認真地玩著「我不能輸」的遊戲時,我恍然明白《理查三世》近年在莎翁劇作中名列「最受歡迎排行榜」前茅不是沒有原因,理查三世的悲劇,就是現代人最能認同的悲劇:沒有被人慾望的外表,就不會被愛;不會被愛,便等於沒有價值;沒有價值,又為何要苦苦與生存摶鬥?要與生存搏鬥,唯一辦法,就是寧可扭曲內心的自我,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外表醜陋 。
-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十四台大戲 六大單元、三地上演
從二○一○年起,由中國戲劇大師林兆華以個人名義發起的「林兆華戲劇邀請展」,今年已然來到了第七屆,以「每個人和它的命運」為主題,邀請了列夫.朵金、克里斯蒂安.陸帕、歐斯特麥耶等歐陸名導參演,推出六大單元、十四齣大戲,分別在北京、天津、哈爾濱三地演出,可說是中國劇界一大盛事。
-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邪惡的雙重向度
由德國名導歐斯特麥耶執導、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的明星演員拉斯.艾丁格主演的《理查三世》,於今年二月初首演,備受媒體與劇評人矚目。濃縮為兩個半小時的《理查三世》,可說是艾丁格的獨角戲,他刻意改變身體形狀「扮演」這個邪惡的怪物,反而引發觀眾的認同,進而產生憐憫的情緒。歐斯特麥耶強調,「扮演」與「偽裝」正是莎劇中經常碰觸的核心:我是誰?人類又是什麼?
-
特別企畫 Feature 德國:發展概況
從日常中挖掘悲劇 形式與內容層層呼應
英國新文本浪潮在德國劇場界亦引發深遠影響,由導演歐斯特麥耶大力推動的「新寫實主義」,為當代劇作家打造了舞台,強調關注「平凡生活的悲劇」,以與當下世界密切連結。知名劇作家如梅焰堡、希梅芬尼和洛兒等,共通點即在於形式上的實驗與內容往往有多層次的對應,在挑戰如何搬演的同時,往往也回應作品的主題意涵。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重生經典、與當代同步——列寧廣場劇院
雖然歷史不及其他劇院悠久,但成立半世紀的列寧廣場劇院卻以多部精采製作,在德語劇壇享有重要地位。前有大導彼得.胥坦為劇院奠定對文本提出新詮釋、以銜接當前社會政治議題的優良傳統,近期則由現任藝術總監歐斯特麥耶以獨特的新寫實手法搬演經典與當代劇作,屢屢讓劇評人與觀眾大呼過癮!
-
 新藝見/新銳藝評
新藝見/新銳藝評一場共同追尋劇本現代意義的旅程
我曾猜想歐斯特麥耶運用悲喜交替的節奏、俗雅雜交的語言,可笑卻能傳遞精神困擾訊息的肢體動作,將會提高刺激觀眾獨立思考運作的可能。雖然我不確知每個觀眾的答案與心理反應,但起碼透過劇作、演員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我看到的不僅只是文本和角色詮釋,而是在觀看與被迫思考的過程中,轉而發掘屬於個人、對於這世界的體認與心理真實。
-
 達人推薦 本月我想看
達人推薦 本月我想看驫舞劇場《M_Dans2010》、歐斯特麥耶《哈姆雷特》
相對於驫舞每次那些混亂卻充滿能量與機鋒的集體即興創作,但對我而言,其實他們每位編舞家各自的獨立作品,都更精準銳利。終於他們願意用集錦方式呈現各人風貌,我以為這樣衝撞出的藝術張力,或許更為強勁。 歐斯特麥耶的《哈姆雷特》是較《玩偶之家》更具野心的作品,也絕對是世上萬千復仇王子當中,最讓人難忘的版本之一。光看開場的瘋狂葬禮滑稽劇,就已值回票價。六人不換裝兼任多角的處理,將劇本的角色內在意義梳理得更為突出,讓人想起這次的劇本修編馮.梅焰堡在他自己的《醜男子》當中類似的戲劇手段。黑暗嘉年華般的情境氛圍,暴露扮演成分的劇場美學,在在彰顯這個時代的藝術與現實氣質。歐斯特麥耶的版本不是沒有值得斟酌計較之處,然而他的膽識,已足為下一世代的藝術家取法。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前浪大破大立 後浪威名遠揚
德國當代劇場不墨守成規,大膽的實驗精神、勁爆的表現手法、精巧的舞台設計,讓歐洲其他國家欣羡不已。而這豐碩的果實,不能單純歸功於新生代的創作能量,畢竟若無前人對戲劇鞠躬盡瘁般的熱情付出與努力耕耘,以及國家持續地投注文化資金,德國的導演劇場恐怕也不可能在新世紀叱咤風雲,走在歐洲諸國的先端吧!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歐斯特麥耶:我想打破詮釋《哈姆雷特》的一貫傳統
曾於二○○六年率領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訪台演出《玩偶之家─娜拉》與《點歌時間》,讓台灣觀眾驚嘆驚艷的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將在三月下旬帶著《哈姆雷特》,來給台灣觀眾一個全新的莎劇體驗。趁此機會,本刊專訪了這位年少竄起、迄今依然引領風騷的德國導演,一談他執導《哈姆雷特》的想法與對自身創作的分析。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消逝中的藝術
真的是依依不捨地送了十一月,真的。 因為在上個月,各式演出的節目之精采,實在不是短短地幾百字能夠形容。從兩廳院主辦的 「德國狂潮」到廣場藝術節、與明華園合辦的歌仔戲《何仙姑》、北藝大的莎劇《威尼斯商人》、創作社的《不三不四到台灣》、還有新象文教基金會遠從天際邀約 而來的高亢雄音《蒙古草原傳奇》不勝枚舉,令人目不暇給。 雖然本刊之前已經做過不少介紹,但對於親臨現場欣賞演出的讀者來 說,都還是 會與我們有著相同的感覺:那種震撼與體會,仍是無法用文字或照片全然表達清楚。因為這就是「表演藝術」的迷人之處,你必須成為觀眾、必須成為演出的一部 分、必須與表演者一起完成表演藝術創作的最後一步謝幕!表演藝術和其他藝術創作之不同,也在於此,觀眾是完整藝術創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為,它 是「消逝中的藝術」。 其實,由身為劇場人到出版人再轉為媒體人,我發現新聞工作也一樣,也是帶著某種「消逝中」的悲劇性格,雖然我們的某 部 分工作是在發掘、在記錄。記得一位老記者曾笑著跟我說:「今天早上再了不起的頭版新聞,到了明天,還是逃不掉被人拿去包便當的命運」但同樣地,這也是新聞 工作的迷人之處。它與其他文字工作的差異、與表演藝術相同的也是:讀者/觀眾的參與程度。編輯部最小的心願就是:您看完我們的介紹,買了票、走進劇院、被 一場演出所感動,或甚至決定日後參與演出創作。香港導演林奕華說:在劇場裡、在兩個小時黑暗不說話的時空中,他希望幫觀眾設計跟建構一個自我對話的過程。 而我想我們的工作就是:成為你與自我對話過程開始的那個推手,當然,也可能還涵蓋著之後的「心理分析的輔助」角色吧! 既然要做到稱職的 「心 理分析輔助」,就是要協助您能更了解你所看的表演。本期編輯部就特別針對了剛閉幕也是最熱門的獨角、獨幕、無對白的劇作《點歌時間》,做了演出中收音機音 樂的解碼分析。而針對在欣賞之餘、還想更進一步創作的讀者,我們也趁著導演歐斯特麥耶來台的機會,請他為台灣的戲劇工作者推薦十部當代劇作家的優秀劇作 (如右列),希望能藉由本期的披露,能為台灣的戲劇界發掘更多好的文本,創造更多可能。 可是,表演工作者的創意只限在劇場內嗎?當然不是!本期「藝活誌」也乘著耶誕氣息,帶您走進藝
-
藝號人物 People 給我戲演,其他免談!
劇場痴人 魅力女優—安娜.蒂斯摩
「我在劇場裡所呈現的,是現實人生中我不會去做的。在這裡面,只有我自己的堅持。」舞台下極其羞澀瘦弱的安娜.蒂斯摩(Anne Tismer),上了舞台後卻爆發力十足,有如巨人。十月由她領銜演出的《點歌時間》與《玩偶之家娜拉》,迷倒了一拖拉庫的觀眾,說不定,她已經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有資格在台灣組織劇迷會的歐洲劇場演員。 與她攜手創作娜拉奇蹟的導演歐斯特麥耶形容安娜‧蒂斯摩是個有劇場依存症的演員,對劇場藝術有絕對的渴求,舞台上的她所跟隨的,是只存在她雙眼的那道光,觀眾的反應與其他事務都不會打擾或影響她的演出。劇場是她的烏托邦,在兩廳院十月的德國狂潮系列節目中,她與她的烏托邦震懾了全場的觀眾,在本篇專訪中,她將打開烏托邦的大門,讓喜愛她的台灣觀眾一探內中風景。
-
歐洲人文筆記
那些年,娜拉是怎麼活過來的?
葛茲與許多偉大的作家一樣,都是無可救藥的偷窺狂,《點歌時間》的誕生也是出於偷窺欲及幻想。他關懷女性和中下階級人物是出自真心,而非他的社會屬性,幾乎有布萊希特的高度,只不過他沒有布氏那麼有名,他也有海明威的氣質,男性、陽剛、永不妥協,只不過他沒法把自己一槍射死。
-
 常客推薦 本月我要看
常客推薦 本月我要看《點歌時間》
而生活永遠是無法逃遁的牢籠。 日常生活歷過種種囂嚷、靜寂、昇迭、淡瘠、滅幻,終將沉默為自我的孤存,而最後面對的永遠是自己。淡若無覺底常習,在某些時刻總要增殖為無限巨大的迫力,一點一點折蝕生命。 做著常務的主角拉許(Rasch),在無言底生活裡無能為力,而《點歌時間》終究無法慰解註定只能自視底靈魂。 或者,不用懂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只要活著,彷彿就可以懂得這生活逼視的懾人。 文字|賴譽夫 28歲,廣告系畢。出版社編輯/業餘歌者、樂手/寫作者/複合媒材創意作者/乙組棒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