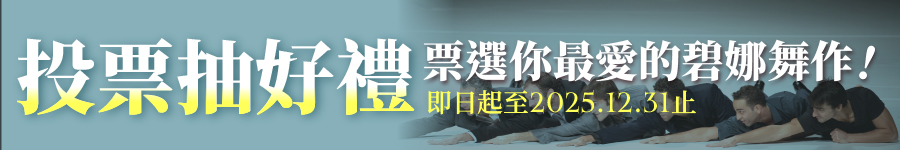小劇場
-
專題報導
成長的印記
《動物園的故事》是梁志民在大學時期的畢業製作,後來除了在蘭陵劇坊加演外,還巡迴至中南部演出。走了十年多,爲了回顧,也爲了重新開始,果陀劇場應兩廳院之邀,將以果園劇場的名義推出第一齣戲《世紀末動物園的故事》,參加「小劇場經典名作回顧展」的演出。
-
 專題報導
專題報導執著劇場 純爲樂趣
第一次看到《寂寞芳心俱樂部》的劇本,陳培廣就「非常有感覺」,因此當劇院提出「小劇場經典名作回顧展」的計畫,在考量各種因素後選定《寂寞芳心俱樂部》時,導過大、小劇場的陳培廣也欣然同意,因爲所有作品中,他最有感情、最想再做一次的也是《寂寞芳心俱樂部》。
-
回想與回響 Echo
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
綜觀全書,作者若能取如《台灣現代劇場論》之書名代以《台灣小劇場運動史》,或許就不會讓人強烈的感受到一位「啓蒙進步主義」者卻持以唯心論的批判立場,那麼作者也不至於因爲對「否定的解釋學」的意識形態批判產生一種憎惡。
-
專題報導
實驗劇場的劇場實驗
位於國家劇院三樓的實驗劇場,十多年來提供了國內年輕創作者一個演出的舞台,在台灣小劇場的發展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近幾年來,由於台灣表演藝術環境的改變,實驗劇場在軟體及硬體設施上,都做了一些新的安排。
-
現象視察
催生一場硏討會
要了解此次硏討會的緣起始末,就不免會把焦點集中在此次擔任承辦單位的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本刊訪問到系主任廖美玉與籌備委員馬森詳盡地描述了催生的過程與其對此次硏討會的觀察和回應。
-
現象視察
背負與跨越
當我們目睹且參與了台灣現代劇場在二十世紀末最後的一場硏討會之後,即便許多要求與期待硏討會修正改進的聲音此起彼落──諸如硏討會的主題分類與命名、論文的蒐集對象與順序安排、論文講評人與發表者組合的適當性,甚至是論文發表與講評討論互動交流的時間分配等技術細節等等;然而,也肯定了劇場/戲劇活動在台灣的歷史價値體系上需要不斷地被重新思考的事實。
-
 專欄 Columns
專欄 Columns被迫的喜悅心情
抱著被迫的喜悅的心情,我經常會有一些意外的發現,有些發現還能澄淸自己的錯覺。一個硏討會的成功,不是只求答案,而是能夠激發辯論,提出値得深討的問題、分享經驗和「英雄所見略同」的發現,或是因挑戰而互相認識。
-
 里程碑 Milestone
里程碑 Milestone紀念葛羅托斯基 1933.8〜1999.1
被喻為二十世紀四大戲劇家之一的耶日.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在六〇年代中期以「貧窮劇場」的理論與實踐震撼了歐美前衛劇場界;七〇年代以後,葛氏便投入探究「生命」昇華的可能。國內劇場工作者劉靜敏與陳偉誠曾參加他於一九八三至八六年間於美國加州大學爾宛校區舉辦的「客觀戲劇」工作坊,之後並將葛氏的訓練方法與貧窮劇場理論引進國內,對台灣小劇場發展初期在訓練方法上有極重要影響;至今不僅在台灣,在歐美其他國家仍有其追隨者依其訓練方法與精神,進行劇場訓練工作。葛氏於一月十四日卒於義大利,本刊為了紀念這位對台灣劇場極具影響力的大師,特別企劃了「紀念專題」,邀請曾參與葛氏工作坊的劇場工作者及對葛氏理論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撰文探討葛氏對台灣的影響、葛氏理論的深入探究、葛氏學生對他的感懷以及國外對葛氏研究的研討報導等,「紀念專題」將分上、下兩期刊出。
-
回想與回響 Echo
在我們故鄕的永恆廢墟
一九九八年,在一場名爲「虛構飛行」的演出中,熟悉黎煥雄劇場的觀衆,在拆開一封寫給不定人稱「演員S」的信的同時,也收到一封寫給過去劇場的信。重逢其中風采依稀的河左岸語句:覆沓的記憶的圖景、迴環往復的語言與意識的倒影,將斷裂的往事重又接續起來
-
 專欄 Columns
專欄 Columns歷史脈絡中的小劇場
小劇場的定義爲何?從六〇年代的李曼瑰起,「小劇場」這個名詞就一直被延用至今,但它的意義卻不斷地處於飄忽不定的狀態。如果說「小劇場」的定義是反傳統、反中產階級、反主流文化、反資本主義(這是套用西方的定義,同時也是個人比較傾向的說法)。那麼,台灣眞正的小劇場要一直到解嚴前幾年才發生。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五月,一個劇場能量很高的月份
五月初,「現代劇場硏討會──台灣小劇場1986〜1995」連續四天在台北舉行。會中進行了論文的發表、座談、及交流會報。 如果說硏討會爲「小劇場史」進行了耙梳整理的工作;那麼,國立藝術學院以台灣史爲題材,融合說唱、民俗,在五月推出的《紅旗.白旗.阿罩霧》,則是爲以台灣史爲議題的劇場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基礎。 《表演藝術》雜誌在這兩項「劇場的歷史」、「歷史的劇場」事件發生過後,分別舉辦了兩場座談會。我們在會中發現,這兩項議題的討論都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劇場的觀衆在哪裡」、「劇場的精神」、「劇場與體制的關係」等問題。 五月似乎是劇場能量很高的月份,在打開更多的討論空間之後, 希望劇場的理論與實踐能產生新的面相。
-
 專欄 Columns
專欄 Columns集傳統之大成,開未來之新端
其實,所有開新端的作品,也並非完全抛棄傳統,毋寧是在旣有的成績上針對某一方面予以創建、革新。要想集大成,首先必須對過去的傳統有所把握才成。我們也有一個不薄的傳統,除了將近百年的現代戲劇之外,還有數百年的傳統戲曲及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地方戲曲在那裡,再加上我國現代戲劇所繼承的那一個久遠的西方傳統,這一切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西方的當代新潮。
-
戲劇
台灣的小劇場不再後現代?
「開始是夢境,從柏拉圖說起,說的當然是愛情,年輕人的那種。一群人就捉起鬼來了,有人不玩。整群人介紹了自己的角色與性格,然後有人表白,於是我們得知了一個愛意的開端。在一種習慣性要知道這個愛情「結局」的慣性下,開始了被表演不停干擾的閱讀過程。」
-
 活動看版
活動看版台灣劇場硏討會宣言
饗宴,就要開始。 爲什麼要有這樣一場以「小劇場」爲主體的硏討會? 因爲以前沒有。現在,我們要它有,它就有了。 多少年來,多少滿懷理想的熱血靑年──這種形容詞聽起來似乎很古老,但事實的確如此──奮身投入他們不明就裏的「小劇場」中,等到短暫的潮紅從臉頰消褪,大家才睁大眼睛: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自己鬥!除了充血的腦袋,你能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雙手。 這就是「創造」的神力! 有些人馳如彗星,光華耀於一瞬;有些人細似流水,精技而進乎道。不管是焚心於自創,或極目於西方,在「台灣劇場」這塊小於或等於無的土地上,總是竄動著小劇場人橫衝直撞的力,終究綻開一朶朶土產的奇花異卉。只是這些花卉缺乏養份,太容易就凋落了。 「時間」對小劇場也不公平。現在大家談劇場,言必稱蘭陵,因爲「蘭陵劇坊」是扭轉台灣劇場轉向現代劇場石破天驚的一擊,小劇場再怎麼發勃,總在它之後。另一方面,逐漸興起中的,由學院戲劇系和商業劇場(以票房爲主的劇場)合構的主流劇場卻尙未繁榮壯大到提供給小劇場一個相互辯證的空間。 於是小劇場必須承擔台灣劇場的「原罪」,小劇場成了台灣劇場發展史上的「黑暗時代」,許多人看到「小劇場」三個字的表情就好像在五金行裏買國產電器;有些學院派學者更直斥小劇場爲「亂象」,亟欲將之摒於劇場史外而後快。奇花異卉的芬膠芳,隨風而逝,殘敗的瓣蕊,化爲灰泥,小劇場的歷史眼看就要變成傳說了。 所以我們要舉行我們的饗宴。它不是無中生有,它是掉到地裏的種子。我們要興高采烈地大嚼大喝,因爲我們嚼的,是小劇場先烈的骨,我們喝的,是他們的血。他們把身體賜給我們,讓我們更加壯大,繼續走要走的路。我們就是他們。就像「木偶奇遇記」裏的小木偶畢那曹邁向「眞人」之路一般,我們堅信小劇場的種子總有一天會發芽,蔚爲大觀。在那之前,一切只是過程。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
回想與回響 Echo
Money Makes People Talk 對兩封給「劇場同志」的信的反思
針對《表演藝術》二月號田啓元的〈給劇場同志的一封公開信〉,與隨後三月號李永豐的〈劇場同志,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這兩封信,國內另一位小劇場工作者,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反思。
-
 回想與回響 Echo
回想與回響 Echo劇場同志,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是誰!你做一齣戲,別人就得重視你,媒體就要把你捧上天。社會要補助,觀衆一定要來看才可以,那有這種道理?」
-
回想與回響 Echo
給劇場同志的一封公開信
「幾年下來,我們社會似乎安靜詳和了些。因此有人說小劇場的批判性沒有了,我很不以爲然。因爲我們的體制還在,社會不平之處,所目歷歷,更何況所謂批判,不應只是批判外在的對象,也要批判自己,怎麼會因爲形式上的轉變就有這樣的想法?誠爲異哉!」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回顧潤十年
起於八〇年代的小劇場,由於政治環境的丕變,政治議題成為小劇場一路發展的主要訴求。九四年的小劇場,除了有與官方因准演證問題而引爆的大對決之外,人間劇展的「收編論」亦讓小劇場一時硝煙四起。反觀九五年,在台北縣另一種「官方」體制主導下,「身體表演祭」裡公然的裸體演出、「破爛生活節」在板橋啤酒廠的大膽作戲,以及十幾個團體在自家人的咖啡廳內推出接續五個月的「四流巨星藝術節」,一些比「傳統」小劇場更邊緣的團體一一正式登場了。在解嚴前夕小劇場運動開始發展至今近十年,小劇場這個一向較封閉的「領土」內是否開始發生「質變」?我們除了為讀者回顧九五年重要事件外,亦請來了小劇場的老人類、新人類,共同為九五年小劇場做一次澈底的體檢。
-
特別企畫 Feature
諸神退位,群魔開始亂舞? 小劇場工作者座談會
從解嚴前夕開始有「精采」演出的小劇場,不管在演出的內容、形式、與議題上,都曾經有一新觀衆耳目的表現。小劇場近十年來所提出來批判的問題,不管是政治性、突破禁忌的議題、或小劇場的美學與身體上的問題,令人關切其後勢的發展。本刊特別邀請數位資深的小劇場工作者,和部分新新小劇場人一起座談。讓大家在檢討實際工作所面臨的問題的同時,也開始為小劇場下個十年整理出過去的脈絡和可以期待的前景。
-
劇場偵測
景氣「紅燈區」 英倫小劇場危機重重
倫敦西區新上演的兩齣歌舞劇《爲你瘋狂》(Crazy for You),及《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再度掀起戲劇熱潮。隨著英鎊貶値,歐洲、美洲、亞洲觀光客大批湧入,倫敦大型歌舞劇戲票,更是一票難求。民間私人戲票經紀商(ticket agent),甚至賣出四倍高的黃牛票。反觀以純戲劇或實驗性爲主的小劇場(戲劇、舞蹈、音樂等小型表演場地)的命運,就不似以歌舞劇爲主的劇院幸運。根據英國政策硏究學院調査小組(Policy Studies Institute)最新報吿顯示:今年戲劇人口比一九九二年多出四分之一,但皆爲歌舞劇觀衆;現代劇(modern drama)及喜劇(comedy)的人口反而只是一九八七年同類型戲劇人口的一半。 面臨經濟蕭條、房租和物價上漲的影響,龐大的赤字與透支,小型劇場莫不自求出路,改變目前營運政策,來面對這不知還要承受多久的危機。 政府補助預算縮減 倫敦自治區補助金計劃處(London Boroughs Grants Scheme)是與倫敦地方政府局(London Local Authori-ty)及倫敦藝術局(London Arts Board)並列的三大主要劇場補助單位,也因其本身經費遭到英國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刪減,而凍結其補助經費長達四年之久。倫敦藝術局一位官員Robert Gordon說:「只靠我們補助生存的表演場地,是不可能挽回如此大量資金不足的局面,我們必須減少我們的補助金」,「我們也面臨極大的壓力,我們自國會得到的預算基金,明年也將削減。目前我們所發出的一英鎊等於是我們將來所需的十英鎊,所以刪減補助是勢在必行的!」 倫敦各地區政府,只有西敏寺市(Westminster)增加其預算,其它地區,已確定平均將削減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經費。 私人及基金會贊助熱情下降 私人贊助的比例也下降。依賴贊助及補助爲生的劇場不是縮減人員就是薪資凍結。以格林尼治少年劇團(Greenwich Young People's Theatre)爲例,由倫敦敎育局(Inner London Education Authority)補助的一百五十萬英鎊已降至十九萬英鎊,人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