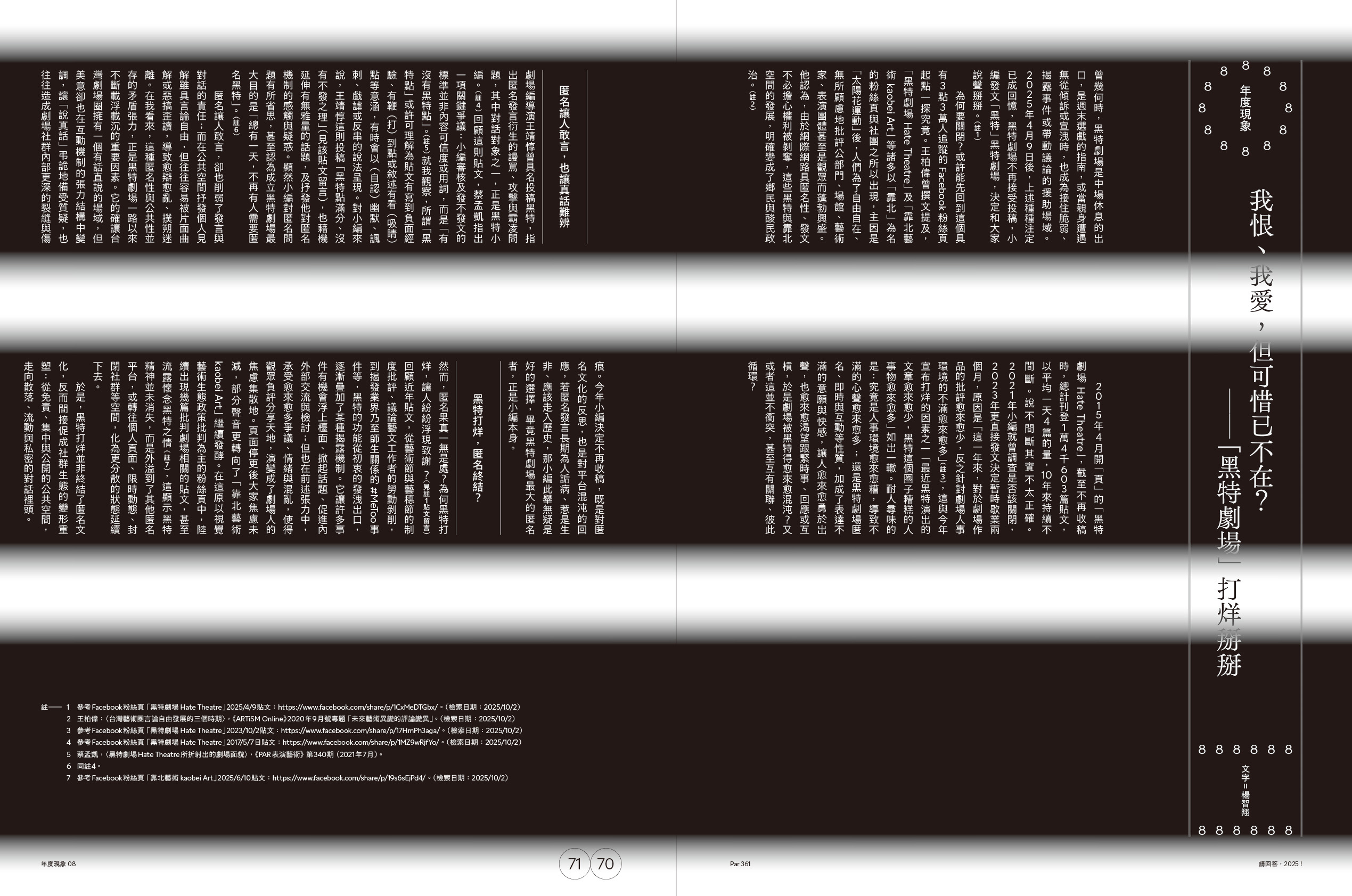吳岳霖
《PAR表演藝術》特約編輯、劇評人、戲劇顧問與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曾任表演藝術評論台執行編輯。希望自己的文字裡能夠有光,還有溫度。
-
特別企畫 Feature
汪兆謙:在最好的狀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對大家一起做事,是有嚮往的。」35歲後感受到體力下滑,但初衷始終撐住他。不過,汪兆謙也認為35至50歲間是「最好的狀態」。
-
編輯 Pick-Up
影集不耐症患者的影集推薦
我現在開始疑惑,到底是推薦影集,還是演員?是林柏宏,我承認。當然不是為了他在《怪胎》裡露出大概不到20秒腹肌的洗澡鏡頭(可能也是原因),而是他依傍著生活感與難用言說的真誠,讓這些角色彷若在身邊某個街口,我們就會相遇,甚至撞著。
-
戲劇
身體、敘事與界線
對於「跨界」,往往著眼於「跨」這個動作;但,「跨界三部曲」得思考的反倒是「界線」的劃分,除涉及門類劃分,更核心的是自我定位的安置,而這似乎是「馬戲」在台灣有急於驗明正身的渴望。對我而言,「跨界三部曲」開發了馬戲的身體、啟動了馬戲的敘事;但,「物件劇場」、「裝置藝術」、「舞蹈」三者與「馬戲」的距離到底為何?我們是否像畫下一條虛設的界線,然後標榜「現在進行一個跨越的動作」?
-
戲劇 C Musical製作《我的上海天菜》
續寫女強人未來 台韓合作「遇/預見」愛情
C Musical製作於十二月推出的《我的上海天菜》是《焢肉遇見你》續作,描繪《焢》劇女主角、由演員陳品伶飾演的女強人律師的未來,描繪她到了上海後,遇見鮮肉天菜,讓故事繼續下去。這次的製作亦與韓國導演成烈錫、編舞金敬用與歌唱指導金仁馨合作,並邀來歌手龔言脩出飾鮮肉天菜一角。並推出特別的行銷手法,舉辦「限時預見會」讓演員與部分歌曲、情節「親密地」預先遇見觀眾。
-
特別企畫 Feature
10個現象,回探這一年的台灣表演藝術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依常規運行的世界,也迅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防疫有成的台灣,在上半年的封閉警戒後,成為全球少數能回歸日常的國度。在回顧過往一年的此刻,我們也觀察到不同與往年的變化與發展
-
特別企畫 Feature
10個現象,回探這一年的台灣表演藝術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依常規運行的世界,也迅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防疫有成的台灣,在上半年的封閉警戒後,成為全球少數能回歸日常的國度。在回顧過往一年的此刻,我們也觀察到不同與往年的變化與發展
-
特別企畫 Feature
10個現象,回探這一年的台灣表演藝術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依常規運行的世界,也迅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防疫有成的台灣,在上半年的封閉警戒後,成為全球少數能回歸日常的國度。在回顧過往一年的此刻,我們也觀察到不同與往年的變化與發展
-
焦點專題 Focus 戲曲╱戲劇演員
朱安麗 願為微光,照亮大家
這條學習傳統戲曲的道路,就像是在尋找遠方的光;過程裡,大大小小的傷都烙在身上。所以我希望能護持這群年輕演員,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傳授出去,讓他們成為國光劇團下一個廿五年的耀眼星星。就算我只是微光,也會去照亮所有人。
-
焦點專題 Focus
告別庚子年 與表演一起甩開陰霾
在這變化迭起、災厄連連的一年,讓人特別感到與「世界末日」是如此地接近,人們透過封鎖與隔離,暫時守住生與死、陰性與陽性的距離,如常,成了奢望。在台灣的我們幸運地走進世界少有的「後疫情時代」,表演可以繼續,在這個美好的泡泡裡,讓我們走進劇場,透過跨年演出,送走災厄、沉澱反思,也把手同歡,迎接並期盼未來的平安
-
戲曲
作者的陽謀
「作者於創作裡的位置」成為理解《光華之君》的方式。 因為,連將其他人物當作道具的光華君也不過是藤夫人的筆下人物,用以排解無處宣洩的依戀,以及與源將軍無解的關係。可惜的是,編導雖時不時安排藤夫人出入情節,卻未改變全劇編寫比例與調性,也未能有效深究藤夫人的內心。她與光華君的對話──「為什麼要創造我?」、「大概是因為寂寞吧。」縱然精采卻流於收尾的權宜。
-
特別企畫 Feature 現代變身-當代劇場
劇場裡尋妖 轉動解決人類問題的鑰匙
妖怪作為複雜人心的隱喻,是許多現代劇場創作者創作的入徑,在台灣的當代劇場中,除了兒童劇常出現的可愛妖怪外,也有如拾念劇集化用《山海經》打造的「超神話」系列,另針對台灣在地奇幻素材發展的有雞屎藤舞蹈劇場《府城仙怪誌》、《府城夜話》,再現劇團的《物怪之里》,還有憑空想像創造妖怪的《雪峰村上的惡人廟》。妖怪在劇場裡的誕生,多是為了解決人類無法以「人類」身分於這個世界處理的問題,是創作者自身的投射,藉此轉動解決人類問題的鑰匙
-
特別企畫 Feature 冒險軸線
我們出發,一起到劇場找妖怪!
妖怪,還躲藏在哪裡呢? 還是,他們早在身旁竊笑,是我們太過遲鈍呢? 妖怪搜查線的最後一站,為了避免被妖怪笑我們蠢,身為特派搜查員的帕帕將光明正大的(?)提供幾條妖怪即將於劇場裡現身的線索,足跡遍布台北、台南、高雄等地。 你,準備好了嗎?接下來的任務交給你了!屬於你的尋找妖怪大冒險立刻展開!
-
戲劇 同黨劇團《星期十,猴子死翹翹》
從極端裡釋放 夢境寫作暗黑家庭戲
同黨劇團《星期十,猴子死翹翹》來自兩廳院駐館藝術家、編劇吳明倫大學一年級時一場詭譎、離奇與瘋狂的夢,「這是想家的夢。」吳明倫說,她將這個故事寫成小說、化為劇本,敘述窮鄉僻壤小鎮裡的一對母子,以愛為名成就控制之下的家庭倫理。導演黃郁晴則將拋開寫實框架,「偏激到底,然後大爆發,不再有任何救贖、或改變。」在極端到極致的情境裡,釋放日常的壓抑
-
戲劇
窺視與指認之後
指認過程讓《有關當局》的整體敘事增添厚度,但也反顯所有編寫都過於刻意,如人物的功能性較強,難以真正檢視情感與動機,因其隱喻已成為必然因果,理所當然、堂而皇之,包含聰哥的偷渡理由、萍姐對孩子的執念等。不過,演員優異且自然的表現確實修補文本的闕如,甚至更顯意味深長。
-
藝@書
整理記憶裡的劇場圖像
劇場影像設計王奕盛的《看不見的台前幕後》由多篇散文/短文組成,保留了說故事的口氣,並擁有回憶錄的性質。每篇短文都以「劇場」為核心進行寫作,同時也成為連結的依據。他用回憶書寫來呈現對劇場現象的觀察,更多的是將每個事件作為敘事基底,讓自己隱藏到文字背後,而其他劇場人的形象就會鮮明浮現;此書「口述歷史」的質性,也讓每個被記錄的當下都被鋪墊成劇場史的一隅。
-
特別企畫 Feature 創作的行動 漫步與找尋
選擇與被選擇 都是「交換」人生
「斜槓青年創作體」的確很斜槓,主創朱怡文、林謙信與周韋廷三人的專長橫跨導演、表演、音樂設計,也以「共創」為原則去回應創作媒材。他們的作品通常與地方緊密相關,透過駐地田調採集、發展創作,如在恆春的《半島風聲 相放伴》還有將在臺南藝術節演出的《香蘭男子電棒燙》。不管他們是「被地方選擇」或自己「選擇地方」,重點都在「交換」用自身與他人的生命經驗,找到可以彼此溝通的當下。
-
戲劇 眼球先生X健身工廠《猛男地獄》
衝突不只在畫面 用改變去觀看世界
「劇場應該要一直有好玩的事情發生。」眼球先生堅定地說,似乎替作品找了個出發點;新作《猛男地獄》談的是健身、整形,然後又與健身工廠的教練合作,讓他們與温貞菱、黃健瑋等專業演員同台演出。但《猛男地獄》何止跨界,也不只好玩而已,眼球先生通過自己擅長的畫面去建構意境,在與自己對話同時也成為觀看世界的方式;他將通過蔚為流行的健身、整形,聚焦出核心問題:改變。
-
戲劇
恐懼失去的焦慮,在躁動
《皇都電姬》的情節易懂、概念明確卻在舞台上亂得可以,這些在戲劇表現上的不足,我認為正洩漏出創作者對現下的不安或許是近期的政治局勢,或許是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其所影射的現實感於劇情間若隱若現(甚至早全盤傾吐),更有種必須於此刻演出的憂慮在躁動。不過,這何嘗不是在指陳「這個時代」可以說是製造混亂,也可能是激進急躁,但人存在的核心意義卻於其中彰顯得愈發堅定。
-
焦點專題 Focus
共同在此的「我」
當吳興國在角色/腳色穿越間,用一句「吳興國,我回來了!這個決定比出家還要難。」然後抹去臉妝、卸下衣著,向觀眾宣告「我」在此,「吳興國」回來了。戲曲演員通過行當、妝容等方式去建構與觀眾間的關係,但其表演行為卻造成一種反差──回來的是戲曲演員,還是吳興國。或許,我們會說當代戲曲以獨角戲方式去陳述自身已見怪不怪,像張軍《我,哈姆雷特》(2018)、朱安麗《女子安麗》(2019)等;但別忘了那時才二○○一年國光劇團尚未以《閻羅夢》開啟「台灣京劇新美學」的時代。
-
戲劇
理解通往完成間的距離
當周瑞祥極用力地去強調「魔術已死」,代表的是我們已處於「魔術已死」的年代?(所以他要極力呼喊!)還是,我們也不曾經歷、感受到「魔術活躍」的時刻?(因此他要強加我們「已死,所以曾活」的想像?)更進一步地,如何回溯(作為魔術前身的)魔法/巫術對我們生命的影響?同時,這又能否因參與「新人類計劃」獲取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