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我們的受訪者立下死志要存錢,仍舊儀式感十足地要買一件衣服回家,哪怕這件衣服從來不穿,哪怕家裡沒穿過的衣服高達幾百件,她說,我只是不想要自己手空空的,這是我上完一整天班後,唯一花錢買來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2026年開春前幾天,到兩廳院欣賞周善祥的鋼琴與管風琴演奏會。曲終人散時走入廣場,冬陽普照,暖烘烘的,讓人心情愉悅舒暢。曬太陽的同時,我看到很多人在走路或散步呢! 一個個優雅從容的行者從眼睛經過的同時,我想到一句很喜歡的拉丁文銘言:「Festina lente」,羅馬奧古斯都把這句拉丁文銘言翻譯成「快得從容」,世界愈快,心要愈慢;愈急的事,愈不可以匆匆忙忙面對、做決定。這幾年我迷上徒步旅行,尤其是長距離的朝聖之旅,雖然不是宗教信仰者,徒步旅行的我的部分的心情在於「溫柔抵抗」比起被動地讓交通工具將自己載到某地,我一步一腳印,完全掌握想要前往的方向在轉速日益加快的世界刻意放慢腳步,只專注在當下,我發現這樣更能聆聽自己的心,也更能覺察自己的意念。 長距離徒步旅行是很有效的身心治療呢!義大利帕多瓦大學大腦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深入研究源於日本的「森林浴」,以及森林浴對人體的生理影響和壓力管理效果:1980年代日本林野廳提出「しんりんよく」(森林浴)一詞,指出沉浸於大自然,讓眼耳鼻舌身沐浴在森林的氛圍中,能有效放鬆、減壓、增加身心健康與提升專注力。義大利的科學家採用前後測設計,讓29位受試者在森林中完全沉浸兩天,並記錄沉浸前後的多項生理參數(例如心律、血壓、免疫力、壓力感知等)。他們發現森林浴顯著改善了受試者的生理壓力管理能力,沉浸在大自然的過程中,不但讓主導警戒和戰鬥的交感神經活性有所抑制,也同時活化了主導休息和修復的副交感神經,我們的身體因此得到真正的放鬆。 這正是我好幾次走在朝聖路上的感覺:眼睛看著周遭綠油油的風景,耳邊有時蟲鳴鳥叫,有時溪水潺潺流過,安靜走路時,感官變得格外敏銳,深深呼吸,感受身旁的樹木、土壤、花朵森林裡真的好香!在大自然裡步行的好處不只有淨化提升身心狀態,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團隊更證實愛走路的人比起久坐的人創造力產出平均增加了60%;而且不管是在室內面對空白牆的跑步機上走路或是呼吸著室外的新鮮空氣行走,兩者同樣能激發創造力。研究人員將吧178位受試者分組,結果顯示,比起環境,其實是「行走」這項行為,讓人靈光滿滿。與坐著的人相比(坐在室內面對空白牆壁,或在室外坐在輪椅上被推著),走路組的人的創造力水準始終明顯偏高,

看電影《F1》兩個半小時注意力緊緊抓住,非常喜歡。看完後,給AI輸入了以下問題: 「模擬評論好萊塢大片的基本語調,對工業、好萊塢、商業、運動賽事、英雄崇拜、劇情老套等堆砌名詞,做一篇貶中帶褒的評論」。 得到如下結果: 《F1》幾乎是為了證明好萊塢工業體系仍然運轉良好而存在的一部電影。它把一項本就高度商業化、數據化、被資本與品牌全面占領的運動賽事,再次轉譯為一個我們早已熟悉的英雄敘事模板:孤狼式天才、失敗後的回歸、團隊合作的幻象,以及在終點線前完成自我救贖的瞬間。 這不是一部試圖顛覆任何敘事規則的作品。相反地,它像一場被精密設計的比賽轉播,節奏、情緒、高潮與勝利都嚴格遵守好萊塢的工業標準。每一個鏡頭都服務於「速度」與「榮耀」的視覺消費,每一次引擎轟鳴都在提醒觀眾:這是一項由金錢、科技與品牌堆疊出來的現代競技神話。 英雄崇拜在這裡被包裝得幾乎無懈可擊。主角不是單純的車手,而是一個被市場需要的象徵經驗、男性魅力、個人意志與資本浪漫主義的集合體。電影假裝討論團隊合作與制度,但最終仍回到那個老問題:當一切崩潰時,拯救體系的依然是一個足夠「強大」的個人。 劇情老套嗎?毫無疑問。你幾乎能提前預測每一次低谷與反彈、每一場衝突與和解。但也正因如此,《F1》運作得異常順暢。它深知自己的觀眾想看什麼,也清楚這個全球化娛樂市場需要怎樣的情緒輸出可被理解、可被消費、可被複製。 如果說《F1》有任何真正的價值,那並不在於它說了什麼新故事,而在於它再次證明了好萊塢如何能將一項現實中的極端資本運動,轉化為一場情感上高度有效的娛樂體驗。它不是藝術電影,也無意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作品;它是一部誠實地為體系服務的電影,而這種誠實,反而成了它最難以否認的優點。 最終,《F1》就像一場完美執行的賽事你明知道規則、知道結局、知道誰會站上頒獎台,但當引擎啟動、燈號熄滅,你還是會不

幾十年的表演歷練,試圖把老師講過的表演法則通通實踐個遍,同時也在實踐中積累了更豐富的體悟,那絕不是把三個動作減為兩個動作那麼簡單。當你拿到1個新劇本,除了藝術家油然而生第六感的敏感天性外,還要把湧動的心脈化為理智的構思。有想像,有見解,有布局,有取捨,有手段,有差別,有風格,這些都是硬功夫以外的頭腦軟功力。

ᛟ // 系統公告 // 協定版本:版號.祖靈.零點一 狀態:強制覆寫中... 警告:此過程將導致文明外殼脫落。 ᛟ // 額心 // 重置。開機。神諭。 我把臍帶接回土壤,電流從腳底往上竄。 啟動不需要按鈕,只需要一次劇烈的羊水退去。 我先聽震動,再看畫面。 晶圓裡的訊號跳三下, 「pit pit pit」, 不是雜訊,是脈搏。 我先用血液冷卻,再交給神經,數據經過痛覺才變成記憶。 hini . . . 連結 下載 . . . ᚾ ᚾ // 耳後 // 接收。濾波。除錯。 把耳機摘下,那是文明的塞子。 把耳廓打開,那是肉做的雷達。 我把 Bug 當成祖靈的敲擊, 把 Lag(延遲)當成靈魂的跟隨。 導航不準沒關係,迷路會回到身體。 身體有它自己的陀螺儀, 它記得重力,記得斜度,記得哪裡風比較甜。 身體把迷路縫回地圖,下一次就更精確。 風裡,我開一個埠口⊙,讓頻率進來測我。 頻率一測,我就知道說話該用多少赫茲。 太高頻是為了嚇阻,太低頻是為了安撫。 赫茲變成歌,歌不是 MP3 或串流, 歌住在〔耳膜〕與〔骨頭〕的縫隙裡。 [pit pit] : [雜訊] : [神諭] [shhh shhh] : [風扇] : [海浪] ᛇ // 眼球 // 顯示。折射。幻象。 眼 : 先閉後見。 視網

回望過去,一次看似不經意的邀約、一封突然收到的郵件、一次改變計畫的轉機,往往成為人生劇本悄然改寫的起點。北齋與高井鴻山的相遇,讓小布施誕生了不朽名作;而我們生命中看似偶然的一次邂逅、一段談話、一場演出,也都可能在未來某一天被證明是改寫命運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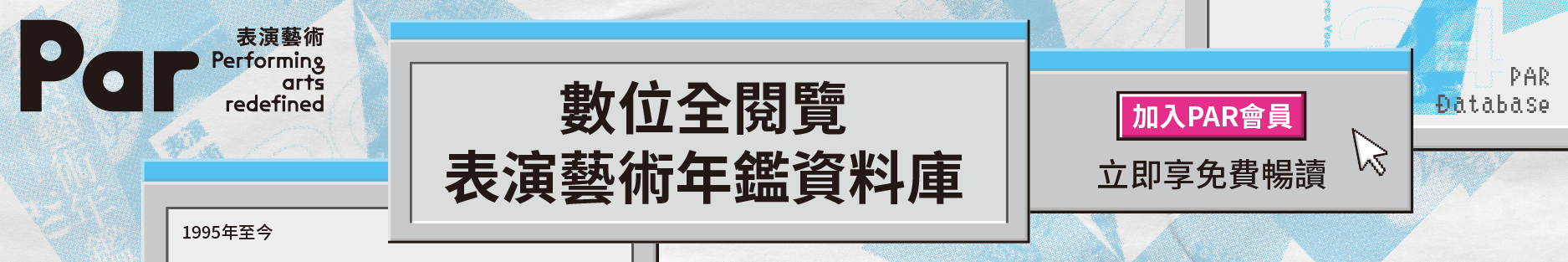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其實和易智言導演合作後,我就改掉了演完後看monitor的習慣,自己是什麼樣子自己心知肚明,如果那與你想要的樣子不同,那麽就算你怎樣想盡辦法處理你的外表,也只會讓你變成一種進退兩難,不痛不癢的樣貌,既成不了這個氣候,也到不了那個目的,終究只是白忙一場。

下筆寫這篇文章時,正值歲末年終,我忙完整年的工作,得閒在家休養生息,同時熱烈歡喜地計畫著來年的壯遊:我要去日本走一千兩百公里的「四國遍路」,這趟環繞四國本島、串連88間寺廟的朝聖之旅,對我來說,絕對會是讓2026年成為永生難忘之年的大事! 大腦神經科學界近年有不少研究聚焦在走路(尤其是以朝聖或修行為目標的步行)對身心所產生影響,結果指出此類活動不但能增加神經可塑性,還能提高情緒穩定度:長時間帶著正念,一步一腳印,重複地、持續地行走刺激大腦神經生成並重組,讓記憶更加鞏固,學習力也一併增強;走在朝聖路上,動中有靜,步行激發正念冥想,讓朝聖者有更高的自律和自我察覺能力,情緒控管力和專注力也得到提升。 原來有這麼多好處啊!難怪兩年前我前後走完日本熊野古道和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之路時,雖然每天步行將近30公里讓雙腿很有感(甚至長水泡感覺痛不欲生),但走在路上的日子,我都覺得神清氣爽、頭腦清明,看什麼想什麼都覺得美好有希望,世界一片光亮!身為大腦神經科學研究者,也是喜愛走世界各大朝聖之路的人,我忍不住研究起「走路」這件事對身心的正能量到底從何而來。 想起自己獨自走在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路上時,有一段路在森林裡,林中竟然有好幾個涼水攤兼賣紀念品!那天,我沒有太大的趕路壓力,觀光客的本性展露無疑:每逢小攤一定逛,有喝涼的地方就坐下吹吹風,很舒服。朝聖路上有什麼紀念品好買?大多是徽章、貼紙等有紀念性的小東西,每天得背著全身家當前進,不能太有物慾;起了物慾、買了東西就得一路背著,再美的物件只會成為累贅和負擔。人生在世,想要的多如繁星,需要的其實屈指可數。我買了一個徽章,上面有雙腳,腳底貼滿膏藥,寫著 NO PAIN NO GLORY「沒有痛苦,怎得榮耀」,水泡真的是不少朝聖者的共同記憶。 走著走著遇到一隊可愛的西班牙年輕人,其中有個女孩背包上掛了數字氣球,是來走朝聖之路慶祝33歲生日的。為什麼走朝聖之路慶生?我問自己。應該是想達成心願、完成目標,感受自己的存在吧。途中真的會深刻感受自己的存在呢!帶著所有行囊,一步一步走,腳會酸、背會痛,身體會熱會冷,肚子會餓;朝聖途中,外在的干擾少了,注意力回到生理與心理的需求,於是深刻體驗自己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是很單純的,腳走著,渴了喝水、餓了吃飯,看到漂亮的風景很開心,當天走到終點覺

真:2025年就這樣過完了。今天說好要談什麼?意外嗎?可是談這個也奇怪,真要說起來,如果哪天生活什麼意外都沒發生,那才是最大的意外吧? 謙:對啊。記憶中,有哪一年真的平平靜靜地過完嗎?如果有,我反而會覺得有點不安。特別我們做這行的,多少該了解,意外才是生活的本質。 真:所以談到意外真的會聊不完。以前拍廣告的時候,大概什麼事情都碰過一輪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們要拍攝一個機器,那個機器非常昂貴一台要6000多萬,沒人敢碰,需要指定的演員、專業操作者才可以使用,結果開拍當天,演員說他太太生病臨時不能來。哇,那怎麼辦?一問之下工廠沒有其他人會用這個機器,誰胡亂上陣都是危險。最後我們只能用鏡頭借位,沒真的碰到機器,只拍局部動作,特寫使用機器的專注表情。不然怎麼辦?我一大隊人馬出動到現場,分分秒秒都要付費,不可能就這樣取消拍攝等別天啊?發生意外的時候就只能趕快把問題解決。 謙:可是人生就是這樣瞬息萬變,你也不能說那是意外,只能說那是常態。 真:對嘛,意外就是常態。其他像是要拍好天氣的日子,太陽遲遲不來,換個位置拍攝,太陽的光就落在我們剛剛安置好的地方。其他像是拍攝手部特寫的時候,光是尋找「手」的演員都好辛苦。之前拍攝能量飲料的廣告,因為廣告客群主打勞工,所以手部演員的手也需要有歲月、勞動的痕跡,找到以後還要拿捏放下飲料的力氣,有次一個演員力氣太大,一放下瓶子就碎了!找來找去,最後是一個製片助理上陣,拍一次就OK,後來成為我們的御用手演員(笑)。 謙:你說的這種例子,我好像也可以舉幾個出來!我還記得綠光最早開始搬演世界劇場《Proof》的時候,我擔任排練助理,那個編制很小,演員只有4個,場景也單純,都是發生在角色家裡的後院,照理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不過,有一場戲是家裡來了很多人開Party,結束之後後院就有各種垃圾散亂,所以會有很多小道具,像是揉成一團的鋁箔紙、啤酒罐子之類的。某一場下戲之後,我把那些小道具平放在道具桌上,結果晚場演出前要

謙:但我們不能每次都仰賴對手演員啊!像這次《八月,在我家》首演週,大概第2場吧?只有你一個人,結果整個忘詞,我在台下看,想說:「哇!你給我寫了一段全新的台詞欸。」 真:我完全忘記那個台詞中要提到的詩人的名字,所以想到以前只能自己墊詞,腦袋一團混亂的時候其實還是有在思考啦,劇場就是這個樣子嘛。 謙:但我覺得,那些意外都比不上「人間」系列有李美國(編按)的演出。 真:李美國那幾次,我想到都覺得好笑。有一場是《人間條件五》李美國跟羅北安對戲,故事中有一塊蛋糕,整個劇組都知道羅北安滴酒不沾,真的一滴酒都不能碰,碰了絕對出事,結果那場蛋糕上的櫻桃竟然是酒漬櫻桃!他吃下之後整個人茫了,忽然冒出一句劇本完全沒有寫的話:「同學我好像迷路了」聽到這裡,我想說完蛋了,李美國要怎麼救?沒想到他乾脆整場戲跳過,跳到下一段去。看到的時候心臟真的漏跳一拍。 謙:這種事情太多了,有次我演故事工廠的《小兒子》,飾演一個很會畫畫的人,對手演員要拿個本子給我畫的時候,四處翻找口袋,才發現作為道具的原子筆根本沒有帶到。 真:說到小道具沒有帶!來,又是李美國! 《人間條件二》有一場很重要的戲,李美國要掏出一張地契給對手演員,表示他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告訴他這張地契代表責任結果,走到舞台上才發現這張最重要的地契竟然沒有帶!然後李美國就全身上下四處翻找,看自己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掏出來的。最後 謙:最後他拿出自己的眼鏡!因為那是全身上下唯一可以拿下來的東西。 真:結果怎麼樣?觀眾竟然還是買單!把那個眼鏡解讀成一種很深的寓意。 謙:這真的太好笑了,可以講一輩子,有人討論吳念真的編劇比喻手法,解析眼鏡到底代表什麼

YC, 年前到香港一趟,適逢香港藝術節,興致勃勃地買了張粵劇演出的票。小時候在家鄉看的是潮州戲,來台灣則接觸京崑、南管、歌仔戲,粵劇難得機緣親逢其盛。印象中的廣東大戲,最早來自兩部電影《南海十三郎》和《虎度門》。 《南海十三郎》改編自1930年代粵劇劇作家江譽鏐的生平,謝君豪飾演這位才高命蹇的粵劇名家,入型入格。裡頭有個片段,十三郎同時開3部戲,端坐在廳堂口述,3名抄寫員俯首案前,奮筆疾書,一人負責謄錄一部劇目。「好,來一段快中板。(哼唱)忠心一片志昂揚,誓闖胡邦降敵往」「(數白欖)我感謝大俠崑崙,救小妹離魔障,惟願今後點打算,我而家都好徬徨」「先來段走馬。哎吔,太惜山伯都未試情共愛咯,迎望夜空等待,傷心百事哀」結果,3個人手速竟然跟不上江譽鏐的思如泉湧,抄寫不及,被他轟出門。撇開情節不提,粵劇詞曲靈巧多變,雅俗有致,自此留下深刻印象。 電影《虎度門》拍的是粵劇名伶推行粵劇改革的艱困,同時又面對自己家庭種種狀況,團務家務兩頭忙。「虎度門」原指演員出入場的台口,伶人上戲,一踏出虎度門,就要忘記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所以其意涵引申為抉擇的關鍵時刻。蕭芳芳簡直是《虎度門》主角的不二人選。她從童星開始演藝生涯,幾乎在生命每個階段都找得到相對應的角色,年輕時期的風颯俠女,轉型期的「林亞珍」喜劇形象,中年後的《女人四十》和《虎度門》,再到後期寓莊於諧的「苗翠花」等,幾乎每個角色的臉龐都鑿刻了她生命光影的行跡。 說到這,就可以回到在香港看的現場演出。欣賞戲曲表演,妙處總在細節,技藝水平分明擱在哪,角兒就是角兒,唱腔高亮脆爽,動作行雲流水,演得入神,看得忘我,興致一來,總幻想自己也能上台跑個圓場。那晚看的劇目,大場面不少,所以有很多跑龍套的小兵、侍從吶喊助威,烘托氣勢。讓我納悶的事情來了,數十來個龍套在台上,年輕到年老,幾乎大半都在狀況外,眼神無戲、動作乏力,和角兒們一併站在台上,高低對比過分刺眼,甚為不忍。 「龍套龍套,深藏奧妙。演員的起跑道,角兒的品德表。」據聞有此一說,跑龍套的「肚子」要很「寬」,因為要

有時會看到一種演員,覺得他演戲好自由,最近遇見的是在韓劇《妳和其餘的一切》裡的金高銀。有時會看到一種文字,覺得他寫得好自由,最近沉迷的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偶爾會看到一種作品,發現自由就是主創的核心,譬如在北藝中心演出的《即席寫真》。 創作的自由也是比較來的。過去半年多,我在文策院參加一個相當密集的工作坊,與韓國的製片工作,將自己的長篇小說《女二》改編成影集。11月也參加了文策院的內容提案大會,做了8分鐘全英文的提案。無論是劇本或提案,都是兩門高深複雜的學問,因為除去內容更關鍵的是必須完全包含受眾的喜好,前者是觀眾,後者是資方。但如果真能摸透他們要什麼(尤其是觀眾)那該算是一種通靈吧。 過程中,剛好看了《妳和其餘的一切》。這部韓劇節奏很慢,沒有結構化的情節波動,在講兩個性格迥異的女生,如何在生命一連串的選擇之下,從朋友變為敵人又回到陪伴。特別吸引我的不是細膩獨特的女性心理與情誼,而是兩位主角的表演,尤其是金高銀。因為角色的跨度,演員必須從20歲的大學生詮釋到40歲左右。金高銀本人是30多歲,確實是個可上可下的最佳位置,兩人在造型上必然需要輔助,相較之下實在驚嘆金高銀的臉型與頭型,能自然駕馭各種變化,這真是老天爺賞飯吃。屬於她個人的能耐,是在跨度上用極為細緻的狀態落差,來為角色做區隔從眼神清亮的大學生,到充滿企圖與夢想的社會新鮮人,以及靈魂受盡影視產業背叛與消磨,從製作人轉職為編劇的40歲階段,全讓人心服口服。另一位主演朴智賢表現也非常亮眼,但姣好的五官在髮型上反而有些局限,全靠演技來支撐,也相當有看頭。 儘管自己身為演員,很討厭聽見別人說「台灣真的沒有這樣的演員」這種話。但金高銀的存在,確實是可遇不可求。不過這齣劇似乎只在某一群觀眾裡發酵著,也讓我再次感嘆自己的品味喜好與所謂的「市場」總是有無法跨越的落差。若這份距離持續擴大,我該如何投身於影集的開發,去尋找或說服那群不知道在哪裡觀眾與資方呢? 從劇場到小說,我都還能稱之為「創作」的事業,到了影集劇本,就完全說不出這兩個字了。當一個產出勢必得用錢才能推動實踐,那就是所謂的商品,而非作品。那到底什麼是商業性?也不見得每個商業作品都能成功變現,不見得每個藝術作品都沒有商業性,譬如最近的日本電


編劇工作的主體,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在買菜和摘菜的路上,我們沿途或不經意或定睛尋找可用素材,時常忍受落空與失敗,然而要到許久以後你才會明白,每一步走過的路途,每一個你曾經聆聽過分享的人們,他們終究會在某些時刻,與你在不同故事裡重逢。

國光劇團以《周仁獻嫂》參加「承功新秀舞台」,無論現代觀眾對捨生取義是否有感,但嗩吶一起,全場情緒瞬間被狠狠揪起,前後排觀眾或啜泣,或噴淚,還有人在尾聲奏起時大大喘一口氣,說:「心臟快受不了了!」 早在團內響排、彩排時,就有行政同仁問我:這音樂是全新設計嗎? 不是,這是70多年前的新戲,首演就如此完整而新穎,在全體名家通力合作之下,在導演鄭亦秋領軍之下。 鄭亦秋是誰?現代觀眾遍搜腦海中的導演名單,絕對不會有鄭亦秋,但我們都看過他的作品,《白蛇傳》、《春草闖堂》、《楊門女將》、《九江口》、《桃花村》、《佘賽花》、《西廂記》、《強項令》、《滿江紅》、《謝瑤環》、《初出茅廬》和《穆桂英掛帥》等,都是他導的戲,也都是京劇史上的經典。 原來,我們熟悉的春草坐轎上坡下坡,穆桂英夜探絕谷的驚人隊形身段,佘賽花與楊繼業的圍場初識,張定邊喪服哭師與跑船救駕,小春蘭連夜趕製女鞋時虛擬寫意的拈針搓線,白青蛇歷經生死搏鬥來到斷橋重見許仙時3人的交互關係與情緒糾纏,這些都是鄭亦秋導演的原創。 而這些都還只是技巧鮮明的高潮段落,其實每齣戲的唱腔、念白、鑼鼓、配樂、身段、舞姿、武技、情緒、性格、節奏、色澤、氛圍、主題,乃至於選擇行當、流派、演員,無一不是導演管轄範圍。 而我們為什麼把他忘記? 因為這些戲已經成為傳統的一部分,觀眾以為杜近芳、葉盛蘭的《白蛇傳》生來就是如此,以為劉長瑜、寇春華《春草闖堂》和楊秋玲、王晶華的《楊門女將》原本就長成這樣,一切理所當然,忘了這是70年前從無到有的全新創作。 就像《鎖麟囊》,大家都會唱,但未必記得編劇叫翁偶虹,這些唱詞是他一字一句生出來的。 他們被忘記,但我覺得這是創作者的最高榮譽。 作為編導,也許一輩子追求的就是「被忘記」。 因為被忘記代表已被全面接受,被視為與生俱來、理所當然,已經納入傳統,不需再提示了。 今天再演70年前的經典,我們都稱負責排戲的先生為「主排」,而非導演。主排要根據現在的舞台條件、演員狀況甚至時代氛圍,精心打磨重新配置(例如國光劇團這次推出《周仁獻嫂》,我便希望妻子替死時丈夫必須深深一跪,70年前沒這觀念,竟是替死的妻子跪丈夫),

(黑畫面)「這是個真實故事,兩年前就發生在我的小鎮,很多人以奇怪的方式死掉這個故事從我的學校開始。」(學校畫面)「梅布魯克小學從幼稚園唸到5年級,一個平常的禮拜三,有一位新來的老師。」(主角跟拍畫面)「她的名字是潔斯汀.甘迪,她在那一天走進她的教室,就像每個早上一樣,但今天不一樣。」 「別班的孩子都到了,就連貝爾老師教的另一個3年級班都坐滿學生,但甘迪老師的班級空無一人,除了一個男孩,他的名字是艾力克斯.利里,他是班上18個孩子中,唯一去上學的小孩,知道為什麼嗎?」 (家中畫面)「因為前一晚,凌晨2點17分,每個小孩都醒過來,」 「下床,走下樓,打開前門,走出前院,走進黑暗,再也沒有回來。」 伴隨著小孩說故事的童音,音樂進,暗夜籠罩的美國郊區住宅,一群孩子以類火影跑(漫畫火影忍者的跑姿)之姿,衝出前門,在空蕩蕩的大馬路上狂奔。 恐怖電影《凶器》(Weapons)的開場,今年看的新片中,最喜歡的開場,沒有之一。 整部片從學生失蹤的那個早晨開始,以人名字卡切換,第二段跳到尋找孩子的父親、接著是偵辦此案的警察、商店門口無所事事的毒蟲、校長、男孩艾力克斯,帶出一個看似老掉牙的吹笛人故事。在看完全片後,讓人驚覺原來整個失蹤案的兇手早就出現了,是一部值得回頭二刷發現細節的電影。 順敘會讓這個故事普通,但敘事的形式即是內容,伊底帕斯王的故事若從頭開始講易流於流水帳,且犧牲了最懸疑的部分,正是這種敘事的巧思,視角的跳躍使得《凶器》免於大多數恐怖片會有的問題:主角降智,看起來詭異的地方硬要進去,無止盡的嚇人鏡頭(Jump Scare),《凶器》展示出真正恐怖的事情 「當人們平靜日常被破壞的瞬間」。 看完《凶器》,立刻找了編導的首作《宿劫》(Barbarian)來看,驚為天人,用3個主要角色,把「地窖裡有怪物」這類經典的恐怖片類型做出新意,一棟普通的民宿,有多少暗黑的過去,編導Zach Cregger非常擅長沉浸的鏡頭、恰到好處的劇情斷點,透過鏡頭外的聲音,想像力營造出巨大張力,透過多線,怪物出現就卡掉鏡頭,跳到下個角色,完美避免角色如何逃過怪物攻擊的疑惑,掛心角色之後的命運。本

藝術評論遠不止是藝術評論家的專利,無需組織文章,從興趣盎然國中生到看戲半輩子的資深觀眾,更多的普通戲友拾起筆來,就他們感興趣的藝術作品評頭論足,甚至有小論文般的長文,更不要說其中上下5千年引經據典的知識含量,讓專業人士大開眼界,讀一篇文章,長一番見識。讓我或者說讓更多的藝術從業者領略到善良的藝術評論對藝術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

每隔5年,當波蘭華沙的舞台再度亮起,那場專屬於蕭邦的光芒便俯瞰全球。該賽事的線上直播及頻道觀看次數屢破紀錄,2021年蕭邦鋼琴大賽(後簡稱蕭賽)的 YouTube 觀看便累計至3750萬次瀏覽、近800萬小時。媒體鏡頭從後台到舞台無孔不入,決賽門票甚至於開賣後數分鐘內售罄。這是全世界最受矚目的鋼琴比賽,也幾乎是鋼琴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殿堂「蕭邦大賽冠軍」幾乎等同於「時代鋼琴家」的代名詞。從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到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無不因蕭賽而一舉成名,立為典範。 事實上,不只蕭賽,全球每年有超過300場國際大賽,規模、獎金與音樂會機會不遑多讓,例如伊莉莎白大賽與范.克萊本大賽。但許多同時獲得多項國際賽入選資格的選手,最終可能還是選擇只參加蕭賽,就為一搏全球最大能見度。它不僅是比賽,更是「成為世界級鋼琴家」的象徵儀式。 我們與蕭賽的距離 如此盛會,台灣自然不能缺席。以我自己的經驗為起點:2000 年,我曾參與蕭賽並進入第2輪。當年評審之一阿格麗希,還特別對許博允老師提到對我的演奏印象深刻。早期資料不易考證,但據我所知,前輩如陳宏寬、陳瑞斌等人,也都在蕭賽中創下不凡成績。 但是顯然的,能夠獲得參加蕭賽的資格就已難如登天,更不用說能夠得獎。2015 年,台灣僅有兩位選手晉級錄影預選輪(註1),其中一位是我的學生詹心柔;2020 年,已有9位台灣選手進入錄影預選輪,其中數位曾受「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International Maestro Piano Festival)(註2)的洗禮,最後3位晉級至第2輪;到了 2025 年,有3位台灣選手進入第一輪,張凱閔最後挺進第2輪。可見,基層的音樂教育與國際連結還是進入國際舞台的重要推手。若說這代表我們與蕭賽的距離愈來愈近,也無不可。 最難的一關,是踏進第一輪 不為人知的是,大賽中最艱難的關卡其實是「進入」比賽本身。我曾擔任多場國際比賽的預選評審,例如韓國的「尹伊桑國際音樂大賽」

lhngaw(洞)之後。bqlit(膝蓋)lglug(搖晃,不穩)。a! qlahang wa (啊!要小心)。這不是 dma(夢),這是sayang(現在)。他以為lhngaw(隧道)是mhuqil(死亡,結束)。aji(不)。它只是bling(一個洞),一個bhruy(彎曲)的elug(路)。 在月球的飛船,或許還未毀滅。 那是一個石頭般的念想,懸在病態的、黃色的天空中。 它不再移動。它在等待。 啊,好可惜,如果錯過。 可惜只是一點點的感覺,更多的是驚惶。 這是唯一的洞,唯一的出口。 他們扛起土地。 他們行走不再輕盈。他們背負。 背負的不是衣服,不是食物。 他們帶著部落的記憶去看。 他們背負著部落,那片如今已是灰燼的家園。他們背負著母親和祖父的名字,那些在山中成為石頭的人。 記憶是肉,沉重。 他們在尋找最後的門。 啊!已經走了。 舊日的靈魂已經走了。 它被拋棄在隧道裡。 hngak(氣息)。第一口氣,是鐵鏽。第二口氣,是燒焦)。整個dxgal(土地,星球)都在 shngak(喘息)。 世界翻轉了。翻了過來。 世界的規範已然崩毀。 這場變化並不乾淨。 它像一支三叉箭,刺入,將身體與心靈強行撕裂。 我們成為癌細胞。受詛咒的膿瘡。 容易被驅使,也時常被利用。 我們增殖,如夏日的昆蟲,卻沒有意義。 活著。真不簡單。 在這片土地上,這片腐爛的廢土上。 金錢成為灰塵。 名譽成為垃圾。 一切都失去了顏色。 只剩身體的聲音。 它在說話,用血液的脈動提問。 怎麼那麼急著要走呢? 這具新的身體想要留下,它適應了這股鐵鏽的氣息。


我很幸運,現在還能擁有直接和樂手、歌手、指揮溝通、一起完成一首作品的機會,我深信真人演奏音樂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碰撞出的火花,每一次都可能因為當下的情緒、外在的環境而有些微不同,有別於AI的精準,人類的價值剛好就是那些「不完美」和「不可預測」,那份獨特的生命力,正是最珍貴的寶藏吧。

我看著一張又一張的笑臉,進場時看到我們迎賓的笑、演出中從我們手中拿到食物的笑、拍照時心滿意足的笑,角色有沒有名字到底又怎樣?戲演完後,幾乎是全場的觀眾都不走,願意排隊等待上台合照,並且熱情地跟我們分享感動,已經有觀眾看了10次以上,這個戲到底算不算是個戲到底又怎樣?

成年以後能吵的事?大概只剩開車 真:今天要談吵架這個主題,以我的立場好像的確可以這麼說男性真的不太會吵架,或者是一直想要避免爭吵。像是如果問我會在什麼場合跟人發生爭執?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過了。真的要講,可能就是開車的時候吧? 謙:你開車的時候真的特別火爆,嘴裡會一直碎碎念。不過這樣說起來,我也是啦。 真:對啊,不是只有我,多數人也是這樣啊。我有一次搭計程車,那個司機看到有人亂開車,就會舉起手假裝是一把槍,然後咻咻咻射那些亂開車的人。我坐在後面,最後就說:「司機先生,今天上路只是開個車,好多人被你射死了欸。」(笑)開車真的好難控制情緒喔。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吵架的意義是什麼?人在情緒當下,無法好好溝通啊,等於吵架只是一個斷裂而已,人跟人無法真的交換什麼新的東西出來,結束以後也不會有什麼新發現。 謙:我常常覺得,爭吵好像就是有一方放棄聆聽的過程。情緒很重的時候,兩個人常常已經不知道話講到哪裡去了,可能原先討論的話題也不存在了。會不會是因為成年以後就更多明白這件事情,才愈來愈不想吵、因而活得愈來愈壓抑呢? 真:所以說,到後來,如果你媽要跟我吵,我就會直接跑去看書。 謙:這就是為什麼,你這幾年可以一直看那麼多書(笑)。 真:不是啦,追根究柢,我覺得學生時期就應該要明白,吵架無法真正解決什麼事情,甚至無法好好釋放情緒啊。先不談我自己,小時候我經常看到鄰居吵架的畫面,非常驚險,夫妻吵到一半,會有人拿著柴刀直接劈出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對夫妻吵到一人拿刀追另一人在路上跑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現在當然不可能吵成這樣。現代人的吵架嘛?記得有次我目睹兩個人的爭吵狀態,哇賽那個畫面之激烈,其中一方盤點誰去喜宴錢包不夠自己墊了多少,另外一方又開始數自己也做了哪些事情。聽到最後,我覺得那兩個人根本不是在

旅途中在威尼斯停頓,看雙年展(今年是建築展)、訪美麗木橋旁的學院美術館欣賞文藝復興威尼斯畫派名家作品,當然也沒錯過波光粼粼的威尼斯大運河旁的佩姬.古根漢美術館:出身於美國礦業與銀行家族,佩姬在紐約成長,於巴黎養成藝術品味,最後落腳在「亞德里亞海上明珠」威尼斯;她熱愛現代藝術,所收藏的藝術品不論質與量都無人能出其右,在20世紀極受討論也備受尊崇。 一口氣看了許多現代抽象藝術巨人的作品: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馬克.羅斯科(Marks Rothko)、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保羅.克利(Paul Klee)心緒翻攪不已、回憶受到極大擾動,該怎麼形容這種感覺呢?欣賞抽象視覺藝術時,我常覺得,重點不是「看到了什麼」,而是「感受到什麼」: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些作品常會喚起深深埋藏的回憶,有時引發困惑,有時福至心靈,有時浮現的感覺難以言喻,卻抒發胸中一口悶氣。 「沒有觀賞者感知與情感參與的藝術是不完整的」,在現代藝術作品面前,觀賞者和藝術品產生了連綿不絕的對話,有時也會自問自答,這不禁讓我想起對藝術和大腦神經科學同樣在行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艾瑞克.康德爾(Eric Kandel)的文字:「大腦利用多種感官經驗(例如視覺和觸覺)以及情感過程(例如模擬和移情)來處理藝術作品,如何理解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是21世紀腦科學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 康德爾提出現代藝術和「觀賞者份額」(the beholders share)的概念,讓我特別感興趣。他說,一幅畫或一件作品,藝術家做完了不代表真的完成,必須有觀賞者加入自己的感受才能得到圓滿;藝術家創作完畢,接下來要有觀賞者接棒,當觀賞的人投入自己的記憶、情感和人生經驗,才能真正賦予藝術品完整的意義。 這些年有不少大腦科學家進行質性與量性研究,試圖了解人們在觀賞抽象藝術時,大腦中究竟發生哪些變化。《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了一項深入探討人類大腦如何與不同形式的藝術互動,並且建構主觀經驗的研究,十分有趣!在這項研究中,科學家線上訪問30位受試者,讓他們對抽象畫和寫實畫分別做出描述,外加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技術觀察29名受試者觀看同一藝術家所做的抽

一整個筆記本的田調素材積累後,我們開始揣想一個大動物獸醫的生活。那些我們備感新奇,卻是他們平凡作息的日子裡,早晨天才濛濛亮,遠處開始有牛隻哞哞叫喚起來,他是否會想起一個老朋友、記起大學時期青春過往,或者,會有一個陌生訊息從遠方捎來

YC, 「重要的是變成了玻璃,再敲敲變成了銅,再敲變成了水這樣的語言質地的變化。」詩人顧城是這麼形容他寫詩的過程,在字與字之間無盡的排列組合,他會先把聲音放在這個地方,試試看,然後再換另一個地方,彷彿字鬆開了身體的關節,咯咯作響,「O點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頭 變成 了人」;「不死 不活 不瘋 不傻 剛剛下過的雨 被他裝到碗裡一看 就知道是眨過的眼睛」;以前讀他的詩是不求甚解的喜歡,從音聲發出,回頭辨識字的形狀,再咀嚼意義的靈動。顧城喜歡把事情說得神秘迂迴,朦朦朧朧,意有所指,卻又萌生歧異。這對年少的自己就是說不出的魅惑。再後來,重讀唐詩,才明白他用白話文轉化了古詩詞的韻律,所以他的詩可以朗讀。美學鑑賞家顧隨先生說:「詩原是入樂的,後世詩離音樂而獨立,故音樂性便減少了,詞亦然。現代的白話詩完全離開了音樂,故少音樂美。」詩的美與音節字句有關,夕陽冉冉、楊柳依依,音節帶來印象的感受和情感,顧城很聰明,換了個作法說法,骨子裡仍是古典的薰陶。再更後來,重讀顧城的詩,總覺得美是美,卻不肯落地,少了世間煙火。 創作之前,我們首先是讀者。寫作之前是閱讀和聆聽。過去這些如此如此,後來形塑成寫作習性,非讀個幾遍,字句聽得舒服,才能落實。若是寫劇本,就更過癮,一人分飾多角,自己在爬格子裡頭演繹愛恨情仇,不亦樂乎。 2015年,我參與大墨(編按:王墨林)導演《長夜漫漫路迢迢》的台北重演版本,擔任副導演。這齣戲在2013年澳門藝術節首演,順應當地演員演出,語言全改為粵語。2014年牯嶺街小劇場「為你朗讀II」邀我來當此劇的讀劇導演,那時候發現,大墨導演從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英文原著改寫成中文,再由澳門演員以粵語個別轉譯,語調風格上出現了不統一,各有各的詮釋和理解,導致彼此對話時,語境無法匯聚成整體的想像。 於是在澳門排練的第一階段,就和全體演員圍坐,按字逐句去尋找華語和粵語之間的音韻聲腔使用,如何調和文讀和白話的比例,然後在兩者疊合中創造別具一格的節奏氛圍,比如某一字詞放在文中語境有什麼意思,和文本內在情境的呼應,以及唸起來在聽覺是什麼感受等。大墨導演希望劇本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