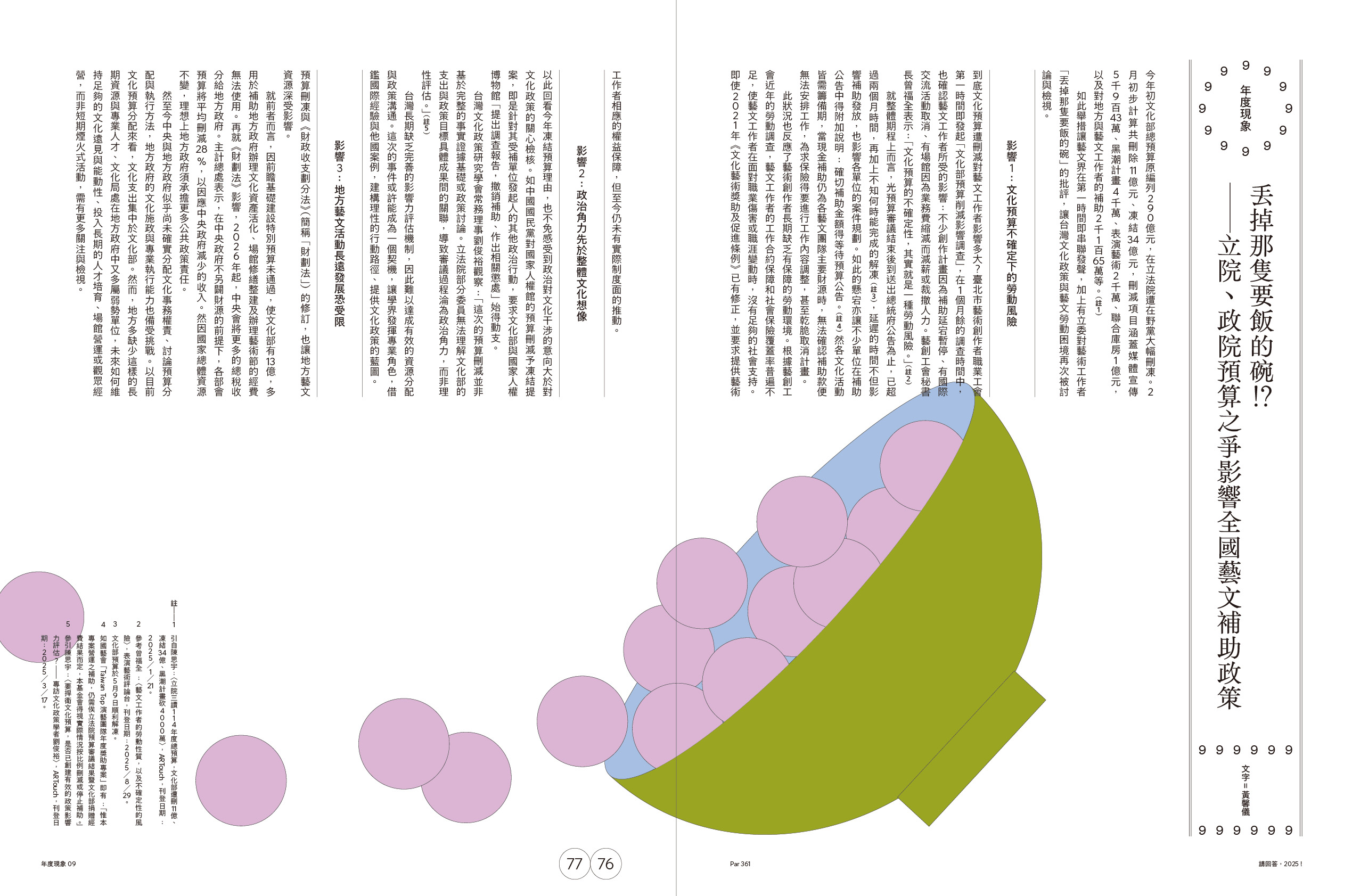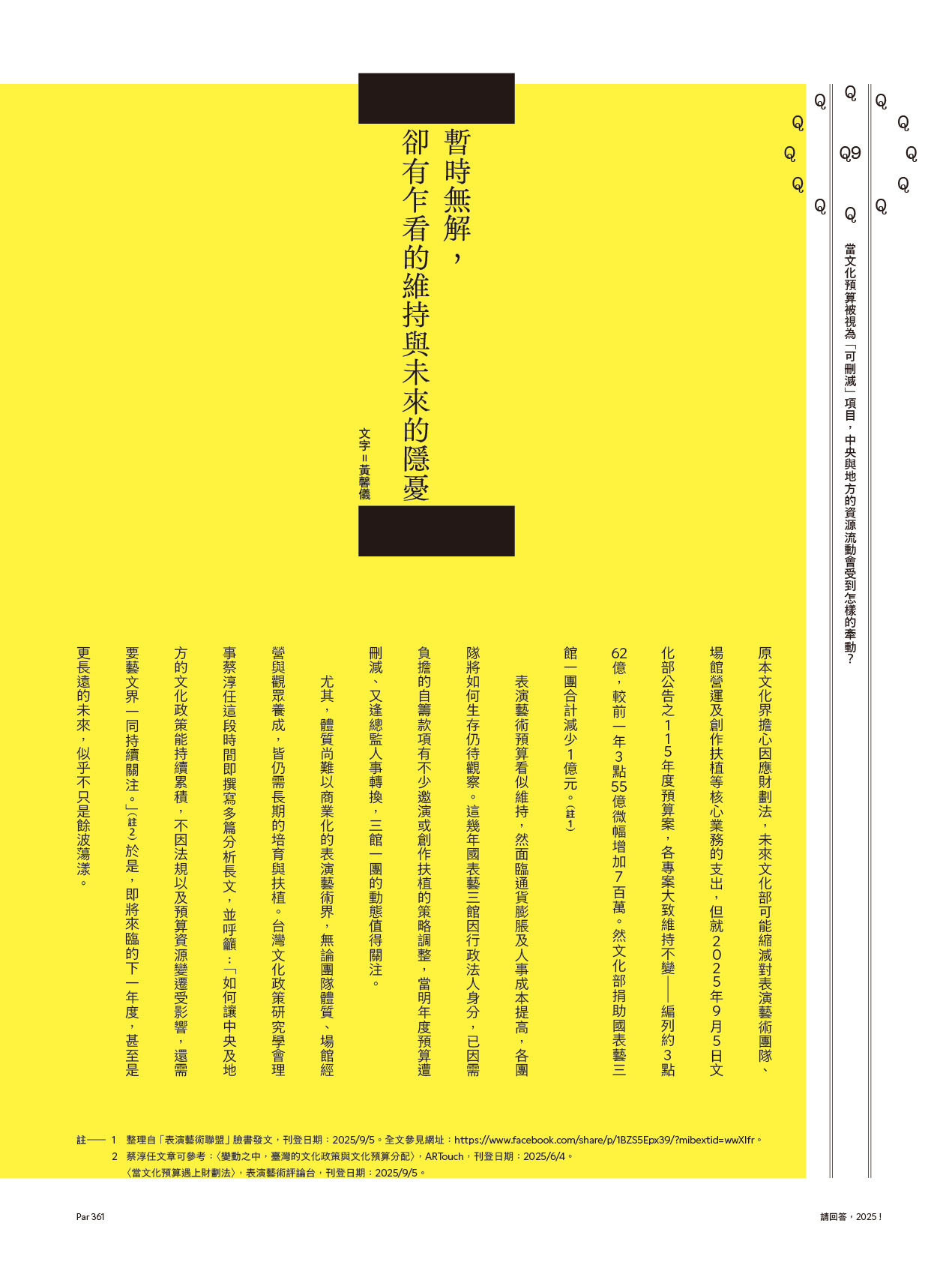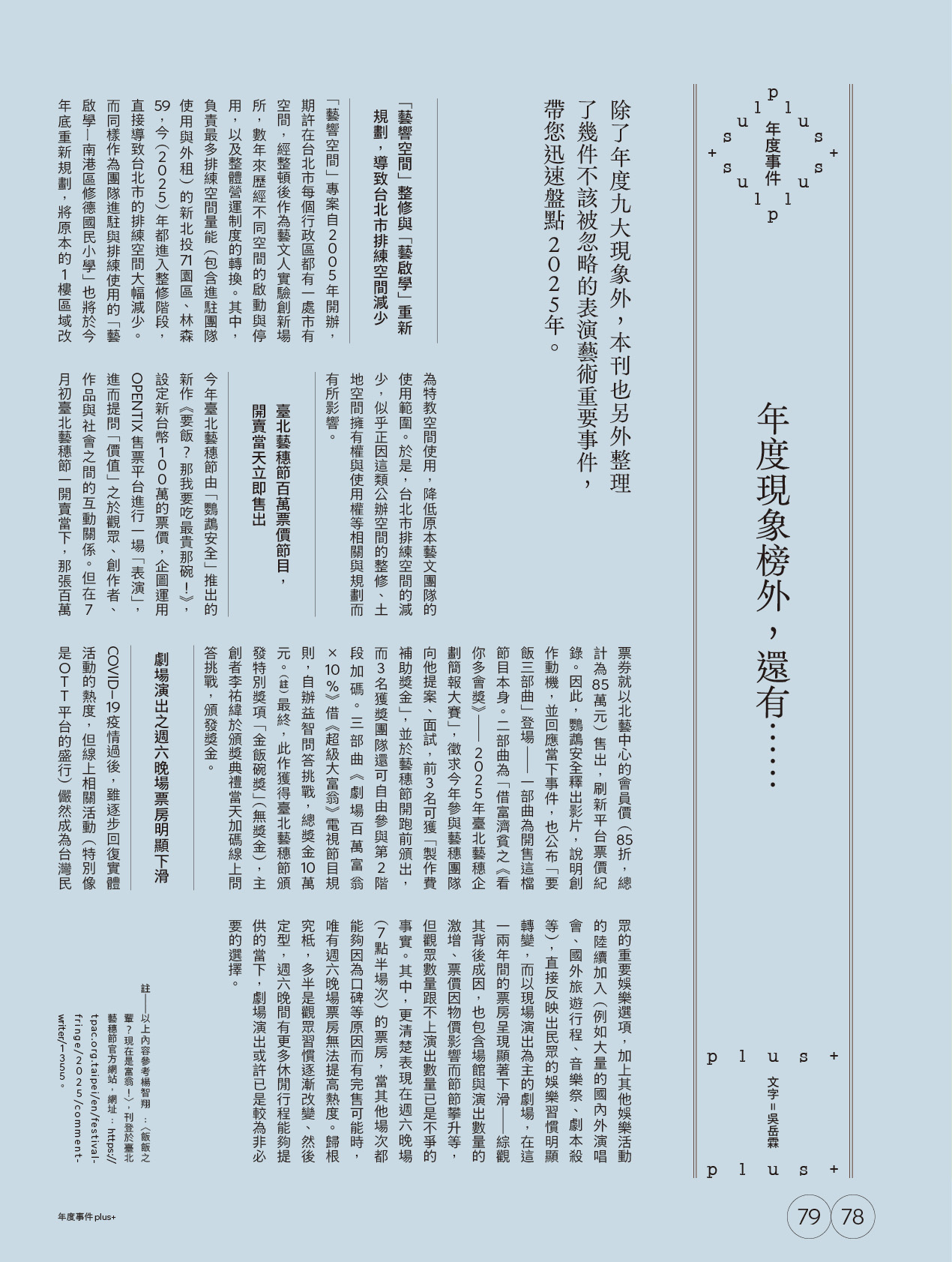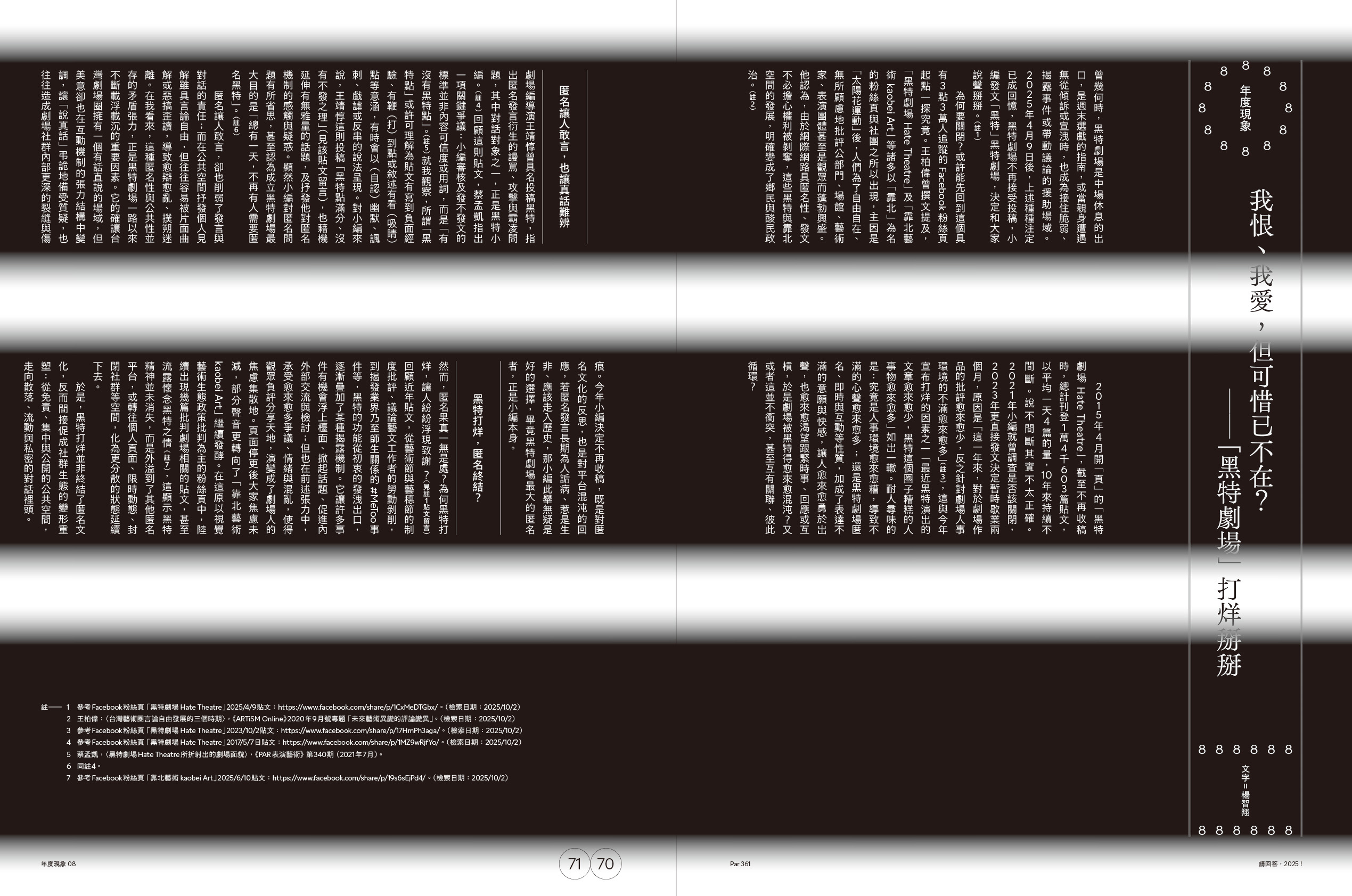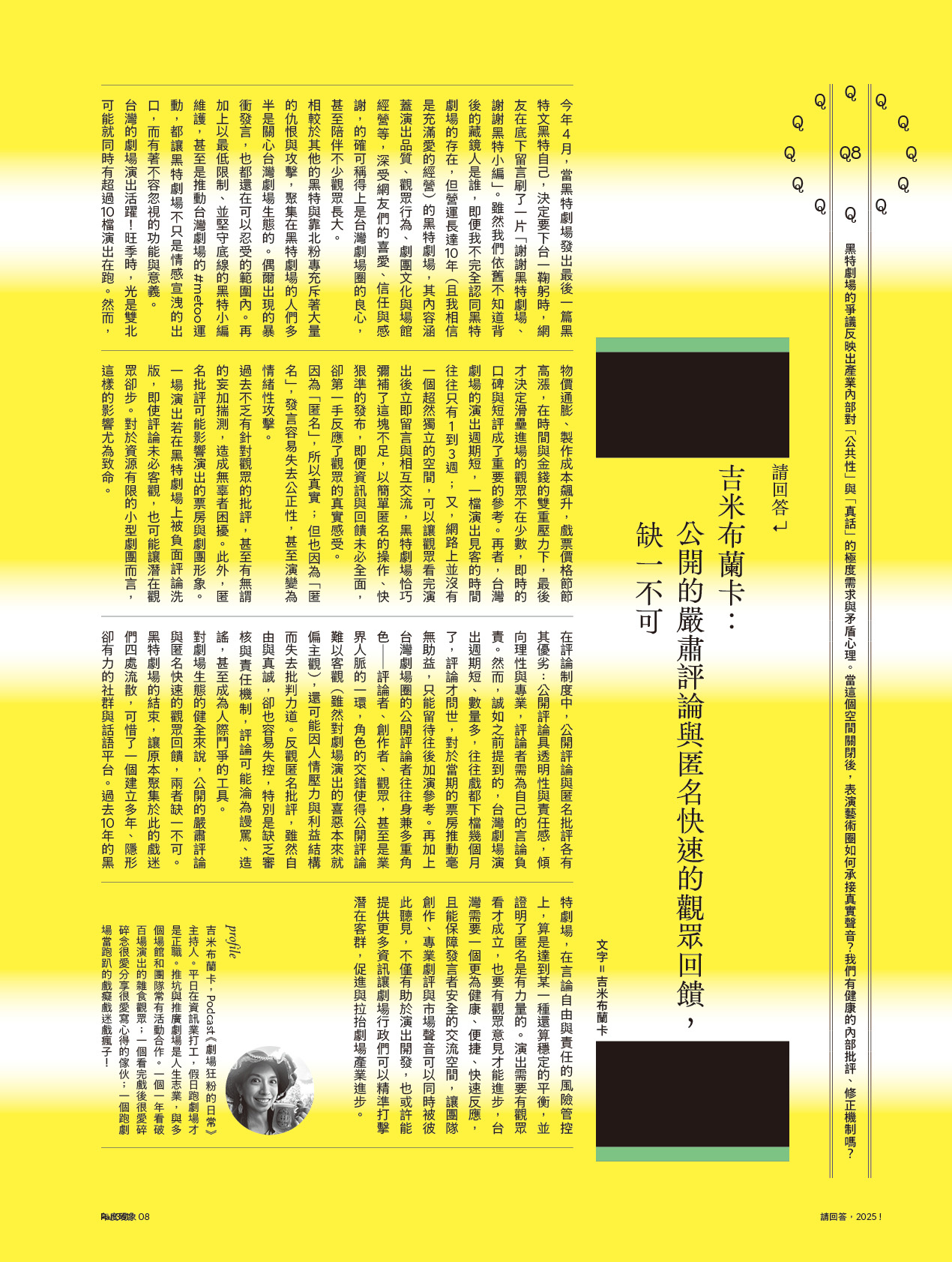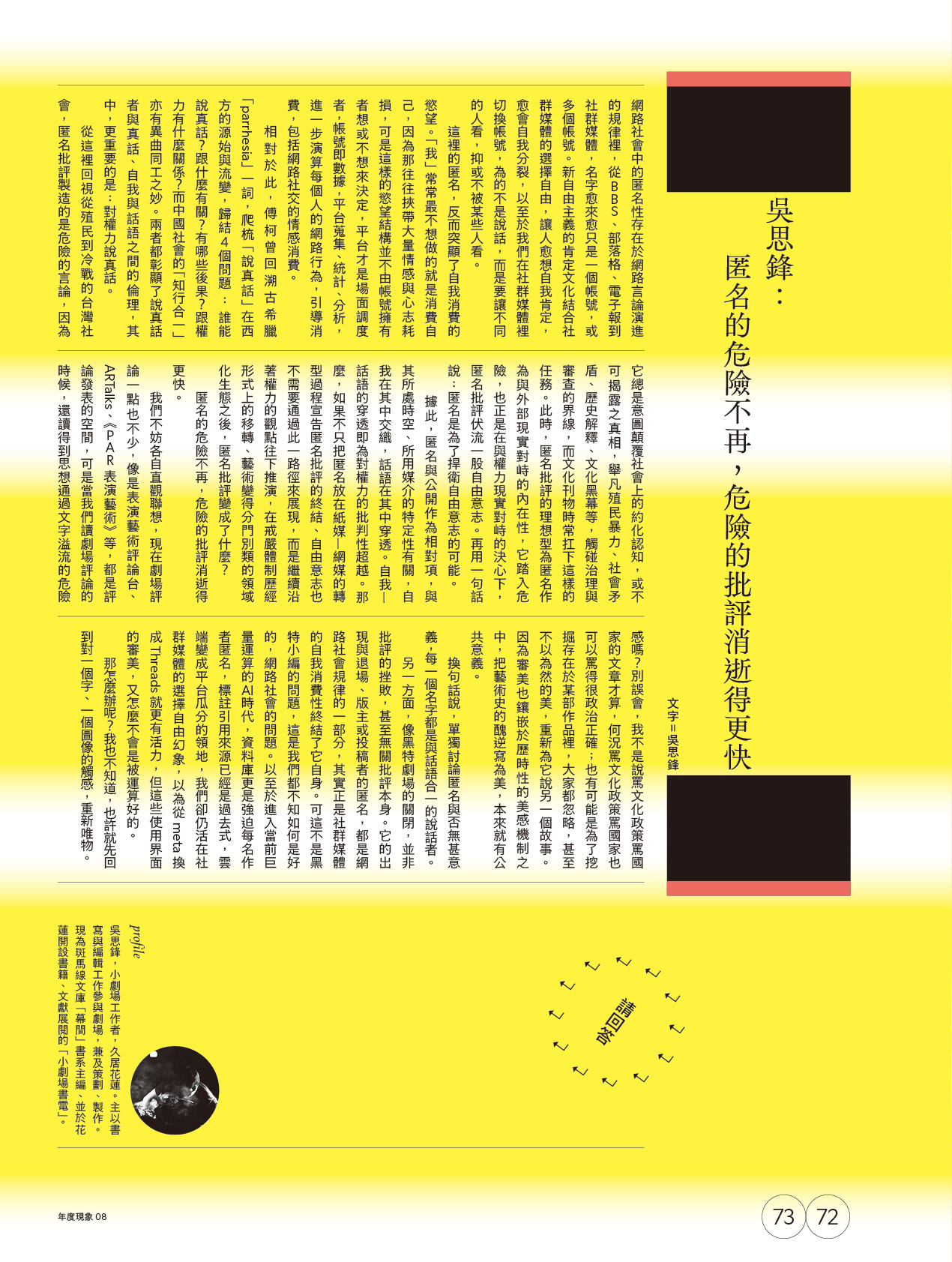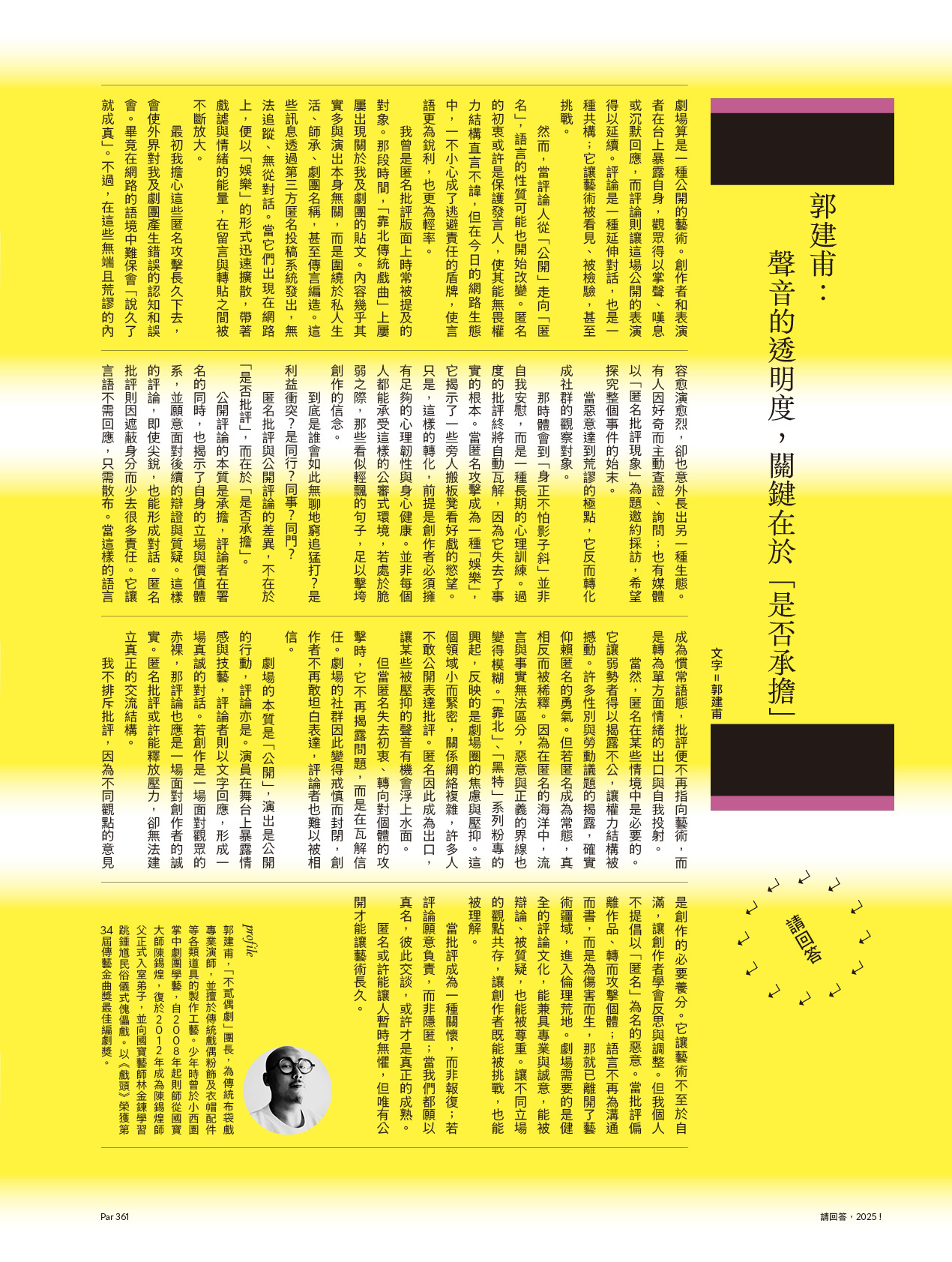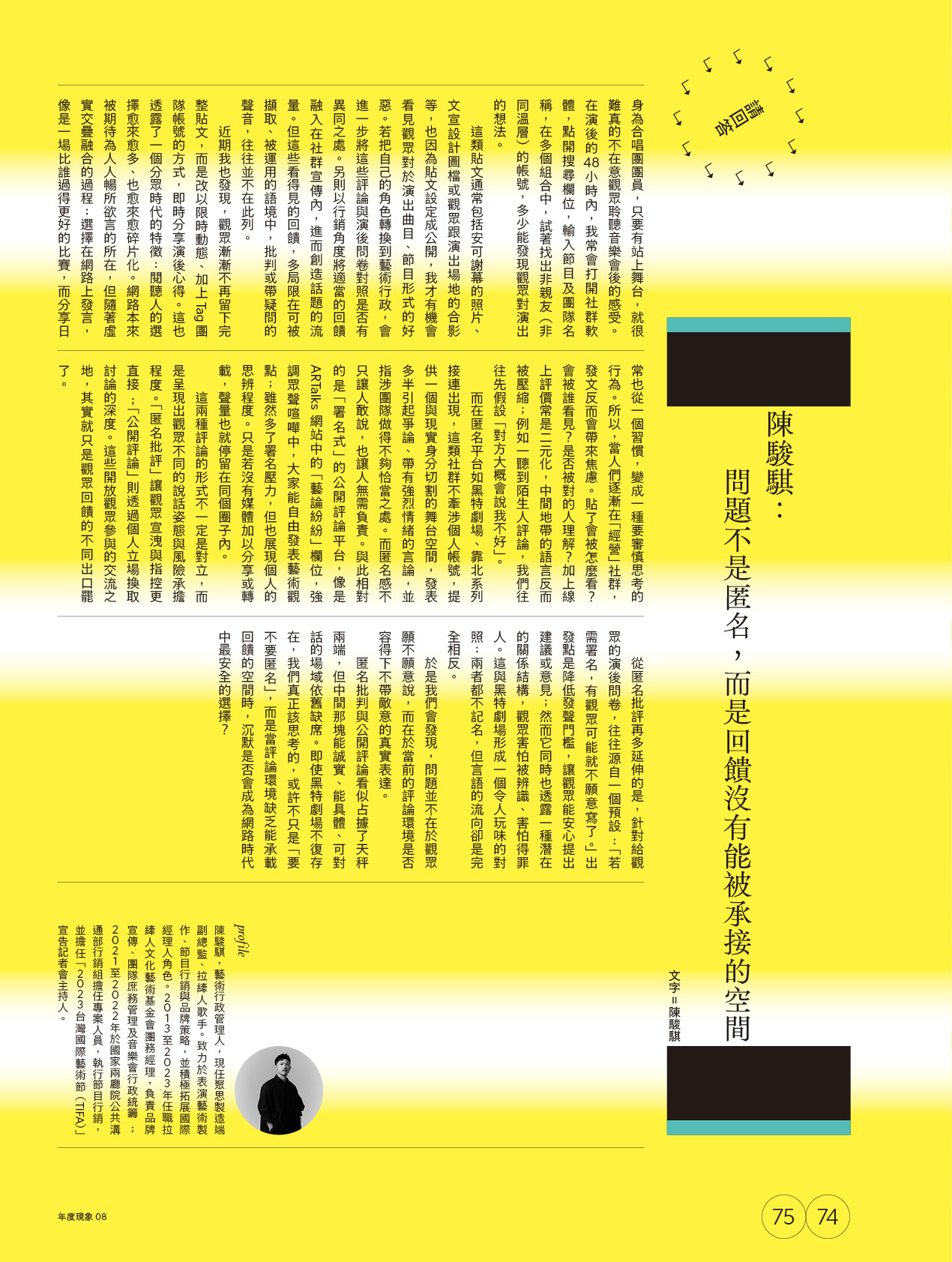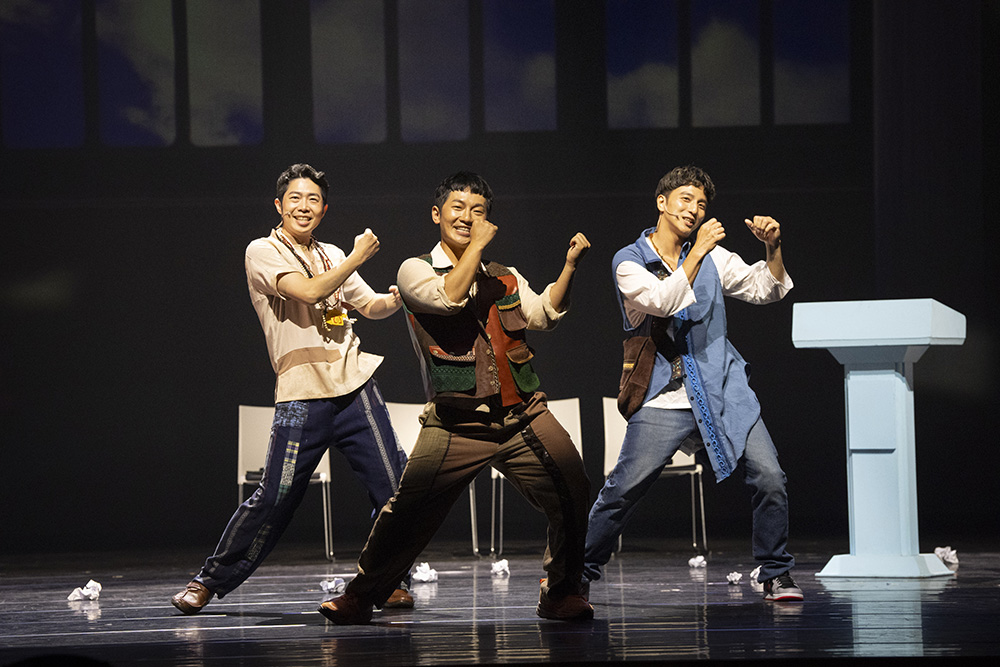特別企畫 Feature
寂寞,專注,且以相對低的成本打造一個渾圓飽滿的新生這是此趟SOLO訪問下來,我們試著整理出的3個關鍵字。
寂寞是演員,專注的是觀眾,且有趣的是,多數人同意他們最早想做獨角戲的初衷,是源自成本考量。
演員王世緯談起這些事情非常公開透明,成本絕對是所有人做戲的時候無法迴避的第一考量。事實上,籌辦「單人實驗場」的策展人李昀芷也是因為深知此事,才希望進一步降低年輕演員的負擔,渴望打造一個平台邀請演員講述自己的故事。
又,幾年前,疫情的波浪之下,劇場連齊心合力說故事的行為都被禁止,然而被禁止的身體卻壓不下更多好故事的念頭,於是如許哲彬引領的四把椅子劇團,開始與演員合作多部獨角戲演出,如膾炙人口的《愛在年老色衰前》、至今仍在巡迴路上的《好事清單》等。
起先,會說這件事情「有趣」,乃因在藝術文化產業,談及利益、金錢之事,弄個不好簡直就像是一句髒話,好像投身藝術中人,必然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最好篤信孔子所謂的「君子固窮」。不過,少有人能切身明白,資源、錢財其實並不與好的作品有所衝突,事實上,創作者腦中的宇宙的確需要等比的資金挹注才能夠搭建出來。這一點在獨角戲創作者們的討論中,時時刻刻被點出。
獨角戲,是我們不需迴避這個問題的第一步。
在某人的注視下,經過一個空的空間
當然,有的時候甚至不只是錢的問題,而是等不到演出的機會;有時候也非關才華的問題,而只是形象不對。在什麼場合需要什麼演員的理由千百種,無法一概而論。
同時,演員長年來作為一個被動的等待者,似乎像是等待兔子的蘿蔔那樣,兀自在土壤中肥大才是唯一選擇。
然而,獨角戲的存在其實提供演員另外一種可能如同魏雋展所說的,一個「自我賦權」的可能性。專訪中,他提及自己早些年想實驗不同的表演方法,若無人可問、無人指導,他找一處客廳、邀請同學兩三,一同觀看點評。
這樣的形式,單純得回到彼得.布魯克於《空的空間》所描述的劇場之定義:「一個人在某人的注視下,經過一個『空的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
(不只)一個人的戰場,解析獨角戲的方法論:導演X策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