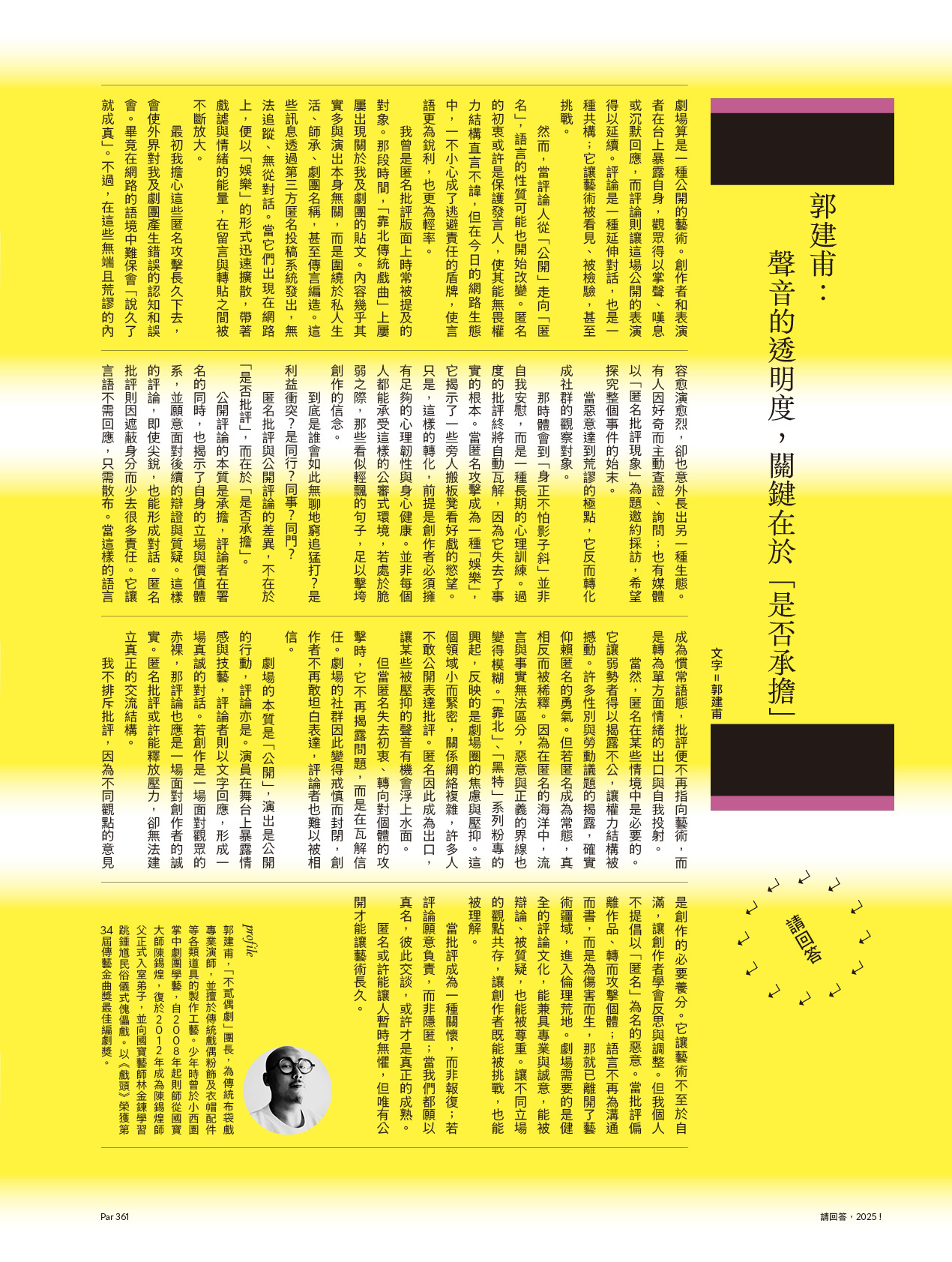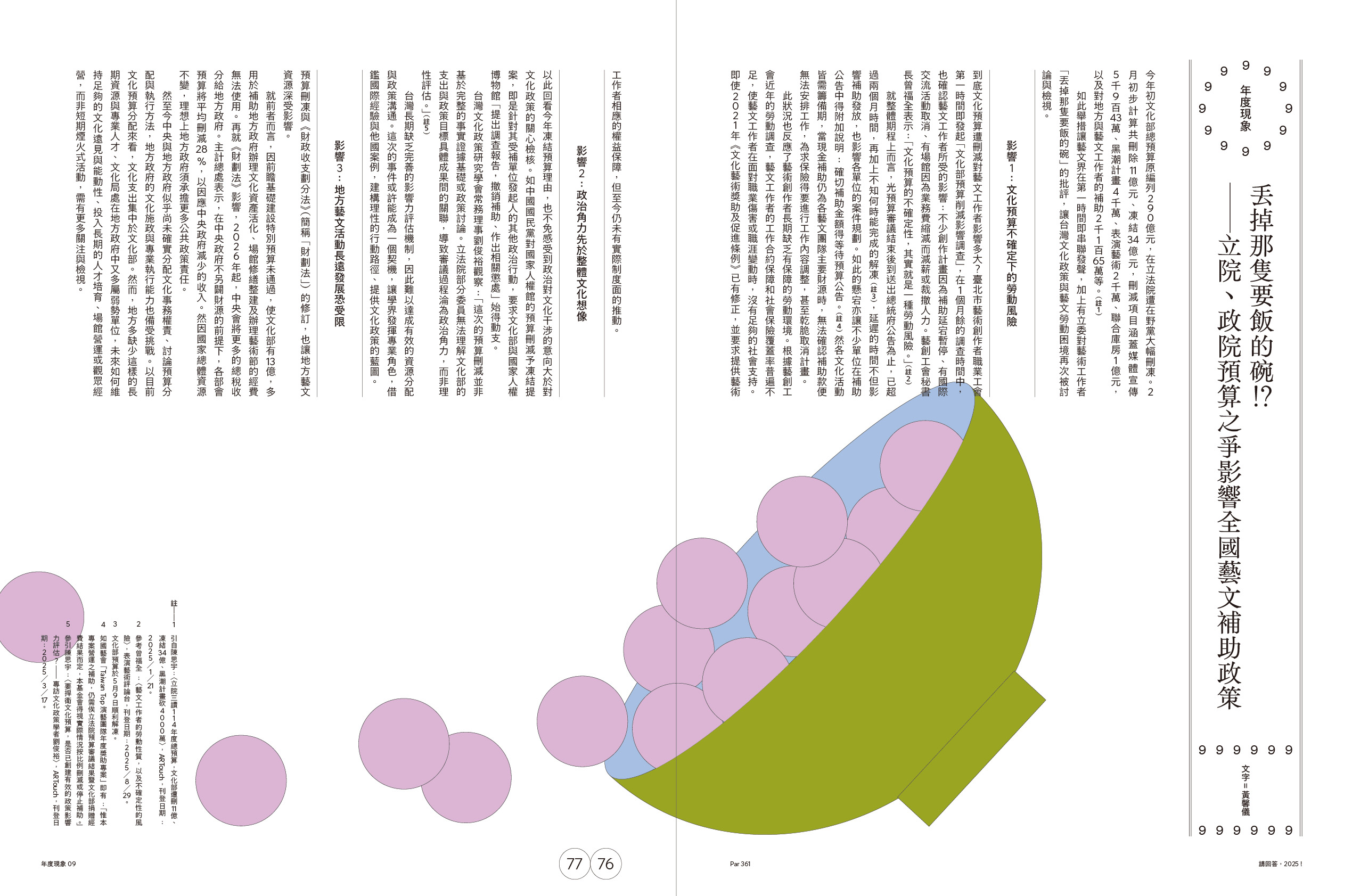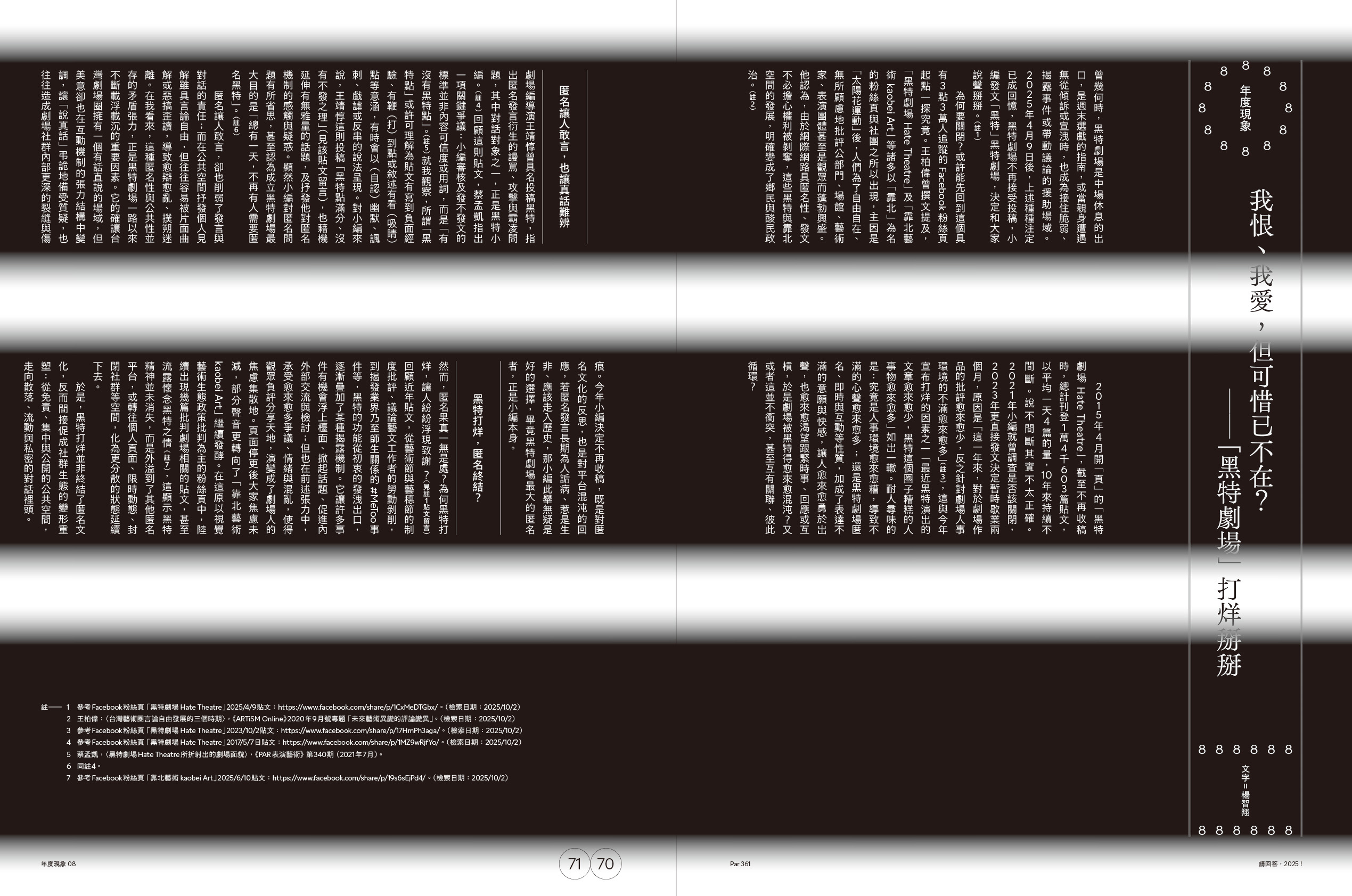以「地方」为单位的策展、艺术节╱季、音乐祭等,在近年蔚为风潮,像是今年下半年单就花东地区就有「台东艺穗节」、「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台东光祭」、「Taiwan PASIWALI Festival 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Palafang花莲跳浪艺术节」、「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等,横跨不同艺术领域与族群,主办单位也包含公、私单位。但,这些艺术节各自的定位为何?诉求的主题与观众是什么?真的与这个「地方」有绝对的关系?反过来说,这些地方艺术节又非得、或只能与这个地方有连结吗?
于是,本期杂志邀请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民担任客座总编辑,并作为对谈人,与甫完成2022年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规划的林昆颖,从一个「从未离开花莲的花莲人」与另一个「离开花莲许久的花莲人」的对话,重新开启我们对「地方」、「策展」与「艺术节」的想像。
时间:2022/12/08 10:30-12:00
地点:大稻埕
主持 黎家齐
记录整理 吴岳霖
Q:从富民的观点来看,怎么看待这些地方艺术节的策展?
杨:前阵子在一个叫做「地方创生的人们」的粉丝团里,出现了一篇高中生被老师带去北投参加某个艺术节后所写下的心得。他写说:「如果北投要办艺术节,我觉得干我屁事。『社区艺术』不过是一群文艺青年想刷存在,或未来要要找工作时,不要让他的履历表看起来很空所干的事,若是没有这些限制,还有多少人会跟一群伪善的政治人物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不仅浪费时间,还制造垃圾,相信我现代物品不会比原始人的骨灰还差,真的不行就是捐钱比较实在,让那些死妈死爸死全家的孤儿有个家还比较实在,别在那浪费资源了。另外,真的不是我在臭,毕竟要我写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没兴趣,而且没意义的活动,论谁都不会有任何心得,所以我只好实话实说。」
我会觉得,每次在花莲丰田谈「艺术」,好像有种时空错置的感觉,就是我到底要谈什么?就像我以前大学时候念文学,这样就会遇到很多不同阶段的质疑——文学可能可以为我带来什么,但很现实的的是,文学能为这个社区带来什么?我又用什么来服务社区的人?
于是,当文学、或是艺术并不是在它们最理想、最符合想像的空间发生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我作为社区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地方艺术节既然选择要到某些地方策展,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是重要的,就像很多工作室只是把工作室搬到农村,但是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我就觉得好像没必要。或者说,每次看到花莲的山东野表演坊在社区做剧场、在部落里办活动,而这些表演活动可以看到社区的故事,那个东西就有点主客位置的转换。我认为,山东野表演坊这种剧场创作就不只是为了创作者而做,而是为了地方而做。
我发现山东野表演坊在地方做戏的时候,是给地方的居民带来的新的希望。甚至也因此让地方的居民成长起来,然后开始有带导览,想说怎么样去做更多事。所以,我们在做地方创生计划的时候,就是想用跟我们不同的方式去推动,让艺术不只是艺术,能够成为社区营造另外一种更好的做法。
林昆颖
豪华朗机工共同创办人,华丽逻辑有限公司创意总监。近年担任台北世大运开幕导演群、台北「白昼之夜」艺术总监(2021、2022)、台湾文博会总策展人(2021、2022)、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艺术总监(2021、2022)。
杨富民
东华华文文学系毕业,现为社区工作者。任职于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专职社区营造与辅导、地方发展、青年培力及地方文化与艺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