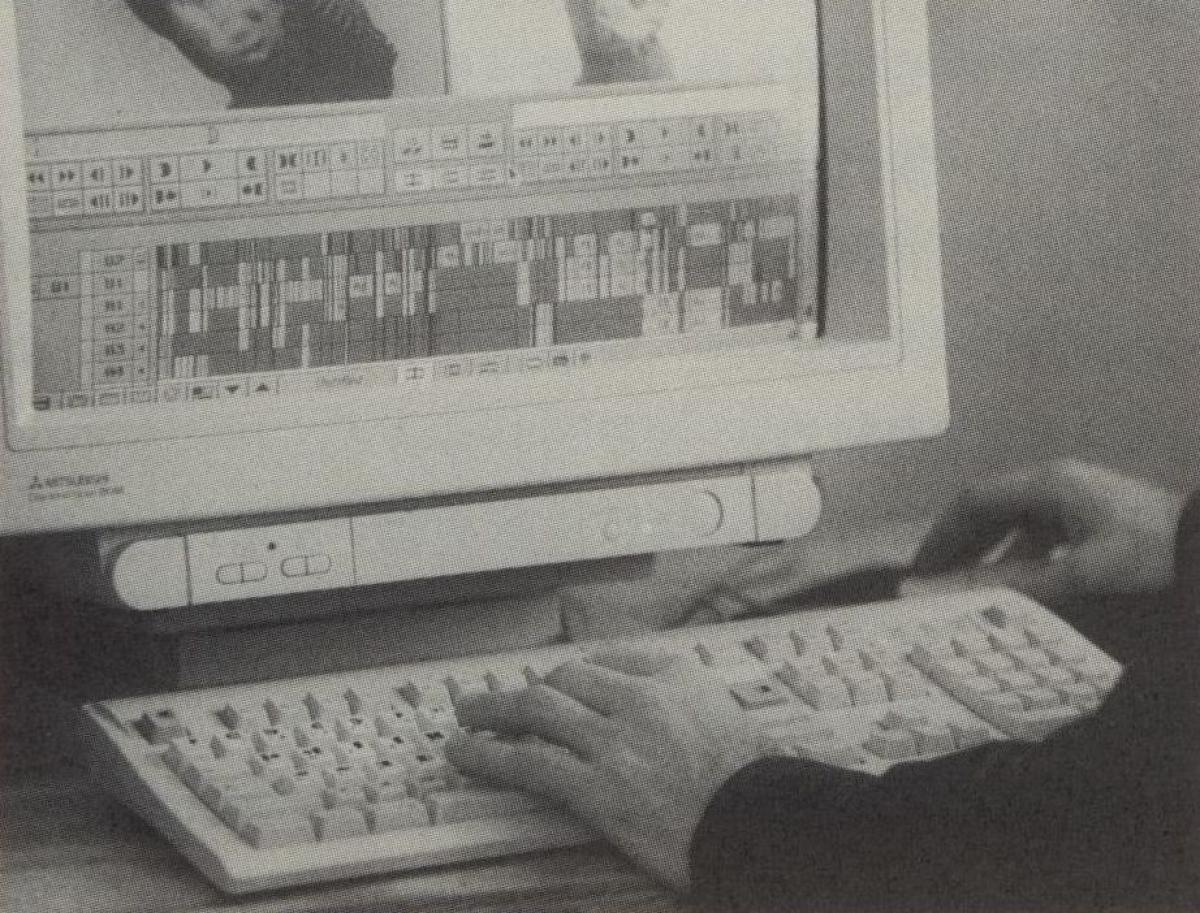原住民舞蹈鑲嵌在祭儀中,以影像的方式被保留下來,
其精神可被了解、傳達及尊重。
台灣原住民部落風情的影像紀錄,拍攝者多以文化理解的角度出發,試圖深入部落發掘山地族群的各個生活面向,諸如敎育、經濟、工藝、祭儀、政治等傳統過渡至現代的議題,而影片呈現時最吸引人的畫面,往往是穿插於這些議題中的祭儀歌舞。當我們進一步探討紀錄片所載的祭儀歌舞部分時,得先釐淸拍攝時是將這些歌舞片段視爲「祭儀風俗」而採集,還是視爲「舞蹈藝術」而保留?中央硏究院民族硏究所硏究員胡台麗,在民族人類學的專業領域中,曾拍攝了《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矮人祭之歌》等,性質上偏向采風紀錄的影片;而在擔任「原舞者文化藝術團」的演出策畫時,爲了讓來自不同部落的舞者學習其他部落的舞蹈,以攝錄影機拍了好幾卷的樂舞錄影帶,則偏向保存舞蹈藝術。
以下將以訪談問答的方式,請胡台麗敘述這兩類有關原住民祭儀歌舞紀錄片的構思、製作、拍攝等過程。
拍攝原住民樂舞的緣起?
我在受人類學硏究訓練的過程中,曾經對民族誌影片(註1)有長期的接觸與反省,影像帶給我的震撼觸發我去學習電影理論與技術。一九八三年我從美國完成學業回來,以排灣族的「五年祭」爲對象製作民族誌電影。在此之前,只有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記錄過此活動,因此我懷著極高的興趣,進入台東縣達仁鄕土坂村,拍攝了《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這部影片。
一九八六至八九年,我從事「台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硏究」的計畫,論文是以文字形式發表的,但是做田野時我選了七個族最重要的祭儀拍攝實況錄影帶,這些錄影帶雖然是硏究用途,我還是稍微剪輯了一番。但是這個部分的「歌舞」實況,重點在於它們如何嵌在祭儀中,而不是當作「獨立的」歌舞來看待,它的背後有個文化架構在。另外,在進行這個計畫的同時,我還著手拍攝一部紀錄片《矮人祭之歌》,以賽夏族北祭團的「矮人祭」十年大祭爲對象。
資料無限資源有限
這兩部紀錄影片的籌拍過程、機器設備條件如何?
八三年拍《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時,曾企圖與新聞局、中影、電視台(無線的三台)等單位合作,但沒有成功。後來意外發現中硏院民族所有一部越戰時期美援的十六釐米手轉發條式(Bell & Howell)攝影機,我在專業攝影師周業興的幫助下,了解如何使用這部機器,再添購二十卷一百呎的底片(一百呎約可拍攝三分鐘的影片)。由於當時紀錄片根本沒有同步錄音技術,我另外準備從美國帶回來的Sony Professional Walkman錄音機進行錄音。
整個「五年祭」祭儀活動共十天,二十卷底片實在極爲有限,每天只能使用兩卷錄影帶(約六分鐘長);錄音則用了二十幾卷(六十分鐘) 卡式錄音帶。當我在訪問錄音的同時,也一邊構思影片的劇本,再確定必要呈現的畫面。在這種片斷取鏡的情況下,加上機器的限制每個鏡頭都很短,後製作期花了許多時間剪接。錄音帶的內容請人譯出,我依據文獻資料和自己的田野紀錄,寫出劇本一稿,然後再補拍一些畫面。
八四年四月紐約大學電影系畢業的錢孝貞協助完成後續的工作,她利用碼錶計算畫面中聲音的長度,以達到類似同步錄音的效果。影片完成版本共三十五分鐘,拍攝率(以完成總長度除以花費底片總長度計)約三比一。
眞實文化與展演差異
八六年拍《矮人祭之歌》時,得到攝影家張照堂及電影工作者李道明的協助,以一部二手的同步錄音機(李道明自購)、CP十六同步錄影帶(向電視台借)進行拍攝。這部片得到中硏院民族所、文建會、柯達影片公司及台北影業沖片廠的贊助,拍了近兩萬呎的毛片,片子完成總長約一個小時,拍攝率十比一。由於有專業攝影、較充裕的資本,事前關於影片的設計與發想都可以較自由。
紀錄片中的歌舞祭儀部分,如何採集?拍攝者的觀點與選擇爲何?
前面曾經提過,紀錄片中的歌舞不能獨立來看,它們屬於祭儀的一部分。因此,當我們進入部落要進行採訪紀錄時,其實要面對的是原住民祭儀的神聖與私密,「紀錄拍攝」的介入與「外人異族」的參與,成爲雙方(紀錄者與被紀錄者)必須最先解決的問題。排灣與賽夏都允許我們將其歌舞祭儀拍攝紀錄,只是要求片子完成後回村裡播放。而我身爲一個紀錄者,拿著機器想要「忠實」紀錄原住民的祭儀歌舞時,得先完全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設想:以影像保留住祭儀歌舞文化,而不是單純因爲歌舞的藝術性,變成鏡頭下的「展演」形象。
其實,一個紀錄者投身的切入點、文化理解的程度,都將表現在影片的呈現上。舉例來說,祭儀中出現的舞步很單純,如果就慣常的「舞蹈展演」來看,可能會覺得它的重複與單一沒有結構可言;然而在祭儀中,單純的舞步並不是無意義的重複。影片的呈現有其限制(如長鏡頭到底或片段跳接的取捨),觀看影片的人不容易察覺這點,而這正是「文化眞實」與「展演」的差距。
貼近每支舞蹈的意義
兩部紀錄片之外,妳在擔任「原舞者文化藝術團」的演出策劃時,也拍攝了許多部落樂舞的影片,這與紀錄片有什麼不一樣?
「原舞者」的舞者來自不同部族,爲了學習其他部落的舞蹈,我們將想要學習的部落舞蹈拍成錄影帶,讓學員透過錄影帶來練習。歌舞鏡頭的取得不光是祭儀現場,有時候也請部落裡的老人家示範指導一些傳統古老的舞步。當然,這與前面所說紀錄片完整保存的出發點不同,對部落的人而言,只是擷取歌舞部分並且將其「挪做他用」─變成純粹的歌舞展演,則要另做考量。
溝通取得信賴之後,我們才以V8錄影機拍攝了一支支的歌舞片段。攝影時取景多爲全景,以特寫處理細部動作。不過這也牽涉到一個問題,我們並不是去模擬舞蹈的動作、外形,或只是傳達舞蹈特殊的美感,而是希望表演者能貼近每一支舞蹈的不同意義。
利用這些實況錄影帶,我們請平珩編寫舞譜,延伸出另一種形式的紀錄。總之,這些錄影帶內容都是來自不同部落的歌舞,爲了讓舞者學習用的。
回顧過去拍攝的這些紀錄片與原住民歌舞錄影帶,最大的意義爲何?
一直以來,在台灣拍攝紀錄片從經費到人力都必須面臨重重難關,我的經驗是「一路找經費」,幸而有如李道明這樣的夥伴以自己公司的人力及設備投入、共同製作,以及中硏院年度預算的經費可以彈性運用。當初拍攝這一部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經費只有十幾萬,雖然很辛苦,可是能爲台灣原住民祭儀及歌舞片段留下珍貴紀錄。漸漸地爲了紀錄片品質的提升,經費與設備都必須配合擴充,百餘萬元的投注也是必要。不過無論資金充裕與否,我們看到原住民舞蹈鑲嵌在祭儀中,以影像的方式被保留下來,舞蹈動作可供學習、欣賞,更重要的是原住民舞蹈的精神可被了解、傳達及尊重。
(本刊編輯 蔡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