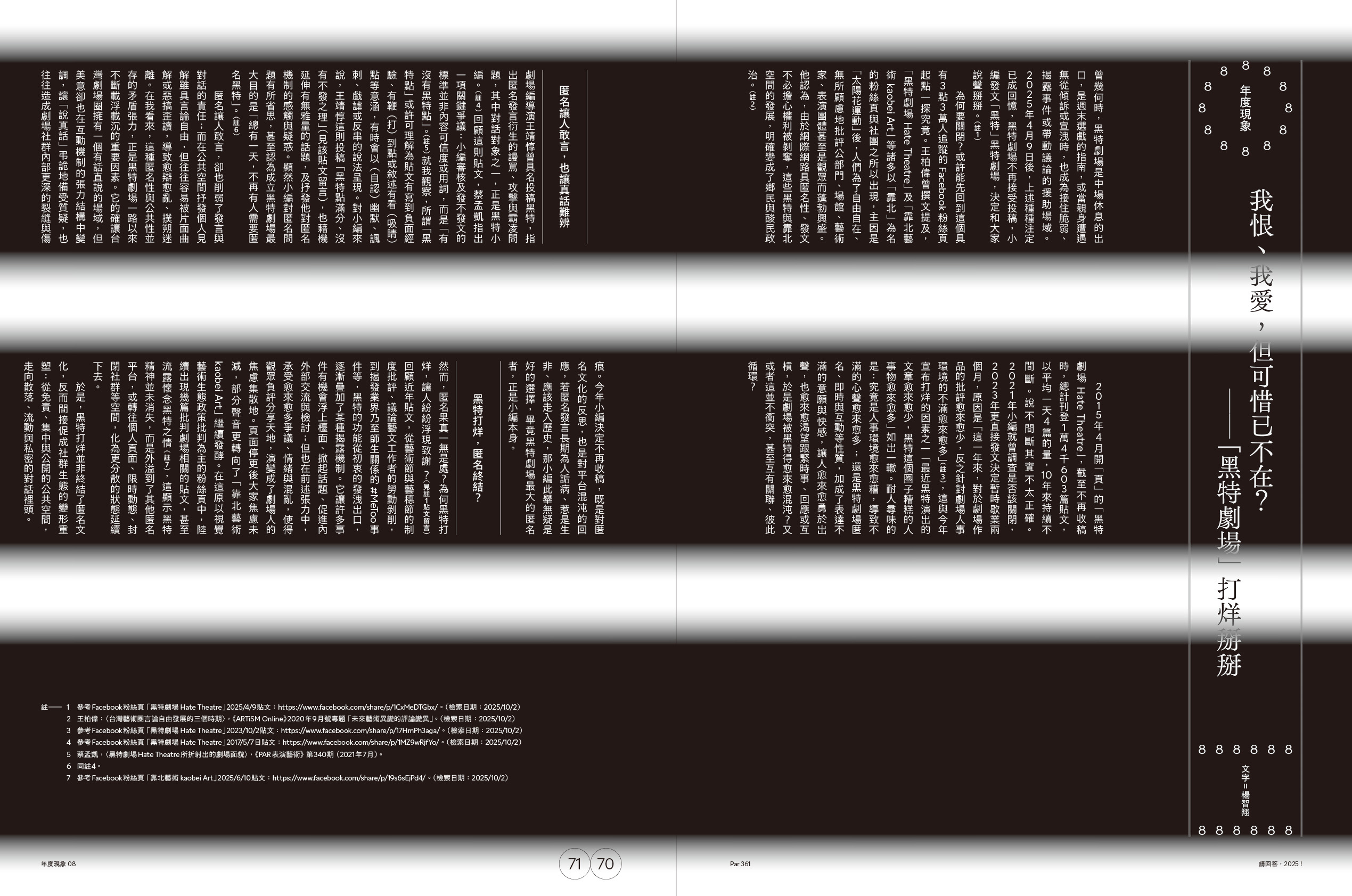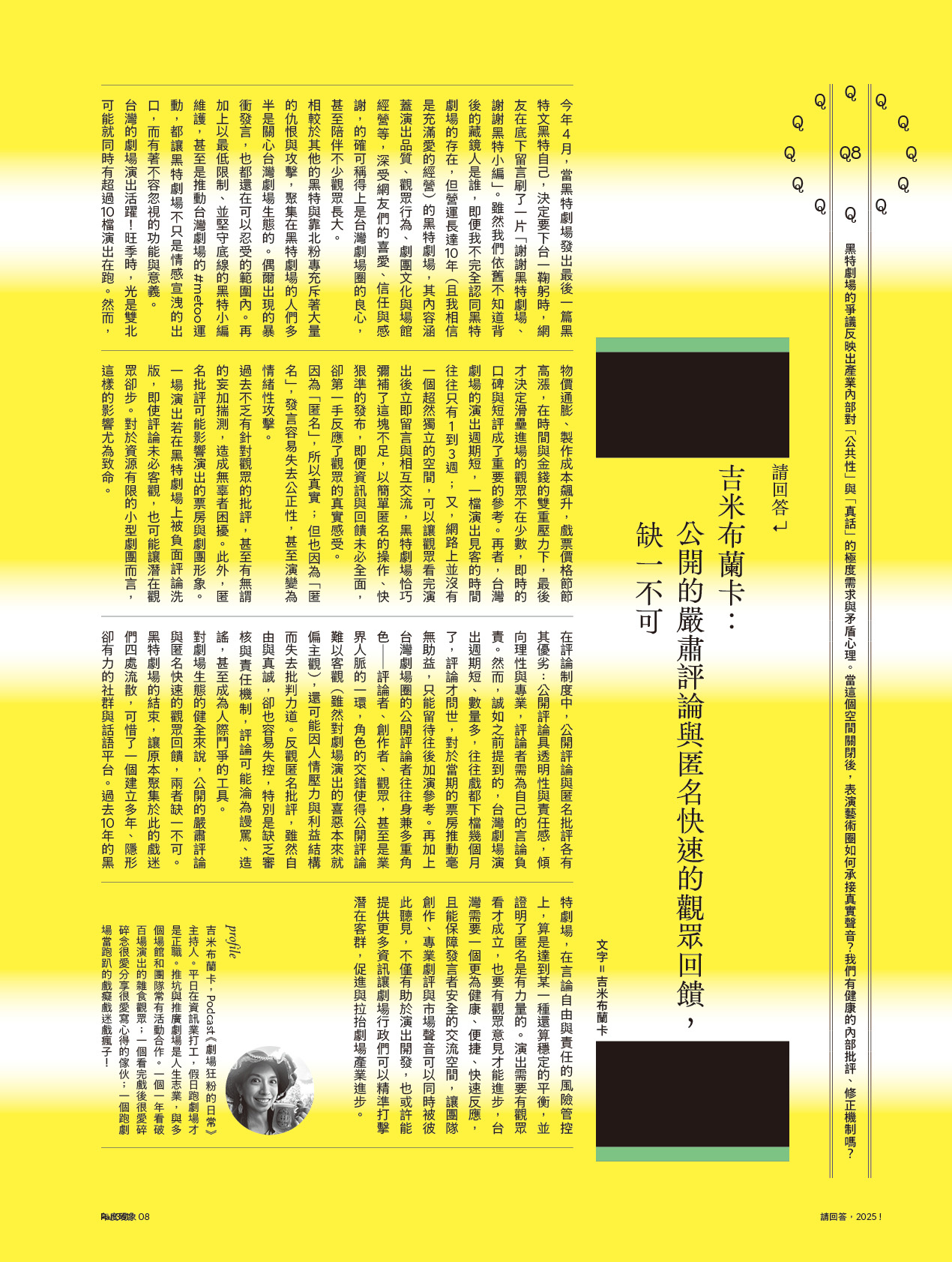真:我一陣子會開玩笑講說,我下輩子不要當長子了。
其實這件事情,你小時候不會去想,直到你人生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以後,才後知後覺地認為長子的成長過程,真的很不容易。不只是身分,也因為他跟你的性格整個連結在一起。
就像你知道的,我們家有5個小孩,小時候我爸媽都在工作,媽媽出門前隨口就會說:「今天會晚回家喔,傍晚你要先起火。」意思就是我要先燒炭,先熱鍋,大灶熱起,這樣媽媽回家才可以趕快煮飯煮菜。都是這樣的,我很自然就要扛起來這件事情。底下的弟妹都小,我跟大弟一人得照顧一個,但無論是誰犯錯,我都得一起捱罵——媽媽會覺得我沒有把大家照顧好。至於我好像也沒有抗拒,很本能地覺得,我就是哥哥,理當如此。
一直到長大以後,我算是家裡⋯⋯生活得較為「正常」的人吧?我不會說出色,就是平穩,正常,因此父母也最依賴我們。有些事情是真的蠻荒謬的,例如有一次,我爸打了電話過來,說他向廟裡捐了兩個龍柱,有刻了我的名字,所以要我付錢(笑)。就是這樣,所以整個家族不管誰出了事,所有人的眼睛一定轉向我。說得好聽一點,這叫做負責,但我認為自己不是因為負責任才去做,而是——若不這樣做,總覺得會對不起誰。
謙:其實我認為,真的影響你成為你的,不是因為排行的關係,更多是因為你的個性。不然你看,很多家族的大哥也不會主動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啊。倒是,我比較相信「占位」這種事情——在一個家族中,若有一個人「占」了最負責任的那個位置,那好像就會有另一個人往反向進行。不過,這種事情當然也沒有真正的平衡存在啦,總之,我認為跟排行沒有絕對關係。
真:這倒是,某些人的性格天生不適合當長子。這種現象,古往今來也看得太多了。像是企業接班也總是想要給長子,而無視工作能力極強的次子。
謙:傳統社會真的對長子有太多不公平的期待了。至於當代社會對於獨生子,好像仍舊也懷有一些刻板印象。像是我從小到大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小時候會不會很無聊?」但身為獨生子的我,真的從來沒有覺得這是問題,因為我非常喜歡獨處。再說,你記得我們小時候住的社區吧?在台北安坑山上,到處都是年紀相仿的小孩,敲個門就一群人跑出來玩。
擾攘的週末風景,都已成昨日光景
真:那時候真的是有夠吵,禮拜天大人都還在睡覺,外面就聽到「黑白黑白我勝利、七七乳加巧克力⋯⋯」。不過那真的是很好的一段時光,一條巷子敞開大門,時間到了就去敲別人家的門出來玩。我記得有次我很感動,某個週日對面鄰居來敲門,要我把巷子的車子移開,所有人的車子都是——淨空馬路,讓小朋友們盡情衝刺。現在很難看到這種光景了。
謙:所以獨生子這件事情,從來沒有成為我的困擾。另一方面也是從小家族內鬥的事情聽得好多,實在是太多了。人一多就難免出現比較、競爭關係。大概是因為這樣,我很小的時候就慶幸只有我一個,家裡只有我一個,好也是我壞也是我,這樣很簡單,若不夠好我只要反省我自己就可以了。同時,我好像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能相對以客觀的情緒感受這個世界。但這並不意味我沒有感受,只是感受未必都需要轟轟烈烈地釋出吧?
真:我少數真的會擔心的時刻,就是現在年紀大,也會想著如果我跟你媽媽都生病,你只有一個人,會不會很辛苦?所以後來才去買看護險。否則從前的確完全不認為只生一個的家庭有什麼問題。倒是,現在看你生兩個,我心裡只有佩服。照顧一個就夠累了,你們真的很了不起!
謙:我也的確是從我兩個孩子身上,觀察到很多我過去沒有發現的。比方說,對於大兒子來說,弟弟的到來必然使他的人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舉個例子,他上廁所開始堅持要關門,說不想被弟弟看見——哇,這讓我震撼不小,原來手足的出現,連帶產生的就是對於「領域」的鎮守。看著他們,會讓我覺得有很多人性本能的東西被回想起來。
真:兩個孩子在一起,也會看出性格上的差異。像是老二吃飯就規規矩矩,老大吃飯起來像是在打仗一樣。
偏心乃人之常情,但常情該如何釋放?
謙:他的嘴巴是拿來講話的,不是吃飯的。所以你說嘛,兩個個性這麼不一樣的放在一起,為人父母有可能不偏心嗎?一起做事的時候,總是有人做得比較好,而你必然會喜歡比較好的那個。我跟其他人也討論過,公平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即便如此,這樣偏心的意識也應該所在我們父母的內心,而沒有必要把它強化、翻出來讓孩子知道。我們喜歡這個吃飯吃得比較快、喜歡那個比較聽話懂事,心裡一陣喜悅,好像傾倒向哪一方,都是人之常情,但這樣的情感好好收著,我認為也是我們為人父母的功課。
真:人家都說寫劇本像是生孩子,我對劇本中的孩子(角色)倒是沒有偏心過。從來沒有因為特別憐惜一個角色,所以多寫他一點。倒是有件事情會影響我比較多,就是在寫本以前,就知道演員是誰。最早是寫《老莫的第二個春天》,製作方跟我說確定男主角由孫越飾演。演員一但確定,我筆下的台詞就會希望盡可能符合演員的說話方式。
其實,《人間條件四—一樣的月光》也是如此,我當時腦袋裡面想著的就是黃韻玲、林美秀兩個人,我們合作過很多次,若兩人再次一起走上台會怎麼樣?一對姐妹的畫面就浮現出來了。寫的時候說會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倒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演員的形象的確能夠帶著角色走得更深更遠,創造出屬於這個故事的調性。在那齣戲中,我最想表現的就是「得到最多資源的人,是否成為掠奪最多的人」。
我印象很深寫下的一句台詞是,姊姊對著海外歸國、看似一帆風順的妹妹說:「現在你有房子,還當組長,有信任你的主管,底下有可以指揮的人……還有一個會拉小提琴的男人可以陪你睡覺,可以弄到你哇哇叫…啊我有什麼?」對我來說,這種恐怖的吶喊,經常出現在台灣社會的家庭之中。因為家裡最優秀的那個孩子,的確需要其他人很多的成全,擁有一切的資源,最後就忘了自己怎麼走到這一步。
謙:這個論點,歸根究柢,還是可以回到我們最開始說的:與人的性格有關。以我為例,作為獨生子,我的確也是擁有你們所給予的很多資源的人,但不是每個擁有資源的人都會變得不可一世。我想,自卑或許是我性格中的原廠設定之一,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哪部分的能力再好,肯定都有人比我更好,很少會覺得自己超強的。無論有沒有手足,無論是長子或者是獨生子,人的性格還是決定了很多事情——甚或是大部分的事情。若從這個部分來理解,也許我們就不會把多數的悲劇推託給命運,而能夠回到自己身上,深深的自省。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