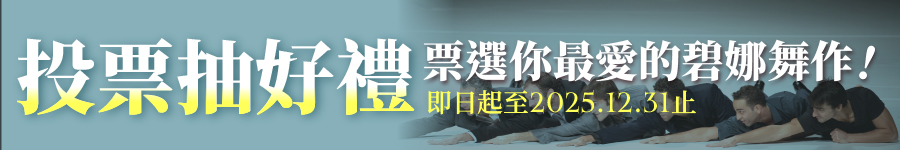傅裕惠
臺大戲劇系博士後研究、國藝會董事
-
台北
女人,如何不甘寂寞
當這些來自台東、台南,甚至背景源自台灣原住民,或是歐洲現代劇場、台灣傳統歌仔戲,甚至是現代小劇場的女性創作者,在劇場裡呈現他們對社會的觀察並提出人生的觀點時,也同時表達了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因此即使是「搔首弄姿」,觀衆或許能解讀出這群目前台灣最有活力的女性創作者,其背後所代表的女性價値觀。
-
跨台演出
「假」表演裡的「眞」人生
相較於以往拍攝電影一千多萬的資本來說,他原本以爲舞台劇排練比較輕鬆,或說,他以爲這件事可以只是他目前忙碌生活中的一項定期的進度。但與演員不斷磨擦、激盪的排練過程裡,陳國富發現自己還是陷入以往創作時的「失神」狀態;不論是搞電影還是排舞台劇,基本上都是創作,陳國富擺脫不了面對自己的壓力。
-
特別企畫 Feature
來自異地的振盪
單看郭文泰Craig Quintero的履歷,會讓人因爲這「層峰迭起」成績,而誤以爲他是硏究台灣劇場的一位學者。透過他溫文沈穩的談吐,很難想像這個來自美國德州的外國人,竟然在大陸台灣之間,風塵僕僕走了七、八年,甚至在九月中左右,還要自掏腰包編導他在台灣發表的第三齣戲:《開紅山》。 從這個額頂流血的宗敎儀式,郭文泰體會到任何社會的眞正改革,似乎都免不了要流血;如此深沈內化的感受創作,難得展現在這麼一位成長於美國外顯價値社會的靑年。去年他連續在差事劇場和誠品藝文空間分別發表了《出山》和《鍋巴》,其畫面意象的深邃與寧靜,被鴻鴻喩爲足以媲美貝克特劇作豐富的意境。不過,叫人好奇的還是他發掘中國文化的歷程。 他在美國芝加哥求學期間,就曾經接觸過李寶春等人,並曾在芝加哥的職業劇場製作《西遊記》裡擔任副導。偶然間,因爲扶輪社獎學金的關係,他開始到上海,日後也遠赴北京學習中文。郭文泰說,他待在大陸的時間,多半用來沈澱自己,跟廟口的老百姓們喝茶嗑花生聊天,沈澱自己的思考。後來一回美國,就發表了四齣劇作;接著,他又輾轉透過蔣經國等獎學金來到台灣文化大學學習京劇表演,接觸到臨界點劇團的一些團員,於是開始連結他在美國創辦「河床劇團」的團員,積極尋找創作發表的機會。 自認作品與生活沒什麼關係的郭文泰,其實相當重視創作的空間與沈澱。從《鍋巴》這齣戲厚實鮮豔的濃度中,或許我們會誤以爲是郭文泰身爲導演的獨裁。即使作品透露出濃烈的情感,但不慍不火的節奏,就如郭文泰對劇場創作的看法一樣,彼此需要呼吸的空間。沒有角色、劇情,沒有完全的文本對話,從腦海中的一個強烈的印象,郭文泰在創作過程中連結次序,透過溝通,沒有解釋,遵照自己的直覺呈現純淨的畫面。郭文泰以「總體劇場」的觀念處理自己的創作,他深信只要掌握戲劇情節進行的節奏,就能慢慢培蘊整齣戲的意象,促使觀衆在內省中體會他的創作企圖。 雖然思考與創作的過程像漏斗一般沈緩,郭文泰的實踐行動力恐怕不可小覷。今年年初,郭文泰帶著兩位朋友,頭上頂著圓形與方形立體的造型,買了票準備「參觀」北美館,挑戰藝術權威者對於藝術品的定義,在現場引發一股騷動;隨後,郭文泰還回美國與朋友策劃了Pioneering Arts Spaces「前鋒藝術空間」的活動。這名之爲《時光》的行動藝術表演,完全自發自主,只因郭文泰
-
戲劇
小劇場承受之「輕」
這次的「放風藝術節」並沒有創造出派出所劇場的人潮,或許背後有許多不爲人知的外力限制與難言之隱。如果因爲現實因素,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小劇場聯盟」即時發揮劃時代的影響力,那麼還是期勉所有劇場工作者,擺脫過去台灣小劇場的包袱與意義,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
特別企畫 Feature
音樂桃花源
基於對音樂聆聽的品質要求,曹永坤花了十年的時間耕耘自己的家庭聆聽室;由於完善的硬體及主人的專業素養,曹永坤的家中吸引許多音樂作曲者及演奏者前來表演,前來享「樂」的朋友常常坐滿二、三樓的樓梯、甚至佔領飯廳。
-
舞蹈
奔馳而不羈的創意
《非關慾望》所顯現的狂妄與露骨,讓我們領敎到一個表演藝術創作者創意的奔馳與不羈;溫.凡德吉帕斯與全體舞者毫不遲疑地表現對肢體直覺與創作直覺的自信,實在讓汲汲於所謂一點專業的藝術創作者,大開眼界。
-
回想與回響 Echo
誰的靑春?誰在塑造?
當靑少年的創意只是不斷地複製媒體輸送的資訊和印象,只能挪用媒體不斷拷貝過的形式和邏輯,除了顯現台灣美學敎育的匱乏外,戲劇專業知識不普及的情況,也幾乎到了令人挫折、憤怒的地步。長遠來看,若不在美學、藝術和人文科學方面的敎育加把勁,不設法開發年輕一代對美感和創意的自覺性與積極性,未來的台灣藝術,恐怕只有不斷繼續移植歐美、日韓文化而禁不起任何考驗。
-
特別企畫 Feature
反射内在的呼喚
溫.凡德吉帕斯創作時並不以「編舞者」自居,他的創作語言常來自與舞者嘗試直覺的肢體反射動作。《非關慾望》藉由精準的肢體技術,解放人性中潛藏的欲望。作品從許多不同的睡姿開始發展,進而展現一片令人驚異的想望冰原。
-
台前幕後
狂歡縱慾、翻騰人性
走過近半生,從事敎職十二、三年的馬汀尼,在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中,讀出了自己身爲台灣女性的成長心事;爲了實踐自己更貼近這片土地的心情,她將協同學校裡的年輕演員與設計群,要把俯瞰關渡平原的露天舞台,點綴得如夢似幻。
-
特別企畫 Feature
獎不獎,未定數?!
不是業者自立自發,不是透過經年累月與觀衆的溝通,所有這類的頒獎活動將會淪爲只是讓辦的人自己高興,而外界的人毫無參與感。如果戲劇圈的人,能夠主動地舉辦這類活動,來個內部大團結,打響這門行業的招牌,才會讓外人看得起。
-
特別企畫 Feature
在表達與生存間尋找平衡點
創作是爲了表達,重點在創作者所思所想;行銷關乎劇團生存,重點在觀衆之所欲。兩者之間未必對立,但總是會見到微妙的拉扯互動、時合時分,各劇團在此中如何求取自我安適的平衡點,同時考驗著創作者與行銷者的智慧,讓我們來看看,國內這些大型劇團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
特別企畫 Feature
日本東京新國立劇場
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分爲歌劇院、中劇場、小劇場的表演空間,已展開了馬拉松式的演出。
-
戲劇
好難揹的大書包!
許多參與貝克特作品演出的演員,都在歷經挫折之後,放棄動機和情感的分析,轉而投入外在肢體和聲音的摸索,反而把握了貝克特作品的神髓,關鍵就在於Simple(簡單)和True(眞實)兩個字。不知道會不會是陸愛玲想太多,想講的也太多,而讓這齣《無言劇》無法拔地而起。
-
特別企畫 Feature
變與不變中完成自我
從《海潮音》引發「道」、「藝」的拈提爭議,似乎將在劉靜敏安於自然山林的選擇之下,獲得平息;鍾傳幸《羅生門》大膽的風格,從女性自覺的角度擴展至編導對人性的關注;而《2000》與《KiKi漫遊世界》輕鬆明亮的色彩風格,魏瑛娟似乎不再陷於焦慮黑暗探索,反而超越人性觀點,走向超然。不論是劉靜敏的求「道」,鍾傳幸的求「變」,與魏瑛娟的求「新」,這三位女性創作者都在作品中轉化自身內在的焦慮,化爲對自己更上一層樓的期許。
-
焦點
他是我兄弟 賴聲川談達里歐佛
對許多國外觀衆或讀者來說,普遍對達里歐佛存有「左派」標籤的印象。在表演工作坊導演賴聲川的眼中,達里歐佛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創意、最精采的「劇場作者」之一。賴聲川認爲,若不細究達里歐佛的作品而斷然予以貼上標籤,將侷限達里歐佛在劇場方面的成就。
-
焦點
超越表演框限的掌中世界
自從五洲園布袋戲祖師爺黃海岱,以「劍俠戲」開創金光布袋戲的突破路線之後,其子黃俊雄以《雲洲大儒俠史艷文》的系列演出,擴展了布袋戲的電視格局。第三代的黃強華、黃文擇兄弟繼承父志,將家族事業轉型爲多元化經營,積極地使布袋戲朝向國際化提昇;八月底更要「攀」上國家戲劇院的舞台,與觀衆面對面地「接觸」。
-
特別企畫 Feature
是敵人,也是朋友
或許是因爲「緊張焦慮」緊緊伴隨著舞台表演的每一刻,這些戲劇演員們早已和「緊張」成了最好的工作夥伴,進而熟悉到忘記第一次「相交」的過程。不過也正是「登台亮相」的吸引力,讓演員在漫長的排戲過程中不斷面對自己、與人砥礪,以求綻放出最亮的光芒。
-
座談會
辣媽媽談辣媽媽
《特洛伊女人》的演出,讓觀衆親眼目睹辣媽媽的實驗劇場傳奇。當年影響蘭陵劇坊創立的Ellen Stewart,與觀衆面對面地敍述這樁傳奇的銳變歷程。
-
座談會
珍惜相互撞撃的火花
《Tsou.伊底帕斯》的演出,引發如何面對不同文化元素衝撞與融合的討論;此外,原住民傳統如何因應現代表演藝術而轉型,更是關心原住民文化者致力突破的目標。
-
名家訪談
無畏無懼無國界
我沒有什麼恐懼。我是個行動力很強的人,一想到什麼我就會去做;自從接觸劇場之後,我會把我的煩惱憂愁寄情於劇場創作。 劇場對我來說就像個大家族,而我就像個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