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在大學上課時碰到器材有問題的狀況,來自她學校的學生多半是第一個發現老師「求救」的哨兵,也常是第一個衝出來幫忙的救援。她的學生在團體演出中,也是很可靠的「核心」,他們懂得「眼觀四方」,對不意出現的「閃失」能立即補救、補位;遇上需要協助的後台活兒,他們也不會做壁上觀,總讓人感受到在「一條船」上的溫暖。這種以身教養成的「雞婆」,讓她成就了更有「人味」的藝術家。

沒有期望,就不會有驚喜;沒有開放平台,就不會有展現新意的擂台;沒有批評爭論的空間,就不會有真理的存在;沒有自由戀愛,就不會有真愛,更不會有令人欣喜的愛情結晶;以少數人的品味作為國家藝術政策與演出節目安排基準,更是不會讓這塊土地找到它深層的聲音。

文化是集體對「我」的認同,藝術是「我」作為個體的提升,歷史烙印著多少由個人抹煞自我價值而產生的悲劇和教訓,所以,在沉重地提出反思的同時,《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可貴,難得在於,即便看似只有花前月下,兒女私情,沒有生靈塗炭,逼害殺戮,但我仍能在有意或無意地擦肩而過時感受到,自由和自我的掙扎與搏鬥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花在欲迎還拒欲拒還迎的時間,加上後悔的時間,比相聚的還要多。

從一開始創建清單時,拉起觀察天線,揣摩摸索,提出疑問,也從犯錯中學習以及反省,檢查表成為劇場學習過程的累積。但也因為每一次的製作條件都不同,所以清單永遠從頭開始,也因為有了這個清單,經驗紮實地落實累積。而非事過境遷,故事一則。

所以,藝術工作多好啊,那位金髮妹妹,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培養了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瑞典的舞團多棒啊,大家因藝術工作的包容而受惠。這麼多年來下,我想藝術工作迷人之處,就是在於總讓我在工作中看到很多無法預期又無法衡量的價值!

若Stern的說法為真,少了文化觀點對流,也沒了文化學習目標,但是耗費著國家的財力與許多人的青春與心神,只是在追求把貝多芬演得「好」;雖然我個人超級喜歡這些音樂,也很高興國家提供支持讓我能夠學習並以這些音樂為業,但是對於國家整體而言又有什麼「正當理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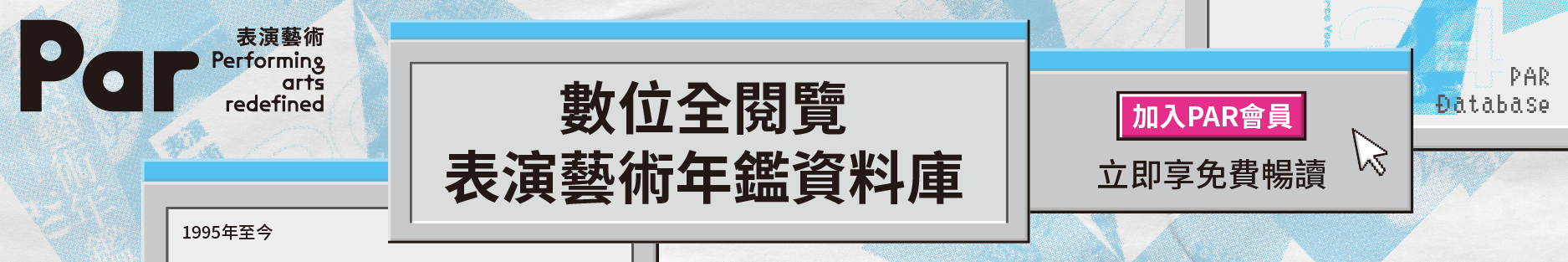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正是由於不能「一腳踢」,便必須借助各方有此才幹的藝術家們的幫忙,但統籌與導演是兩個崗位。前者是程序,後者是內容。所以,儘管我並不精於個別的藝術,但一定要認識它們在那方面能對作品發揮作用。由此百川入海,就是學習,也是決定要做一個怎樣的導演的必經之路。 從而體會,做導演,就是要做一個懷疑自己的人。

舞台監督在跟隨著導演與演員,或是編舞與舞者排練過幾個月的過程中,記錄下來所有演員的走位、細小動作,或是舞者的一轉身、跳躍、成群、落單等等舞蹈身段,更有的時候是音樂其中。最後賦予整齣製作生命的就是無數巧思安排的技術提示(cue),引導觀眾專注方向引發最終感動!透過一次一次地跟排,舞台監督累積與演員的默契,將「期望」建立為「預期」,一氣呵成。

有回演出前,行政經理好心想幫旅美的韓裔編舞家燙衣服,沒想到那小背心的質料遇熱就被熨斗黏住而馬上焦了一大塊,經理二話不說,立即抓起電話,聯絡服裝設計林璟如老師工作室的老師傅,擇要說明背心的式樣及顏色,然後殺上計程車,前後不到一小時,在開演前五分鐘帶回了一件剛出爐的新背心。這不但展現了行政人員平時累積的好人脈,更反映出她的機智和效率!

我真心認為「音樂」是種「另類飛行」「每次起飛都是可選擇的,但是降落卻是必定的」,就像「每次聽音樂都是可選擇的,但是曲終人散卻是必定的」。「獨立蒼茫醉不歸」,與古往今來大師、名家、知音的心靈交會,一種獨特穿越雙重時空的經驗,它將我們融入人類生生不息的歷史長河之中。

《相愛相親》銀幕上的人在據理力爭,我漸漸感受到有一種能量傳播到銀幕下,他們誰是誰非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們的努力溝通,使看戲的我也投入了當中的情感交流之中,銀幕上的人或許永遠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他們幫助我開始和自己聊起天來,由他們的問題,折射到自己的思想。

對於即將要發生的演出,一路的動腦、發想、發掘、探討、理解至精益求精的完善準備之追求,當你發覺有能力可以開始去預期、去預見未來,舉一反三地將面對的製作困難一一解決,也是真正能夠享受劇場工作的開始。


藝術行政,絕不是可以照著標準流程操作的公式化工作,而是必須將「藝術」與「行政」兼容並蓄的工作,至於到底是以藝術的眼光處理行政?還是以「懂得」的共識與藝術家工作?或者是用「藝術」的理想建立目標?這一切並沒有定案,只有不斷嚐試更好的做法!「藝術行政」最迷人之處便在於此。

藝術欣賞應是脫離自我踏上朝聖之旅,而不是把它強拉到身邊,合我可用者留,無利者退,並名之為「市場機制」,實則完全不解藝術對人類的「無用之用」。若沒了藝術的層次別,不認知境界差距,不視其高於蜉蝣生命之上如同淨心仰望的「空氣稀薄」聖地,我常會想,以我們對「夜市文化」的推崇,把「橙汁鴨胸」賣到路邊攤上的日子,將會不遠了!

現代戲劇的精神如果不能應用在行動上,有多少因素,是源於我們的文化習慣把戲全部當成遊戲,無須當真? 現代戲劇再發展至當代戲劇,文化的脈絡就更不容忽略。就是觀劇文化,也因時間對有著不同生活體驗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以致製造不同的觀眾和期望。有多當代,或現代,不只是戲劇形式,是思維。

表演藝術製作是一個團體工作,需要的工作技能可以規範與學習,但「人」卻是具備各式各樣的性格,及來自各不同社會層成長背景的養成。經過多年的種種不同製作的試煉,我一路以來每進一齣新製作,都會帶著自己的紀律,歸零的心態,啟動同理心,去理解未來要工作的團隊的需求,以及建立所需要的模式。而這模式每每都會不一樣。我也同樣地透過每次的進程,持續學習。

藝術行政到底和一般行政工作有何不同?藝術行政到底教了我什麼?回看種種,無非是一連串的自我思辨,及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中,尋求最大的可能。取個名字是如此,「抗拒」老爸是如此,「出國演出」也是如此。藝術行政,重要的或許是「藝術」那兩個字,更重要的或許是藝術中的「創造」精神。

當下台灣樂界主流仍是「追上西方當代」居多,「混合風味」次之,一九三○年代前面那些老輩們的論調「兼容並蓄」、「融合古今中外」則已經乏人提及。盛開在柏林、紐約的花朵,我們試著要讓它在台灣落地生長,「混合風味」或「民謠編創」被嫌有著「土味」不適合輸出,二者之間沒有漸層光譜,也無自省反思。


人都很複雜,但不就是因為這些複雜性,才使人生被比喻為戲?怎麼很多時候走進了戲劇世界,觀眾反而被扁平化了,就算當上「主角」,也只是被控制的偶,而非被重新發現的「我」? 創造觀眾,其實是不斷追求不想與你交心的人發生愛情。辛苦背後,是我作為戲劇創作人對於這個「愛人」的未知的無限好奇。

最近最深刻的經驗,是剛剛完成的二○一七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開閉幕式,整個過程,讓我深深領悟到跨世代的共事是目前表演藝術界所有人的一門重要功課,必須要學習,管道需要建構。所有人的成長都因為何時生、生何處開始建立,這個主要因素也就造就了每一個人之不同。我們需要建立看見彼此差異的能力及如何互補或互閃的事實。並認知到除此之外,前浪或後浪,我們當下都是平等的!

舞蹈人首先學著依附音樂起舞,然後學著與它並行,再又獨立地拉出彼此的空間來。所以音樂對資深舞蹈人來說,就像是他舞蹈中的另一層皮膚一樣,因為對大局的了解,所以他可以選擇自由進出音樂,和音樂起舞、狂飆,進而帶領音樂,等待音樂,遠離音樂,對抗音樂、甚至忽視音樂;所有的反應都在音樂一發生時就已經開始。

我是如此散漫,又是不知不覺對表演工作,鍥而不捨地做了四十五年了,我的前輩一位位地走了,消失了,我也快了,不知道什麼叫悲傷,也感覺不到什麼好喜悅的,有戲就去演,沒戲就休息,一直到老無悲無喜回到我年輕時喜歡過的那句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每個看過《CSI犯罪現場》影集的人都知道,一根頭髮就可以揭開一個人的死亡線索。這兩位美國的貝多芬狂熱分子顯然看過這個影集,因為在他們買了頭髮後不久,就把頭髮送去做分析。這下子,狂放不羈的貝多芬頭髮終於在他逝世兩百多年後讓真相大白,原來他是死於慢性鉛中毒。 法醫總是會說:「頭髮不會騙人。」但是,只有我是受害者,所以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道生一,一分 ,上天下地,上面的圓弧為天,下面短短的橫線,為指「地」的指事符號,意思是往下、朝地的方向。下,是讓飛在天上的概念、有深度的理論或很有感覺的心理詞彙落地,天上飛久了會自以為客觀地鳥瞰、一目了然的錯覺,或有不被眾人理解,獨愴然而涕下的封閉孤絕感。劇場導演即是如何具體地勞動,將其平安地降落地面,才是關鍵。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