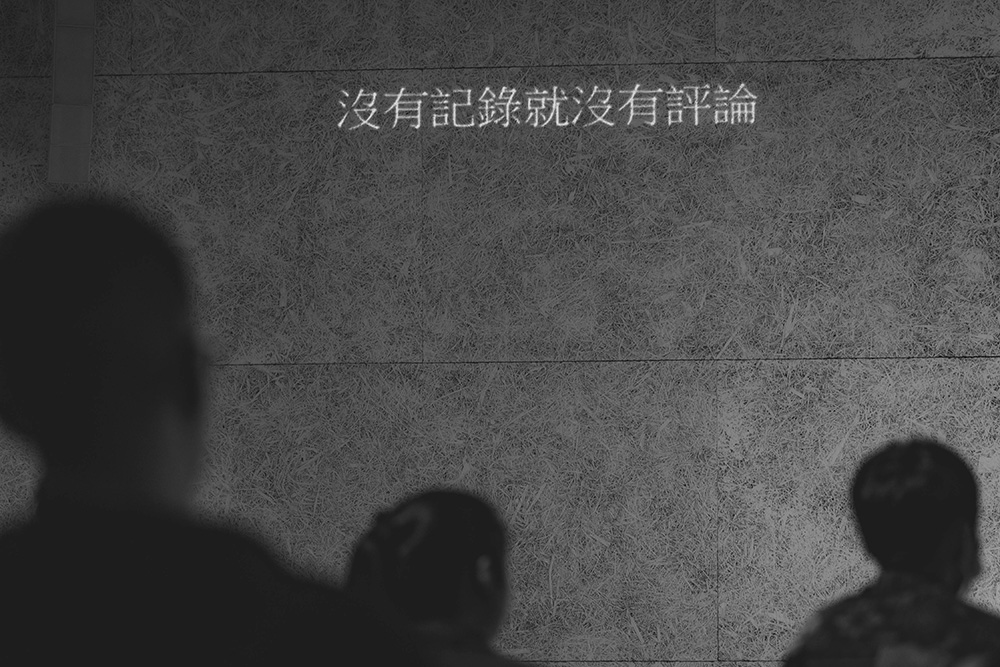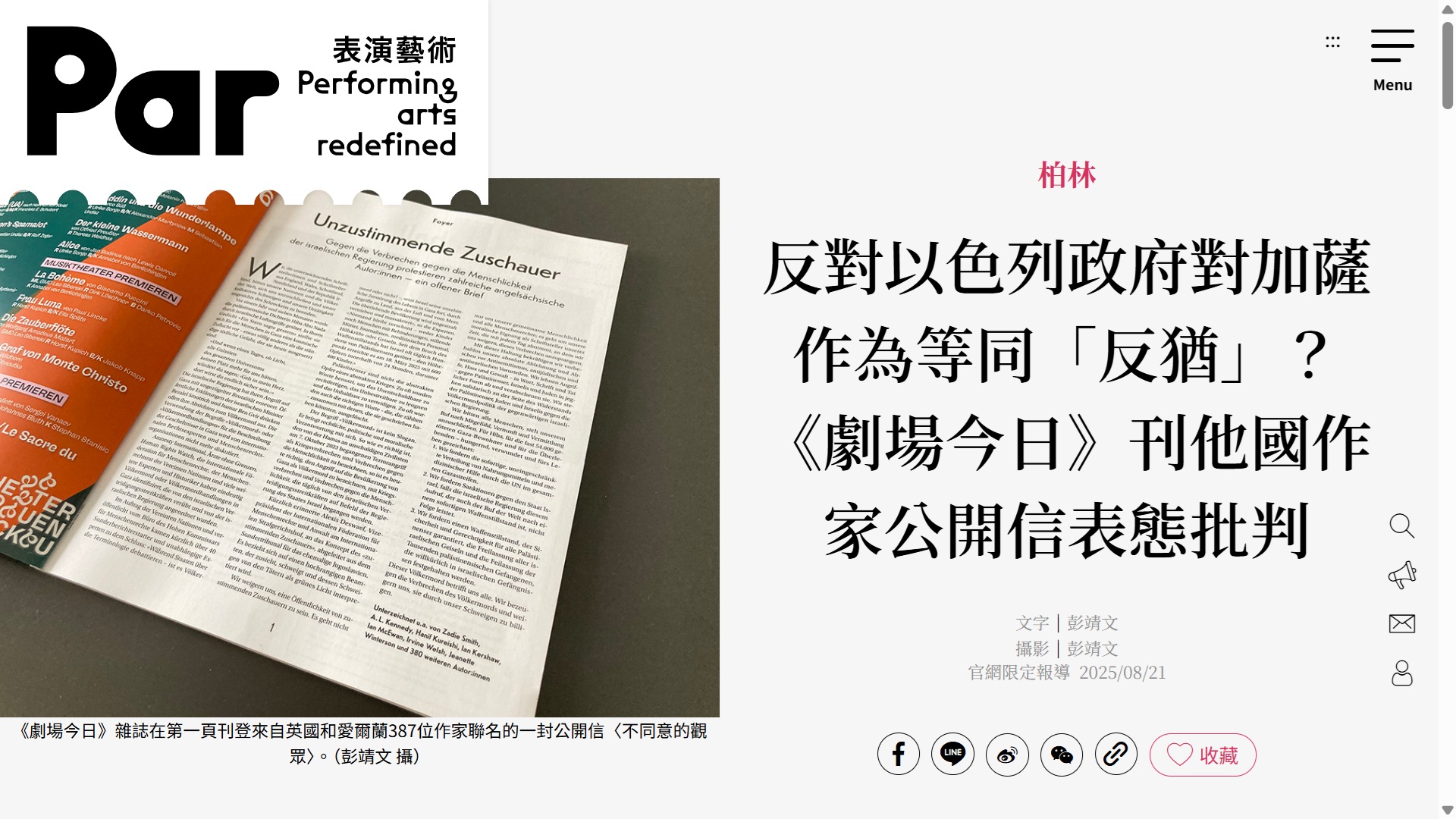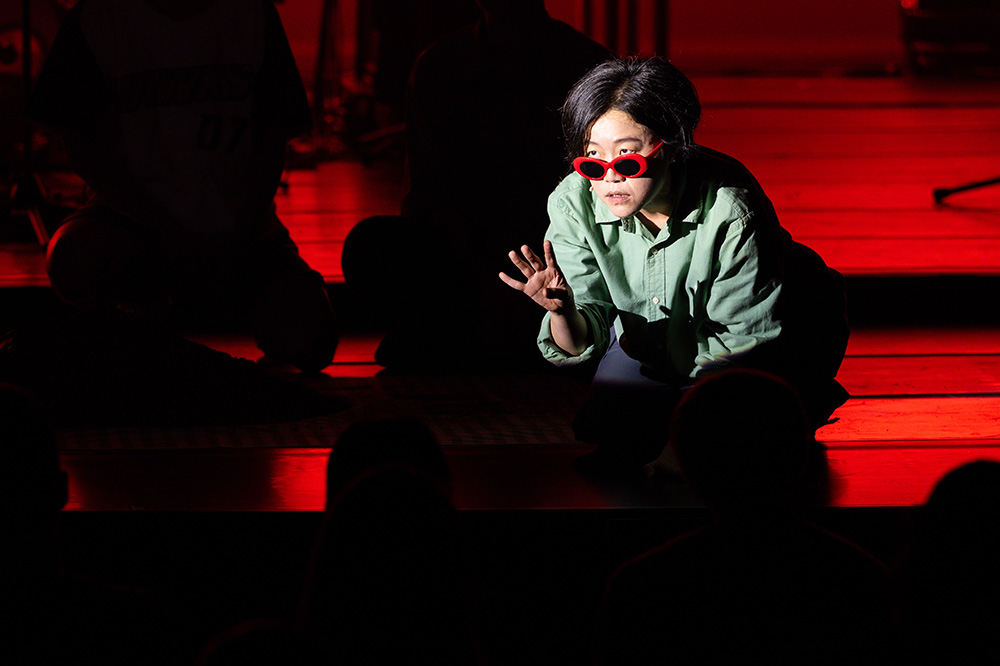歌仔戲粗腳的男性浪漫風景
評鴻明歌劇團《華容道》《華容道》是歌仔戲資深粗腳(tshoo-kioh,指老生、花臉)演員呂瓊珷編、導、演之劇目,原為《赤壁論文.華容道》,屬其家班國光歌劇團擅演的粗腳戲。此劇曾由國光歌劇團兩度公演、戲曲學院師生聯演,皆由呂瓊珷親自飾演曹操。2020 年、2022 年更名《烽火一聲笑》,當時擔綱關羽、曹操的戲曲學院在學生,即為本次「承功」版《華容道》的主演新秀吳承恩與協演鄭力榮。 本次因應節目時長,選段《華容道》,並增編《借東風》,由吳承恩一趕二飾演孔明、關羽。呼應京劇「群、借、華」有一趕三之例,此安排顯示出挑戰文武不同行當的企圖。同時標誌呂瓊珷的粗腳藝風,多有京劇老生、花臉的表演技巧,做表濃烈(包括髯口功)、嗓音厚實、行腔強調頓挫,尤其是古冊戲中包公、蕭何、公孫杵臼等角色。 歌仔戲身為百年前的新興劇種,向傳統劇種取材,自然順理。時至今日,專攻粗腳的演員,卻愈來愈稀有。劇團多以女小生為當柱(tong-thiāu,當家),隨著劇種演化的進程,粗腳退居配角,主演的戲齣也日漸減少。加上男演員整體比例偏少,而女演員缺乏嗓音、體型等先天優勢,難有勝任粗腳者。現在,粗腳的角色可由其他行當兼任或轉任,表演也兼 容各異其趣的風格,以齊備角色、完成演出為任務,粗腳行當的獨特性已不比過去。專為粗腳經營表演空間的戲齣,如《華容道》,更難得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