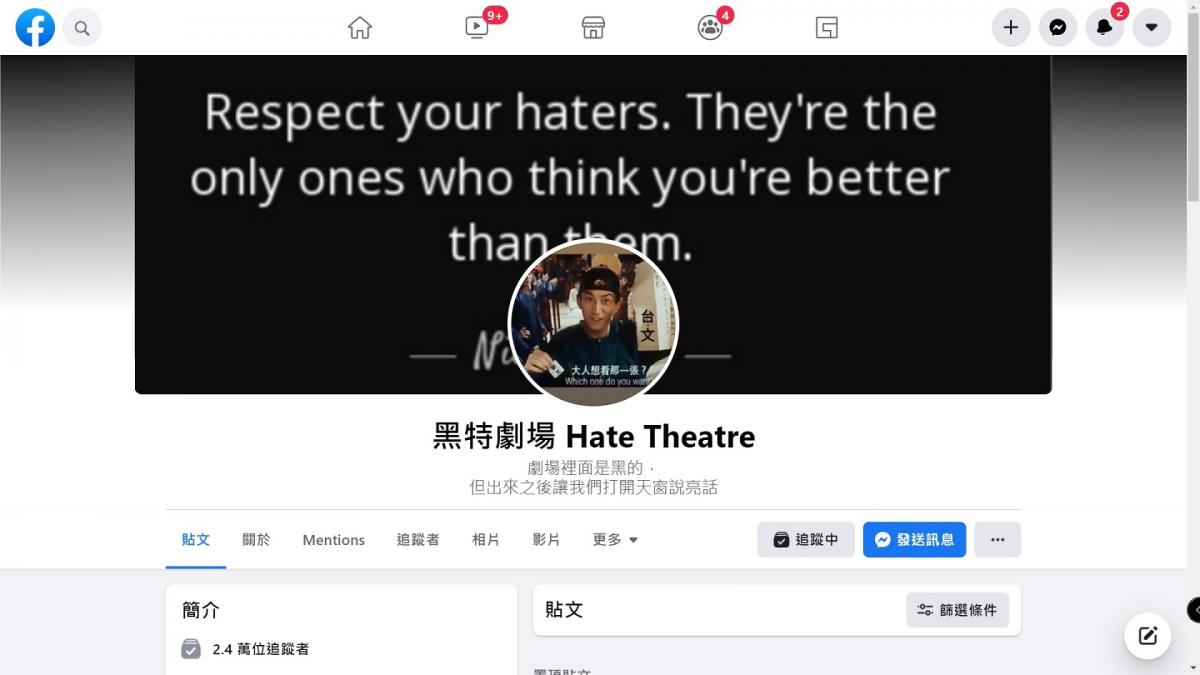當代演員劇場的「傳承」:從當代傳奇劇場的科技京劇談起
時至今日,我們對京劇仍有「一桌二椅」、「演員劇場」、「抒情」、「寫意」等理解,但在當代創作裡確實已不是不可推翻的定律,於導演、舞台美術、燈光等現代劇場編制介入後,多數劇團都重新詮釋、或回應京劇的美學,在劇本、表演等方面產生質變。去年年末,「科技京劇」成為另一個話題。(註1)事件本身已暫時落幕,此議題的發酵或偏離主軸、或正中核心,都有待時間檢驗。但記者陳宛茜當時的報導文章〈傳統戲曲擁抱高科技 失原味恐四不像〉(註2),將當代傳奇劇場《蕩寇誌之終極英雄》全沉浸體驗展(後簡稱《終極英雄》)拉入批評行列,倒出現根本性的謬誤:國家劇團與私人劇團對「傳統藝術」的態度,是否有本質的不同?在此「不同」下,兩者就算都以科技為創作走向,背景與目的能否歸於同樣探討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