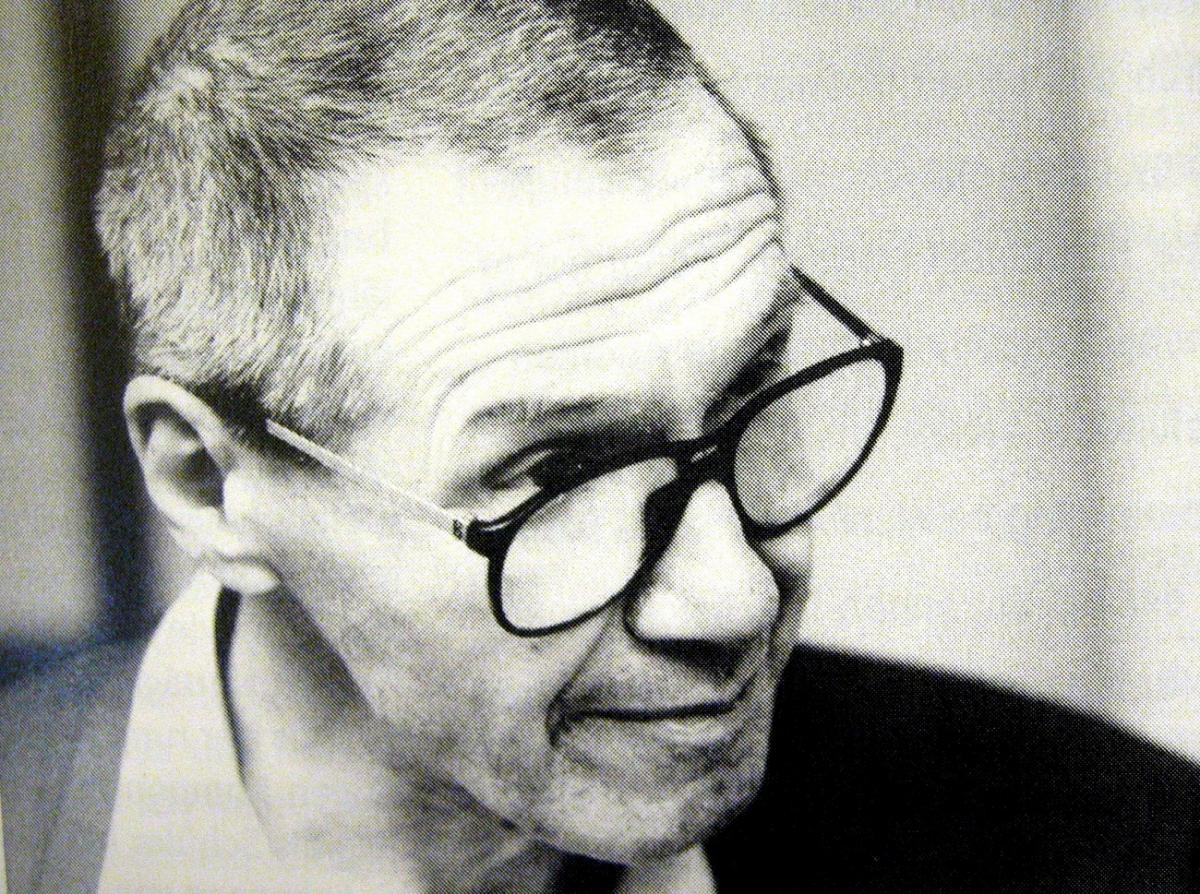小说的原生地在书场,其表演的、大众化的本质对戏曲艺术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和启发。正如小说不畏冒犯正统历史一样,具有独特表演美学的戏曲也不会拘泥于小说,尤其是当代的新编戏,为了揭示创作的意义,对历史、小说的解释权不遑多让。
国立国光剧团《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5月23〜25日
台北国家戏剧院
戏专京剧团《翼德的情人》
5月7〜8日
台北新舞台
在西方,戏剧列位文学之林,自古而然。反观中国的戏曲,其唱、念内容所诉求的雅趣或谐趣,循的不外中国诗、词、谣的传统,究其剧目,更是大量取材自中国古典小说;然而,因为戏曲乃「合歌舞演故事」,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体系鲜明而巩固,其经典的建立,倚赖表演的程度远胜过文本本身的文学性,相形之下,戏曲的文学系谱便不像西式戏剧那么受重视。
四大小说原生于书场上的表演
在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中同样被视为小道、裨类的戏曲和小说,其实渊源颇深。它们同样是包含角色、动作、对话、情节的「故事」,只不过,相较于早出的小说,由演员在台上以唱念做打虚拟出角色、情境的戏曲,显然是更新奇而生动的载体,又因看戏、听戏撤除了读小说的「文字」门槛,受众更多了。在戏曲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时代,不断的演出使剧目的需求量极大,小说有现成的故事,广为流传者尚有现成的知名度,自然成为优先考虑的取材对象。从实例上看,经典的小说未必适合各剧种,即使顺利台上见了,也未必一定能「演」成戏曲的经典。但挑战文学经典毕竟是很大的诱惑,故有「中国四大小说」之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直以来都活跃於戏台之上,经过累代的锤炼、创造,不但相关剧目多到有所谓的「三国戏」、「红楼戏」,其中变成戏曲名作的也不在少数。
四大小说堪称是戏曲所踩的「巨人的肩膀」,但事实上,四大小说除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之外,余三者在成书之前,书中的故事老早经过历代的职业「说话人」在市井的书场锤炼、创造,还有许多作为表演底本的「话本」应运而生,像最有名的「说三分」(即说《三国志》),从宋代起即是书场中的一门「专科」。由此可见,署名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作者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其实也是踩在「作者集团」的肩膀上集其大成的。正因为这些小说的原生地在书场,为了提供当下的听觉娱乐,不可能曲高和寡,而且,其本质原来就是表演的、大众化的,包括一人饰多角的说话人要有音韵铿锵的声情表演,人物要清晰,故事性、趣味性要很强,在「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中,一个人物牵引出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牵引出一个情节等等。这些特色尔后对戏曲艺术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和启发。
各剧种发展不同的小说剧目
戏曲声腔繁多,各自形成不同的剧种调性;剧种的剧性各异,也使它们在向小说取经的路向上各有不同的取舍。例如,越剧、黄梅戏的声腔、身段多阴柔之风,历来即擅长儿女情长的戏,因此诠释起《红楼梦》以宝玉、黛玉为重点的戏,犹如当行本色,十分对味。相对地,阳刚味重的京剧演宝、黛之情,就有点像关西大汉打著红牙板唱闺情,虽屡有新编,也热门不起来。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京剧(尤其是京朝派京剧)就合该演英雄豪杰忠孝节义的大历史,如「三国戏」,或是展现表演功法的戏,如出于《西游记》的《美猴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不厌精细的《红楼梦》显得琐碎、施展不开。
实际上,《红楼梦》非仅宝、黛之一端,它和其他章回小说一样,人物众多、事件迭出,对有「红楼作手」之称的陈西汀来说,《红楼梦》直是取撷不尽的宝藏。他前后编了八出红楼戏曲,王熙凤挂在剧名的居其三(注1),另外,还有让前辈京剧名角童芷苓从舞台红到银幕上的《尤三姐》,刻划宝、黛之情的黄梅戏《红楼梦》以及昆剧的《妙玉与宝玉》等。国光剧团即将推演由陈西汀编剧、童芷苓晚年的代表作《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出戏之所以能与文学原著各得各的光采,首功固然归于好演员的二度创作,但也多亏剧作家对这个大宅门的人情世故有深刻的体悟拿捏,经一番删繁就简,再以文学写戏曲、更写人性的深厚力道化入京剧的表演之中,该剧方能成为红楼京剧的佳作。
中国的古典小说何其多,被派上戏场的当然不限于这「四大」。拿台湾的布袋戏、歌仔戏来说,在它们的「古册戏」(注2)当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没有缺席,但有更多取材自《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杨家将演义》、《封神榜演义》、《孙庞演义》等通俗演义小说的剧目,而这些通俗演义小说与宋代以降传下来的讲史、平话,莫不有密切的关系。歌仔戏在内台的时代,因为时兴演「连本戏」,从章回小说延伸而来、可以一天接一天演下去的剧目遂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机。一九六○年代初期,台湾曾盛行拍黑白的歌仔戏电影,这些通俗演义遂一系列一系列地跟著戏班上了大银幕,如本于《征东》、《征西》的《樊梨花下山》、《薛刚大闹花灯》、《薛刚三祭铁坵坟》,便是其一。退到外台之后,在庙会演出的脉络里,这些有朝有代、教忠教孝的「古路」剧目便被置于日戏(即下午的演出),主为酬神,兼以娱人。
小说是新编戏曲的几块拼图
对昔日布袋戏、歌仔戏的表演者和观众而言,「古册戏」几乎同义于「历史戏」。但戏台上的历史,其实是正史游于「艺」之后,由说书人、小说家和戏曲艺人共同铺演出来的,它和正史的差异,除了反映民间与官方对所谓史实的观点不尽相同之外,也与剧性以及演出条件有关。例如,同样是「关公戏」,歌仔戏处理的方式就和京剧大不同。京剧中由关云长擅其场的经典,包括《单刀会》、《斩颜良》、《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战长沙》等,歌仔戏受京剧影响很深,观众又嗜看关公戏,所以歌仔戏也有不少同名剧目。然而,因歌仔戏演员多为女性,且向来偏重小生、小旦行,故能胜任关公的武老生可遇不可求,关公戏的发展自然有限。最常见的,是在正戏开演前的「加演」(注3)中,安排一段如《斩蔡扬》的关公戏,这种三十分钟不到的段子没什么情节,目的仅止于卖弄关公骑马、耍大刀的功架。关公若出现在有情节的正戏里,做法之一,是仿傚同名京剧的穿关、情节,唱曲则夹杂「外江」、北管以及歌仔戏等诸多曲调(注4),形成京剧为体、歌仔戏为用的关公戏;此外,歌仔戏为了藏拙并扬其所长,还杜撰出关羽「打红面」之前的身家故事,从「关公出世」演到「桃园三结义」,也算是另类的歌仔戏关公戏。
正如小说不畏冒犯正统历史一样,具有独特表演美学的戏曲也不会拘泥于小说,尤其是当代的新编戏,为了揭示创作的意义,对历史、小说的解释权不遑多让。像去年国光剧团演出的《阎罗梦》,虽然从《三国志平话》到《喻世名言》,小说文本有迹可循,歌仔戏也有出于同源的剧目名《三国因》,但《阎》剧新颖且耐人寻味的题旨与形式,其实大半出于编导的提炼、创发。如《阎》剧当中的戏中戏融入了几个取材自小说的传统戏,即曹操/关羽的《华容道》、吕后/韩信的《未央宫》等,看似老戏,实则经过重新设计(注5),以兼顾表演和剧中人性格,成为符合戏之需要的典故。因此,若说《阎》剧「改编」自小说,并不适切。
过去的传统戏大多是摘取小说片段出来,斟酌取舍之后,再加以形象化,便成一出戏;而新编戏较传统戏更注重首尾完整,以及契合现代人的情感思想,故对其而言,小说可以只是戏的几块拼图。戏专京剧团的新戏《翼德的情人》就突显了这样的新关系。《翼》剧的创作灵感来自「三国戏」的《定军山》,编剧从诸葛亮点将、老将黄忠取代猛张飞前去迎战敌将夏侯渊一段戏中,硬是窥出了端倪。他结合「夏侯渊有一女」的野史记载,令张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夏侯女为妻,于是阵前面临翁婿交战的挣扎。《翼》剧试著重塑张飞的形象,舞台上还有类似小说「意识流」的实验,以戏中戏刻画夏侯女想像中的张飞。虽然创新不必然成功,但在在可见当代戏曲推陈出新以抓住观众的强烈企图心。
(本刊编辑 施如芳)
注:
1.即《王熙凤》、《王熙凤与刘姥姥》、《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三出。
2.泛指改编自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剧目。
3.戏曲界有「女演员不能扮关公」的禁忌,早期歌仔戏班「加演」作关公戏,经常自京班借将。
4.歌仔戏演关公一定唱「外江」,以显其威武,所谓「外江」就是京剧的曲调。
5.参见王安祈〈关于《阎罗梦》的修编〉,《国光艺讯》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