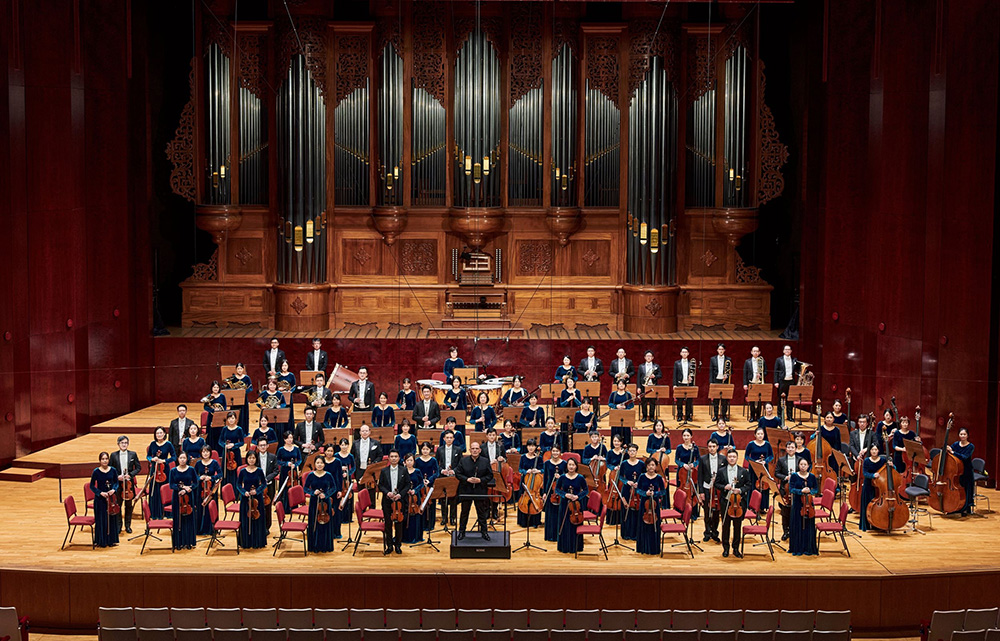今年「舞蹈秋天」的《微舞作》,由郑皓、苏品文、田孝慈担纲上阵,这回的命题是「神话」,三位新生代编舞家各自从自身体验取径:郑皓的《触底的形色》从近年的生命低潮状态,发展为对于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的思考;作为性别研究者、女性主义倡议者的苏品文,则希望让观者在《嗯哼》阅读到女人与性的关系;田孝慈则以《清醒梦》作为个人创作阶段性的回顾,质疑僵固的惯常。
2019舞蹈秋天 田孝慈、郑皓、苏品文《微舞作》
10/11~12 19:30 10/12~13 14:30
台北 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国家两厅院「舞蹈秋天」系列的《微舞作》,邀请了三位新世代编舞家——郑皓、苏品文、田孝慈,以「神话」为创作命题,在集体恐惧的时代,提问编舞家们什么是二○一九年的时代气味?舞蹈又可以如何表现?
《触底的形色》 从低潮出发切入科学神话
郑皓的《触底的形色》从近年的生命低潮状态,发展为对于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的思考。科学精神如何取代宗教神话,如同量子力学的光是波动还是粒子构成,常常是逆反我们直觉的。
「过去我认为身体有好的和坏的运作,想找到跳舞的正确方法,要享受自己做不好的时刻很困难。这次创作处在比较理想的生产节奏上,尤其七月参与了『身体微旅行』工作坊,陈彦斌的戏剧课让我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跳舞。」
独舞创作历经《落后巅峰》、《水银猜想》、《阻力的总和》到《触底的形色》,郑皓这次从低身心的状态与姿态出发,音乐使用声响逻辑来引起共鸣。他在三、四年前开始接触太极导引与武术,也好奇如何以不打开身体跨度的方式往下蹲。因为身体愈低愈难行动,如何在蹲低膝盖碰地的情况下;在双重、单重、失重不同模式之间;在转之中重心如何转移而不会飞出去而喷掉,找到身体动的自在?是这次动作的著力点。
他谈及从二○一六年以来的纯身体创作走到了瓶颈,想要松一松过去线性的逻辑思考。郑皓自嘲地说,《触底的形色》的英文名“Touchdown”是美式足球的「达阵」,「以摔倒为成功,愈摔愈成功,起不来才是成功。」人生总会遇到撞壁的时候,当微调没有用时,就需要更彻底的改变,希望透过舞蹈呈现这种翻转,去感受一个人如何逃离低潮的过程。
他透露,未来可能创作狭义相对论、牛顿力学有关的作品也说不定。用诗意科学来表达数学,不一定要走新媒体的科技技术路线。对郑皓来说,融合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讲台上纸与笔也可以。
《嗯哼》 探问用身体本身论述的极限
苏品文的研究型编舞计划《嗯哼》从「裸表演工作坊」开始,作为性别研究者、女性主义倡议者,她认为做性别议题在台湾很困难,希望这个研究透过工作坊能触及更多人,让观者在《嗯哼》阅读到女人与性的关系。
「我们的环境很难有机会让我们好好看一个人身体的全貌,这个资讯量很大。当表演者裸体被观看时,皮肤暴露在空气中所接受到的各式讯息都会影响她们,包含表演者对个人身体脉络的不同理解,这是需要练习的。」
就苏品文所知,台湾的表演艺术环境并没有系统地教授裸体表演,找表演者非常困难。《嗯哼》从举办「裸表演工作坊」开始,从裸表演技法、爱抚,到舞作试排练共三场工作坊,从中找到本次合作的三位表演者卓家安、陈诣芩、周宽柔。期间透过试排练、文本阅读、性别议题作品欣赏,参与性别讲座等等,慢慢形塑出《嗯哼》的样子。
对她来说,女性主义作品要有明确的理论论述在后面,《嗯哼》就是她对男/女性别在本质主义论述的回应。如何理解性别?她回到更个人的,女性个体身体来思考性,而不是去建构自己或任何人的剧本。排除会产生二元性别的动作,回到身体本能与知觉,去打开论说空间,而不要舞蹈剧场式抒情。
「谈论性还不集体恐惧吗?谈论性在台湾就是『喔我有一个朋友呀怎样怎样……啊你觉得怎样怎样……』用迂回的他者来论述。」苏品文直截了当地说。
「神话」对她来说更是代表父权——被受感召、十分相信、不可忤逆。而提倡多元主义本身就是非常女性主义思维的,编舞家真正言说的其实是更公众的政治议题,个人身体与公众论述的权力关系,以及性别议题在当代的困境。
《清醒梦》 藉薛西佛斯启动的自我提问
在纷乱与动荡的时代氛围下,田孝慈从卡缪一九四二年写就的《薛西弗斯的神话》开始,创作《清醒梦》作为个人创作阶段性的回顾,质疑僵固的惯常,她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开始对人生、创作提问时,所产生的那个自我意识——即使最终理解到,这提问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就像薛西佛斯作为推石头的人,大家会觉得他命运好苦,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会不会其实是快乐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每个人不也都是这样吗?每天都努力朝著梦想前进,路线也许不像薛西佛斯都是很固定的,会绕那边,会走这边……」田孝慈说。
面对这样荒谬存在的自我提问,田孝慈坦承现阶段找不到「动」的理由——不想生产新的动作,不如就回到过往作品所累积的动作语汇,回头看它们是什么?当时百分百相信的那些「相信」是什么?透过重新执行动作的「过程」找线索。但也不是一定要找到什么答案,言谈之中充满了许多对当下思考的不确定感受。创作就像做梦,她试图把这些不安、恐惧、漂浮感等情绪放到作品之中。
《清醒梦》作为一种反提问与反理所当然,田孝慈想要表述一种持续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落差——「你看到的跟你想像的不一样,你听到的跟你看到的不一样」。面对环境与社会的不稳定,当所有不可能发生的结果都发生了,不会这么糟的事也都不能再更糟了,或许就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时代的集体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