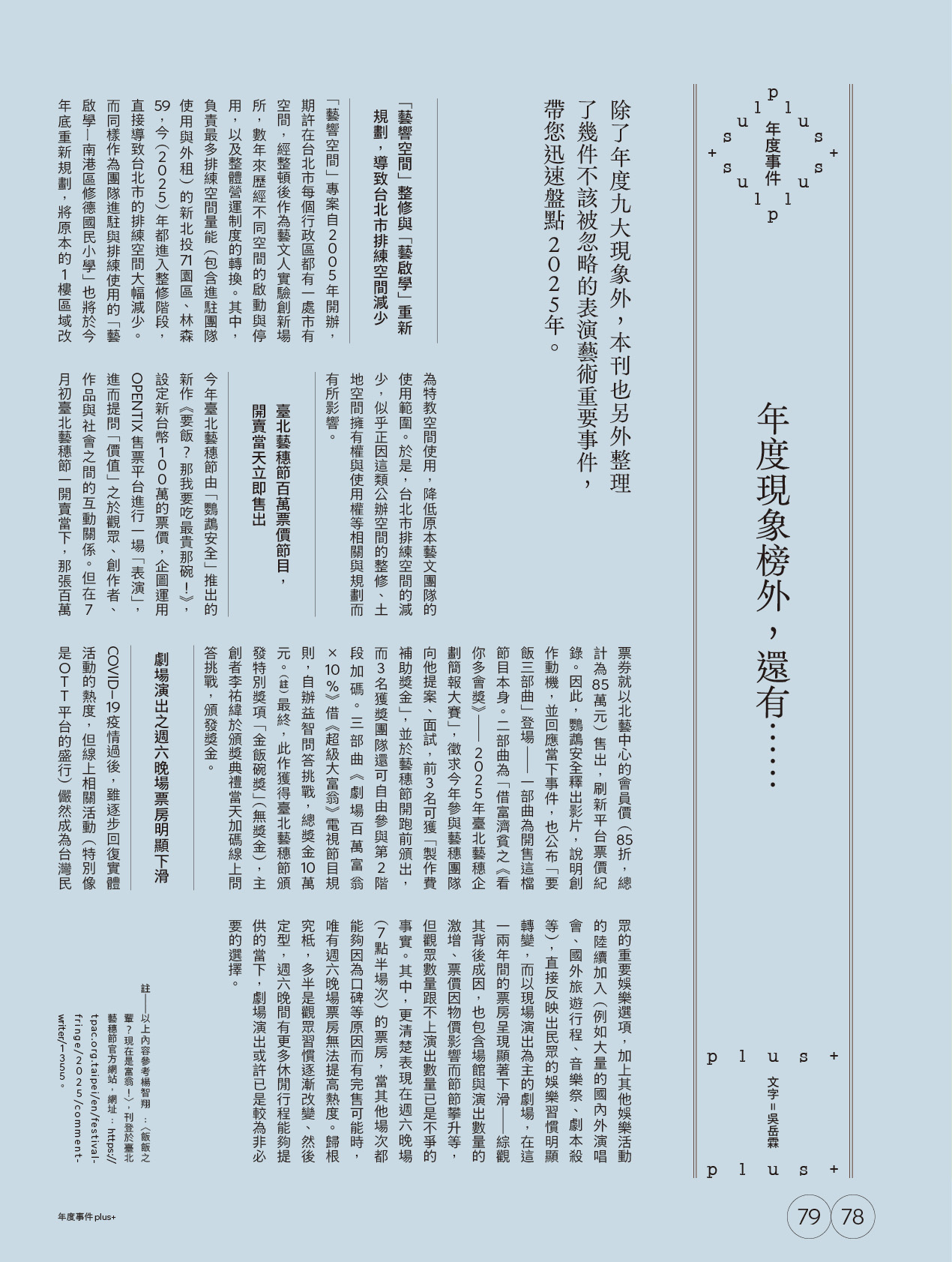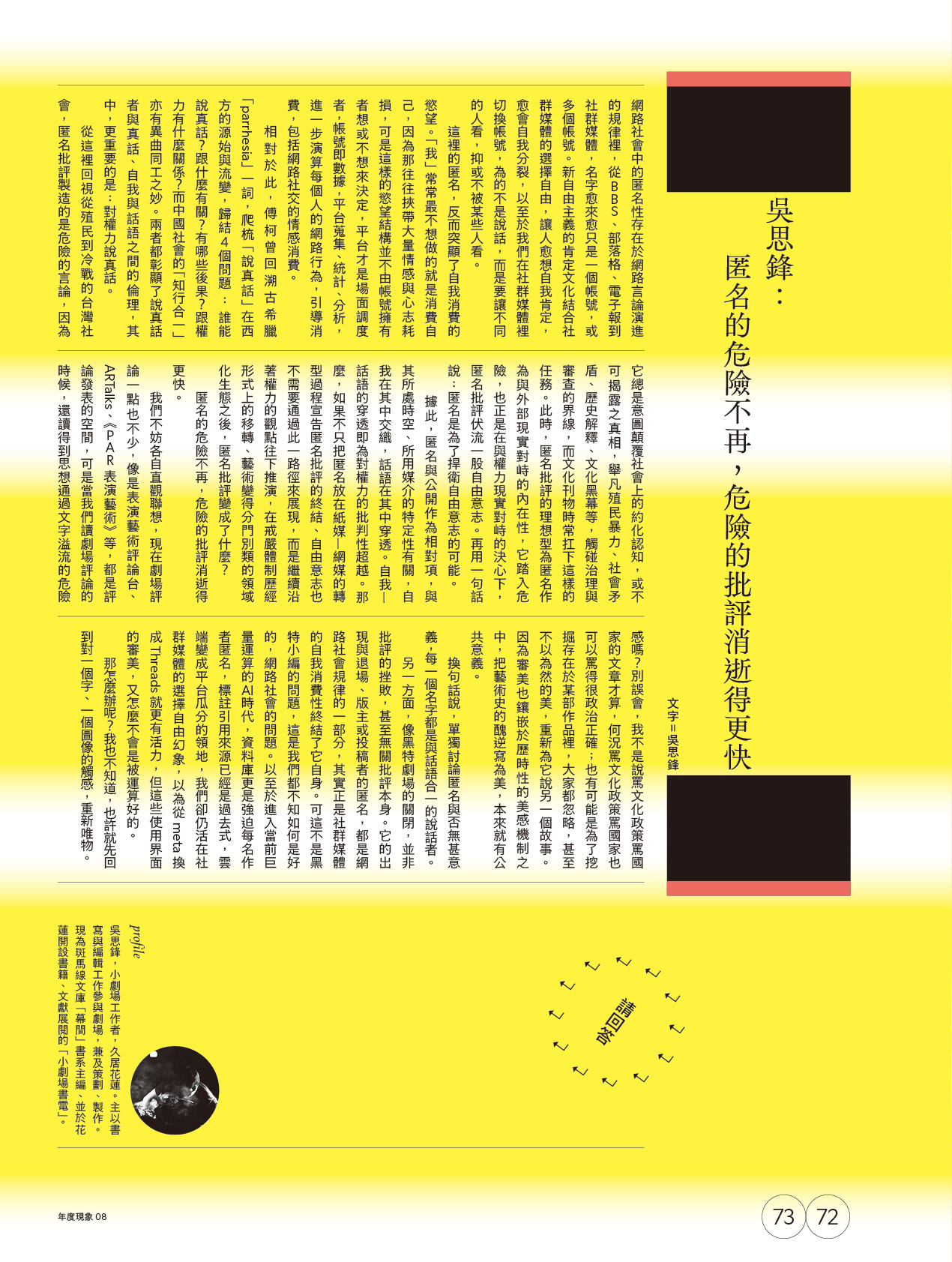1978年12月16日,31岁的林怀民带著5岁的云门在嘉义体育馆演出《薪传》。
那是戒严、审查制度横行的恐怖年代,前一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坜事件等后续影响仍在发酵,种种因素都拉紧警备总部的敏感神经。按林怀民日后的说法,为了让这支可能是第一出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剧场作品避开被扣上「台独」帽子的禁演风险,他「决定把首演搬到颜思齐墓的所在地,嘉义,向开台先民致敬——远离警总,即使事后被禁演,至少演完一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匆促的决定,会严重影响云门日后的发展。」(注1)
首演当天早晨,远方传来台美断交的消息,当晚的演出,有6,000人挤进体育馆。根据量子物理学的多重宇宙观点,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带领他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历史的巧合与林怀民强大的意念与选择,让《薪传》这出原本有「鼓吹台独嫌疑」的舞作,走进了一个舞蹈能跟民众、国家同舟共济、感性发声的宇宙,也象征了一位忧国忧民的艺术家的诞生。云门日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了。他们走进地方、飞越国境,影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蹈家与观众,得到许多国际舞坛大奖与尊敬,成为台湾大众最熟知的舞团。
今年,这件传奇的作品将再度重演。但身为观众,我们还是得追问:为什么我们需要观看一出首演于45年前的作品?对此,我们来到(另一个1978年宇宙中)《薪传》原定的首演地国父纪念馆,并邀请著名诗人杨泽、舞蹈学者陈雅萍、策展人龚卓军同桌对谈,不只聊70年代,也回探50、60年代,并延展到我们所处的现在,尝试透过跨域的观点理解《薪传》,这件在特殊时空中生成与壮大的作品,并同时认识到在这个氛围中的艺术家与观众,是如何定位自己跟他人、跟社会、跟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薪传》是70年代的林怀民在混乱的世界局势中,对前卫批判与诉说自己故事的时代趋势的「呐喊与突围」(注2),此刻我们身处疫病、战争威胁,资本、国家力量介入更隐微的时代,或许也能透过观看《薪传》,重新定位此刻所身处的位置,找到突围的力量。
主持 陈品秀
记录整理 张慧慧
时间 2023/01/10 14:30-18:00
地点 国立国父纪念馆、布兰梅德国下午茶馆
Q:云门成立于1970年代,《薪传》(1978)当年首演后轰动社会,成为台湾现象级的制作。除了受台湾在全球政治局势的影响之外,《薪传》就艺术本身而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如今在45年后将再度重演,三位如何看云门创立到《薪传》产生的整体氛围?而70年代的社会、文化又是何种样貌?在当时呈现出什么样的身体面貌与存在状态?
杨泽(以下简称杨):「云门50」近一甲子,我自认是某种同代人(见证过《薪传》首演台北场),却觉得,怕谁都难从个人有限的小历史,去对已跨入集体历史,集体记忆层次的云门任意说三道四,重探歴史需要无限谦逊,底下浅见仅供参考。
大家知道在创云门前,林怀民是个杰出的小说家。也因创作生涯最初从文学首航,后出舞作常被质疑文学味太浓,或有文学包袱,但我不认为这是问题,世上没有哪个创作者可以横空出世,没有脐带,林怀民用文学当动力动能,后来走得多远,也许才是观者要关心的。
1973年云门成立,同年我从嘉义北上念书,其时已拜读过小说家林怀民69年出国前出版的《蝉》及其他中短篇。70年代是云门开创期,也是我念大学及研究所阶段,但这里容我绕点路,先谈谈林怀民和(奠定战后台湾文艺基础的)50、60年代的渊源。
首先,2022年林怀民自云门退休后新出书《激流与倒影》,书名其实取自痖弦长诗〈深渊〉。痖弦显然是林深爱的诗人,小中篇《蝉》的结尾大量引用痖弦〈如歌的行板〉,令人印象深刻。回头看,发表于50年代末的长诗〈深渊〉充满一股激越无比的悲剧性张力,对林怀民早期舞作风格影响颇大。除了上述「激流如何为倒影造像」这样至今可以直接被林拿来说舞的句子,我揣测〈深渊〉底下两句「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也和云门后来突围而出的创作美学有可以相观照的地方(「突围」是林本人的说法(注3))。
讨论编舞家的文学影响,不能不重提60年代重要作家陈映真,他因左统色彩渐为台湾社会遗忘,但林怀民并未淡忘,2004年舞作《陈映真.风景》重拾后者念兹在兹的人道主义精神及救赎主题,只为了确认,小说家陈映真不单单是林自己,也是战后台湾文艺精神一大指标。
69年林怀民离台赴美,首站密苏里大学新闻研究所,没念完,转去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所,72年拿艺术硕士后即回国教书。72年到73年创云门,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突然转换跑道,变成了职业舞者和编舞家?
这是林怀民后来常被问到的大哉问,但如果我们理解,50、60年代既是战后台湾文艺的奠基期,也是大摸索期,从诗到小说、音乐到摄影、剧场,纷纷以现代为名,一贯标榜打破、重组各类形式技巧媒材的实验可能,当此之时,才华横溢的头号文学青年、时代青年林怀民从现代小说转到现代舞,也许并不是那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另方面,60、70之交的「时代的闷局」固然是当年林怀民及其他台湾文青、艺青屡屡想突围而出的决定性因素,但我更好奇的是,从69到72年的留美期间,除了短暂在美习舞(在爱荷华学舞,也到纽约玛莎.葛兰姆及模斯.康宁汉学校短期进修),林怀民在海外到底学到、看到了什么,使他得以迅速打开他的眼界,能在回国短时间内创立舞团,先以《寒食》及《白蛇传》初试啼声,几年后即以《薪传》大展身手,一飞冲天?
杨泽
上世纪50年代生,成长于嘉南平原,73年北上念书,其后留美10载,直到90年返国,定居台北。已从长年文学编辑工作退役,平生爱在笔记本上涂抹,以市井访友泡茶,拥书成眠为乐事。著有《新诗十九首》、《蔷薇学派的诞生》、《仿佛在君父的城邦》等。
陈雅萍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博班总召集人,《身论集》共同主编。专研台湾现、当代舞蹈,亦涉猎香港当代舞蹈研究,著有《主体的叩问:现代性.历史.台湾当代舞蹈》,文章发表于表演相关期刊及多本中、英文舞蹈研究论文集。
龚卓军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教授,《艺术观点ACT》主编。曾担任「近未来的交陪」、「曾文溪的一千个名字」等展览策展人、台新艺术观察员。著有:《身体部署》、《交陪美学论》及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