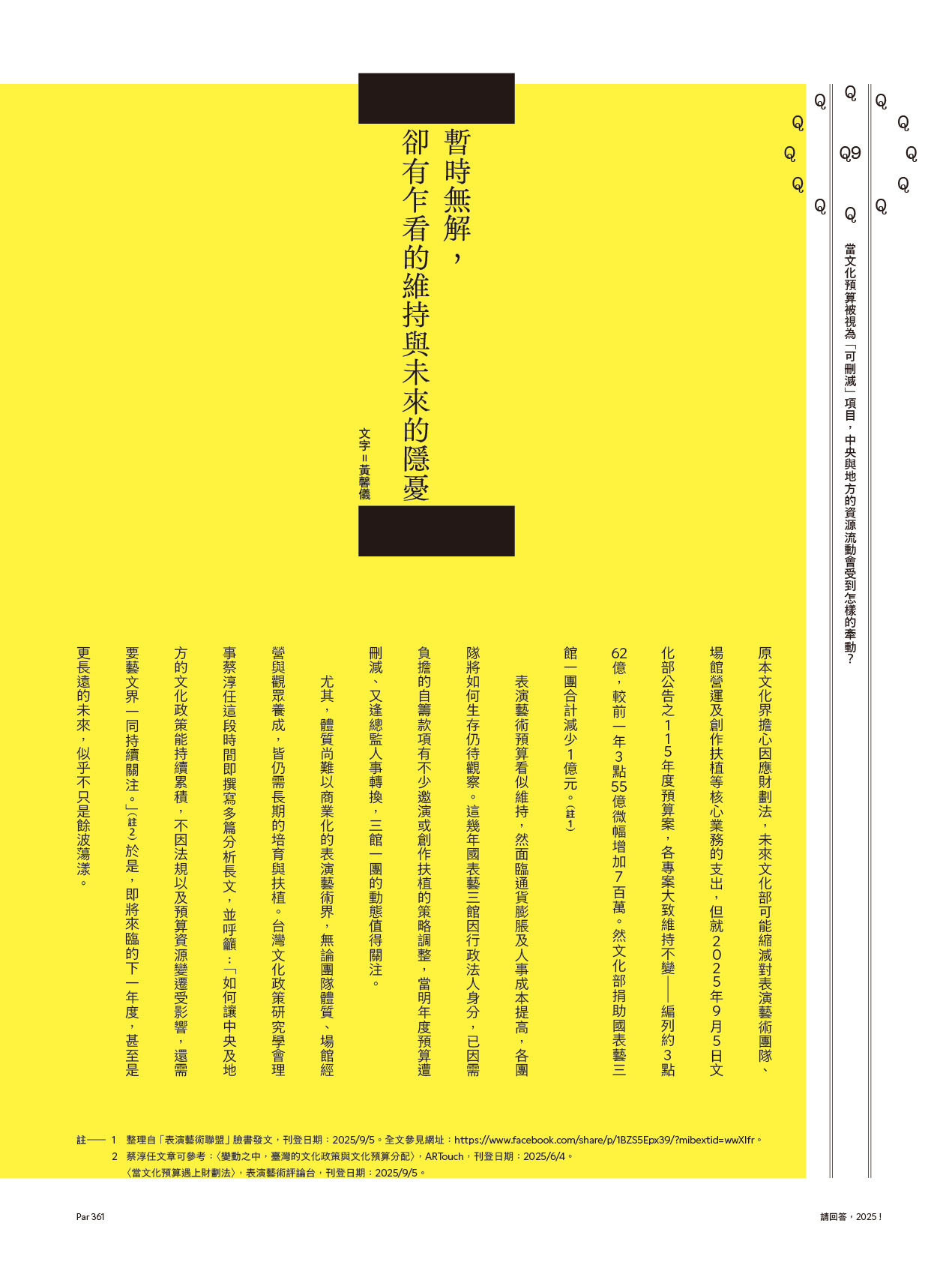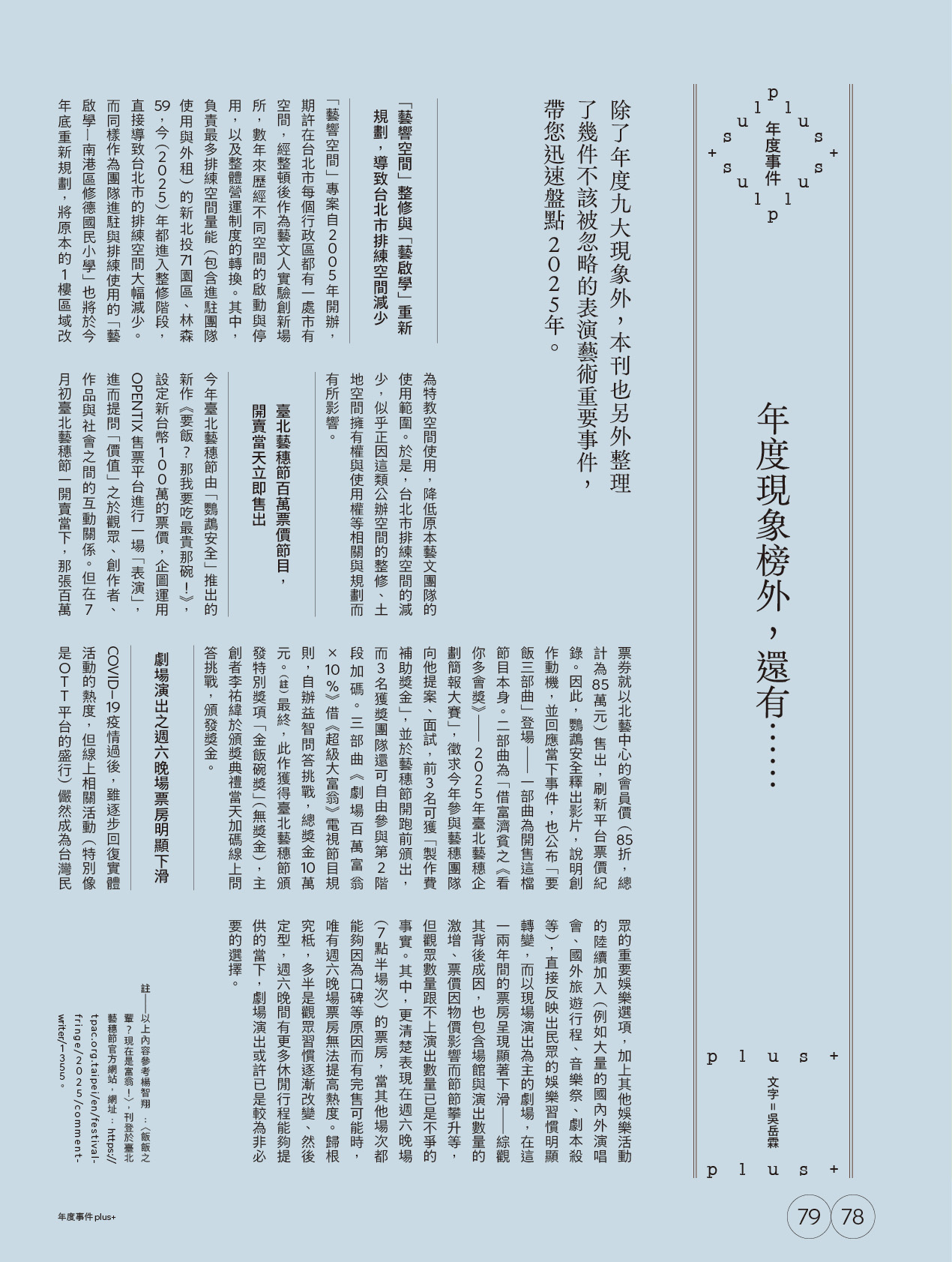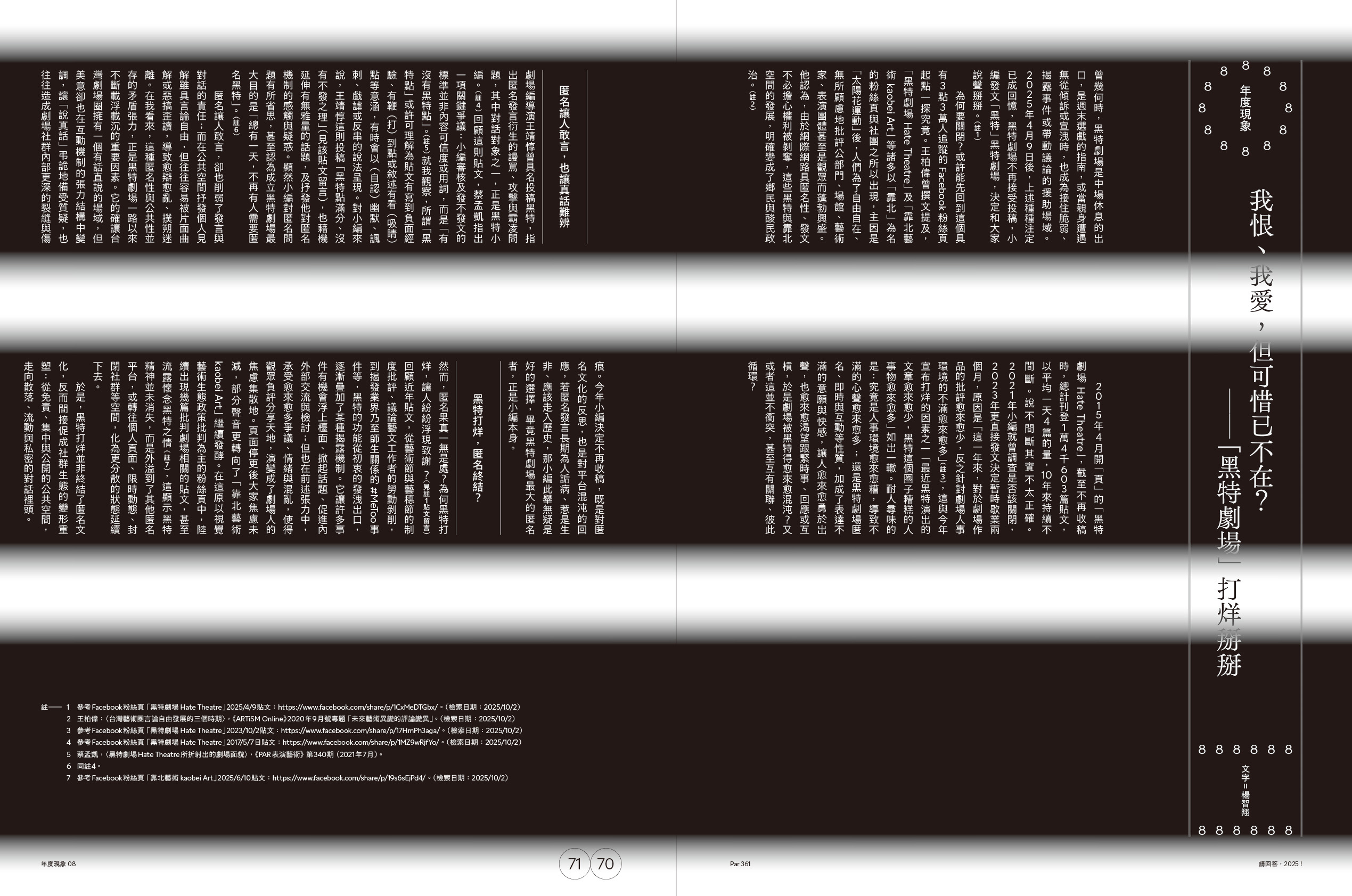柏格曼剧团《羊之歌》
2024/12/1 台北 国家戏剧院
故事一开始聚焦于一位蒙著红色面纱的白人,他轻敲钟声,宣告了剧情的开端,也无声地揭开了羊的心灵之旅。这只羊,最初仅是羊群中的一员,但随著时间的推移,它内心深处的渴望悄然发芽:想要追求理想。剧情将此过程转化为羊对成为人类的渴望。
随著羊逐步接近目标,它的旅程如同一条无休止的输送带。这条输送带象征著一旦启程便无法停歇,并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无力感。羊与其他人类一同无力地奔跑、跳跃,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未来。而当半兽羊与一名女子所生的孩子被无情掐死时,这一悲剧象征著羊在追求人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失败与痛苦,尤其是那段曾遭霸凌的黑暗记忆。霸凌的回忆像幽灵般贯穿整部剧,无法抹去。当今社会,霸凌的形式无所不在,从肢体、语言、性别、网路、校园、职场,甚至反击型霸凌,无一幸免。为何霸凌如此猖獗,直至今日?是不是现代人背负的压力过重,无法承受?或是年轻的无知?也许,许多人带著千疮百孔的伤痕,仍然步履匆匆,继续行走在这条迷途上。最终,半兽羊终于变成了人类,却惊觉曾经的温顺、纯真与善良早已不复存在。它已不再是那只温和的、单纯的羊;当它回到羊群,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被认同。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段无法抹去的伤痛,或者某些无法向人言说的孤独。正如编舞家吉赛儿.韦安所诉:「当人们开始对周遭世界变得敏感,并具备同理心时,彼此之间更容易凝聚;相反,当人们长时间对环境麻木,对他人的痛苦失去感知与同理,暴力便在无形中滋生。」
剧中有两段操偶师与偶之间的微妙互动。这种关系,仿佛是上帝对人类的教化。善与恶,在这个世界上并行不悖。我们从小便被父母教导,要成为「好人」,然而随著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好人」的定义渐渐模糊。使得许多人无意间走向了「坏人」的角色。剧中的操偶师一再对偶进行道德教化,要求它抑制欲望。然而,当操偶师最终消失,这个偶是否真正理解了道德?学会了自我控制?抑或它仍然只是表面上学会了规则,而心灵深处的本能依旧无法抑制?
剧情的高潮或许是主角终于实现了成为人类的梦想,但这个变化却并非它最初所期待的模样。这让人不禁深思: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如何避免迷失自己?如何保持那份最初的纯粹?这同时也引发对霸凌者与被霸凌者的反思: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如何寻求帮助?社会又该如何协助这些深陷困境的人,无论是霸凌者还是受害者,去帮助他们重拾失落的人性光辉?
此外,为何在剧中,半兽羊的死亡来自一位女性之手?在西方的英雄叙事中,反派角色常常是女性或有色人种。这些形象背后,又有著怎样的文化与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