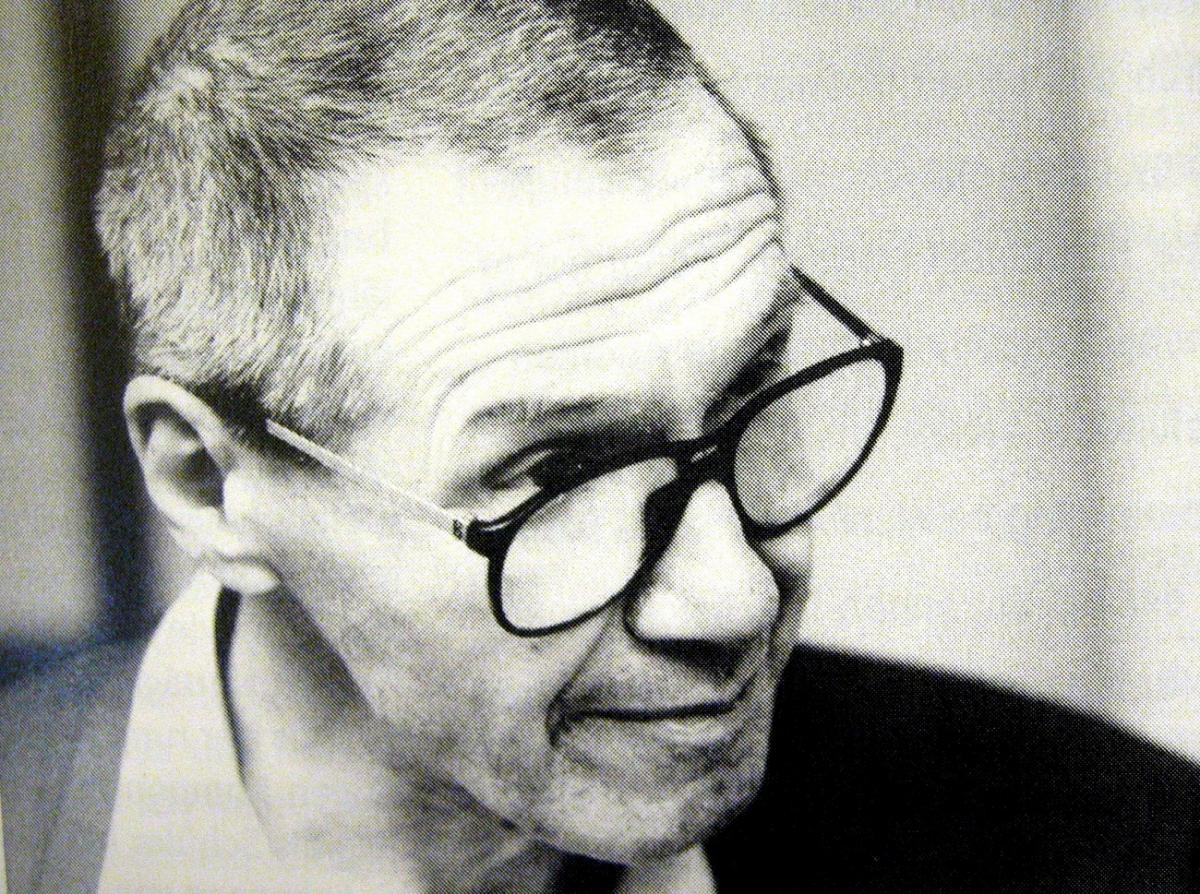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無調性」遠離了二十世紀前以和諧觀念為主的「調性」音樂,迎向前去開發不諧和音的領域,預示了二十世紀音樂的主流。「無調性」為音樂發展進行了自由與大膽的「解構」之後,頓時將音樂導入一個失序而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
兩廳院於四月上旬推出的「非常現代音樂節」,連續在幾個演出場地推出密集的七場管弦樂、室內樂演出與研討會,並邀來德國音樂名家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以及「摩登樂集」(Ensemble Modern),主導這一系列的活動,頓時讓一向冷清的國內現代音樂界帶來些許熱鬧的氣氛。這一系列音樂會所安排的曲目,雖未能廣泛的、周延地涵蓋二十世紀音樂的主要表現方式,卻大體地呈現出所謂「現代音樂的」的一些形貌,足以串成一段二十世紀音樂演變的簡史。
現代音樂的晨曦-魏本、瓦雷茲與梅湘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後浪漫派的音樂以它那震顫、悸動的強烈效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如世界末日般的緊張局勢以及「世紀末」的人心惶惶。理察‧史特勞斯、馬勒等這類具有「表現主義」傾向的音樂,在第一次大戰稍前,被荀貝格(Arnold Schoenberg)、貝爾格(Alban Berg)、魏本(Anton von Webern)師徒三人加以激化,終於形成了所謂的「無調性音樂」。「無調性」遠離了二十世紀前以和諧觀念為主的「調性」音樂,向前開發不諧和音的領域,預示了二十世紀音樂的主流。「無調性」為音樂發展進行了自由與大膽的「解構」之後,頓時將音樂導入一個失序而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經過多年的探索,荀貝格等三人終在一九二○年代以後,創立了一套講究條理與邏輯,強調明晰與勻稱的所謂「十二音音樂體系」,將無調性導入正軌。無調性音樂宛如一場音樂革命,它徹底地顛覆了傳統,卻進入了破壞後的騷動之中,「十二音」則有如破壞後重建的新制度。
此次演出的兩套魏本作品:一九○九年完成的《六首管弦樂短曲,作品第六號》以及一九一三年完成的《五首管弦樂短曲,作品第十號》,雖然都屬於無調性時期的作品,卻已預示出日後十二音音樂的某些特質。這兩號作品儘管都是為大型管弦樂而寫,卻顯得相當樸素精練、清晰均衡,各種不同樂器迅速地輪流交錯出現,造成的瞬間多彩的音色變換,這正是典型的所謂「音色旋律」(Klangfarbenmelodie)的效果。這兩號作品儘管存在著上述的相似之處,相較之下,作品第六號卻顯得較澎湃洶湧、自由豪放,稍遲數年完成的作品第十號顯得較細膩拘謹、澄澈清晰。
有別於無調性,十二音的創作方式,與魏本同年的法裔美籍作曲家瓦瑞斯(E.Varese)則是以噪音式的新穎音響效果、爆發式的狂猛節奏去震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樂壇。原先學習科技卻轉行從事音樂創作的瓦瑞斯,對聲音的特質、音樂新素材的研探相當熱中。此次演出他的大型管弦樂曲《美國》,是他早年在這方面第一個成功的實驗。曲中,他似乎得到斯特拉溫斯基《春之祭》的真傳,而且變本加厲地重用管樂器(尤其是銅管)、敲擊樂器(包括可演奏滑音的警報器),以突顯出充滿噪音與不安定感、在世紀初已顯得相當商業化的美國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止了瓦瑞斯的音響實驗,魏本則在戰爭剛結束之際,慘遭一位冒失美軍的誤殺。戰爭期間,成為戰俘的法國音樂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在他被囚禁的德國南部第 VIII A號集中營裡,完成了《時間終止四重奏》,並由包括梅湘在內的四位學過音樂的戰俘在營中舉行首演。此次音樂節的主辦單位將此曲譯為《世紀末四重奏》,顯然有誤;作曲者宣稱此曲的靈感來自聖經〈啟示錄〉中,世界末日來臨時,時間將終止運作的說法。在兩次世界大戰有如世界末日的時代悲劇中,魏本、瓦瑞斯與其他許多前衛作曲家的音樂,都直接地顯現出悲觀的時代精神,梅湘卻嘗試透過他的音樂去傳達某種靈性的、人道的訊息,期盼為這個悲慘世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在物質主義、進步主義、無神論甚囂塵上的二十世紀,梅湘卻有如一位傳道者般,孜孜不倦地傳播著靈性與傳統的奧義,述說著宇宙與大自然的美妙。在前衛精神成為主流的世紀中葉,梅湘創作觀雖未獲得作曲家們的廣泛認同,但他的音樂卻搏得一般聽眾普遍的共鳴。
現代音樂進入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德國南部的達姆城(Darmstadt)幾乎已成廢墟,然而卻在一九四六年,該城逐漸復甦過來,開始舉辦一年一度對日後所謂「現代音樂」具決定性影響的「達姆城暑期音樂課程」。瓦瑞斯、梅湘、荀貝格的學生萊柏維茲(Rene Leibowitz)等,都曾受邀前往講課,誕生於一九二○年代前後,出道於戰後,來自歐洲各地的年輕作曲家們,成為此音樂營的擁護者,稍後更將前衛性與實驗性的現代音樂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推展開來。這些作曲家中,較著名的有:布列茲(P.Boulez)、史托克豪森(K.Stockhausen)、馬德拉(B.Maderna)、諾諾(L.Nono)、貝里歐(L.Berio)、韓澤(H.W.Henze)、齊摩曼(B.A.Zimmermann)、普舍(H.Pousseur)。
這些與達姆城有關連的音樂家們,以魏本的音樂為根據,並將之發揮成更繁複、更細膩的所謂「全面音列音樂」(total serialism)或「後音列音樂」(post serialism)
,以便與戰前的十二音音樂或「音列音樂」(serialism)有所區別:十二音音樂在進行音列的排列組合時,特別注意到音高的配置、安排上的均衡勻稱,全面音列音樂則同時考慮到節奏、音色、立度、各種不同變化的發音法(articulation)上的配置,這些也都必須達到相當嚴謹的程度。這類既繁複又嚴謹的譜曲,要求作曲者具有精密準確的數理與邏輯概念,而且對一般唱奏者的能力與技巧是極大的挑戰與考驗;一些專門演奏這類高難度樂曲的合奏團於是應運而生,例如此次來台的德國「摩登樂集」、布列茲創立的法國「當代合奏團」(EIC)等。此次演出中,史托克豪森的《對位》Kontrapunkte、匈牙利作曲家庫爾塔克(G.Kurtag)的《鋼琴、大提琴的雙重協奏曲》Doppelkonzert Op.27/2、以及前來現身說法的拉亨曼的幾首作品,都具現出全面音列音樂那種理性、抽象、繁複、富於音色細膩變化且具有立體空間效果的「現代」特質。
現代音樂的擴散與「反現代」
「全面音列音樂」在一九六○、七○、甚至八○年代被達姆城樂派的擁護者們推展到世界各地,儼然成為當時推崇科學與進步精神社會的音樂主流。然而某些作曲家們不再拘泥於音列音樂嚴謹的細枝末節,而尋求較富於彈性較自由的表達方式。例如此次演出中德國作曲家郭貝爾(H.Goebbels)的近作《白紙黑字》,延續了卡格爾(M.Kagel)慣用的「音樂劇場」的表現方式,結合器樂與戲劇因素,嘗試藉演奏者的肢體語言與表演,沖淡現代音樂的冷漠與舞台上的單調。老將李蓋悌(G.Ligeti)的《鋼琴協奏曲》就像他的一些新近作品一般,不再向他早期的創作那麼「酷」,例如他的第二樂章流露出有如達利超現實畫作般夢幻的抒情,第三樂章則是作者再精研非洲黑人音樂後的成果。明確的,由幾個一再重複的頑固節奏型態重疊而成的複節奏,儘管顯得有些複雜,卻不至於讓一般聽眾感到無所適從。
四月八日演出的節目中,一口氣排出美國作曲家賴克(S.Reich)完成於一九八○年代的作品:《紐約對位》、《八條線》與《不同的火車》。這三首曲子與李蓋悌的《鋼琴協奏曲》一般,同樣強調明確的複節奏,但卻顯得更加明確、單純。賴克的這類簡易明嘹、經常充滿著幽默感與親和性的音樂,被稱為「反複音樂」或 「極限音樂」(minimalism)。這類音樂和其他種種在一九八○年代以後興起的種種流派,經常被現代音樂人士認為是退化、無內容、譁眾取寵,而被冠上一個具貶義的名詞「後現代」(post modern)。然而經過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具「反現代」本質的後現代音樂,似乎有逐漸取代現代音樂而成為主流的趨勢。
兩廳院此次舉辦的「非常現代音樂節」,突顯了一九五○到八○年代之間的現代音樂,而這類音樂雖被當時的人稱為現代,在今日看來卻成為「昨日的現代」。相較之下,該音樂節卻忽略了目前方興未艾的「今日的現代」,令人覺得有些可惜。
文字|陳漢金 東吳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非常摩登,摩登非常
細覽二○○三年「非常現代音樂節」
林芳宜【本刊編輯】
首次在亞洲登台,摩登樂集的曲目相當全面性,誠如策畫人卡斯登.威特所言:以音樂節的型態呈現現代音樂不只是在台灣,甚至在整個亞洲都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現代音樂對於大部分聽眾而言,仍然是門陌生的藝術,在這種現象下,選擇一開始即局限在某個特定範圍內,呈現一個全面多元的音樂面貌是更為重要也是正確的方式。
猶記得去年「啟動台灣的聲音」音樂會冷清的現場,除了親友團熱情出席以外,從觀眾群中可以感覺到,聆聽現代音樂仍然是極小眾族群的愛好。儘管一整年慘澹的票房與寥寥無幾的觀眾,兩廳院推廣現代音樂的魄力並沒有因此受到打擊,相反的,經過新春期間長長的內部整修,兩廳院再度開門即以令人驚嘆的節目「非常現代音樂節」向大家招手。
主辦單位一出手便請到世界頂級、來自德國的現代音樂樂團「摩登樂集」(Ensemble Modern)擔任這次為期八天的音樂節樂團。摩登樂集自一九八○成立起便以演奏當代作品為職志,成員均為極優秀的演奏家,在不設立常任指揮與藝術總監的狀態下,每個成員平等承擔樂團營運的盈虧與演出品質的維持與提昇,換句話說,樂團的菜單由所有成員一起擬定,也因此使得摩登樂集擁有極為多元化的演出型態
以多元化節目呈現全面風貌
首次在亞洲登台,摩登樂集的曲目相當全面性,誠如策畫人卡斯登.威特(Kasten Witt)所言:以音樂節的型態呈現現代音樂,不只是在台灣、甚至在整個亞洲都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現代音樂對於大部分聽眾而言,仍然是一門陌生的藝術,在這種現象下,選擇一開始即局限在某個特定範圍之內,呈現一個全面多元的音樂面貌是更為重要也是正確的方式。
所以從節目內容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音樂的源頭──第二維也納樂派的作品:安東.魏本(Anton von Webern)作品第六號以及第十號的管弦樂作品,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第二維也納樂派已經被歸類於「古典」的聲響,但是由摩登樂集呈現魏本的管弦樂色彩仍然令人十分期待。
動用了一百多人的法國作曲家瓦瑞斯(E.Varese)的《美國》Ameriques,將由摩登樂集與NSO攜手齊奏,台灣聽眾將親身經歷瓦瑞斯特有的強烈音響,也能一窺音樂創作者為了掙脫幾百年來的傳統所表現出的實驗精神。另一位聆聽現代音樂不可缺席的大師:梅湘(Olivier Messiaen)的《世紀末四重奏》Quatour pour la fin du temps也將被演出,這首一般被翻譯為《時間終止四重奏》作品創作背景十分奇特:被納粹拘禁於波蘭西南方的西里西亞集中營的梅湘,將聖經〈啟示錄〉中關於世界末日的章節化為音樂,寫成這首為豎笛、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的四重奏,並於集中營中首演。摩登樂集優秀的獨奏家們將以他們高超的演奏技巧呈現集中營裡人們的絕望與渴望。
作曲家現身說法
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作曲家中極具代表性的德國作曲家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此次將隨著摩登樂集來台。他不但將在音樂會前解析魏本的作品,也將解說自己的作品,以增加聽眾對現代音樂的理解,拉近現代音樂與聽眾的距離。摩登樂集將演出拉亨曼的幾首經典之作:《圖畫》Tableaux、《流體》三重奏Trio Fluido、《樂章》Movement等,由作者本人解說作品,並馬上進入音樂會聆聽該作品,當可感覺第一手的大師的靈感。
除了拉亨曼,摩登樂集也帶來同樣來自德國並且可視為現代音樂里程碑的作曲家之一的史托克豪森(K.Stockhausen)的重要作品《對位》Kontrapunkte,寫作此曲時的史托克豪森正歷經十五個月的巴黎之旅,除了實驗性極強的聲響表現方式以外,也極力使用各種不同演奏方式與嚴謹的架構開展他的創作,《對位》正是此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而摩登樂集的指揮史帝芬.艾斯伯瑞(Stefan Asbury)與鋼琴家烏立‧魏格特(Uli Wiget)將在音樂會前現身說法,不只因為鋼琴為此曲的關鍵性樂器,更因為摩登樂集與魏格特也將呈現現代音樂史中極為艱難的大師之作:李蓋悌(G.Ligeti)的《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標竿作品重現台北
來自今日屬於羅馬尼亞境內匈牙利語區的李蓋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布達佩斯跟隨巴爾托克學習作曲,一九五六年逃往西方,最早在科隆,稍後大部分時間在維也納與柏林兩個城市生活,也曾擔任漢堡音樂院作曲教授。相對於史托豪森對於電子聲響的喜愛,李蓋悌本人曾表示他仍然較偏愛傳統樂器的共鳴。這首《鋼琴協奏曲》被公認為李蓋悌純熟器樂曲中經典之作,艱深的演奏技巧更是令不少傑出的鋼琴家視為攻克的目標。
李蓋悌之外,摩登樂集同時也將演出與李蓋悌來自相同地區,甚至一同跟隨巴爾托克學作曲的庫爾塔克(G.Kurtag)的作品。如果說李蓋悌的作品每每將樂器的精確性與演奏可能性發展極致的話,那麼庫爾塔克的音樂無疑是以樂器原本的色彩,用音符揮灑出一幅幅聲響的圖畫。這次台灣的聽眾將有幸聽到庫爾塔克的《複協奏曲,作品27/2》Doppelkonzert, Op.27/2, 親身經歷作曲家以音符為顏料創作出的藝術品。
除了這些現代音樂的經典作品以外,當然不可忽略當今極受歡迎的「極限音樂」。摩登樂集將有一整晚的曲目為極限音樂,包括台灣聽眾不陌生的賴克(S.Reich),當晚還會演出賴克、萳卡羅(Nancarrow)等人的作品。
現代音樂將創作的可能性向無邊的境界開展,與其他藝術的結合也是自然而然因應而成的現象。這次音樂節中最令人興奮的當屬郭貝爾(Goebbels)的音樂劇場作品《白紙黑字》Black on White,這是當代作曲家與樂團合作的典型合作模式:作曲家深入理解團員的特性為該樂團量身定作音樂,一九九六年摩登樂集首演這齣「屬於」他們的作品,震撼了歐洲音樂界,這次不但將原汁原味在台北重現,郭貝爾本人更將為觀眾講解這首作品。此外,摩登樂集也將呈現另一位與摩登樂集合作的主要作曲家之一──梅森(B.Mason)的《卓別林歌劇》Chaplin Operas, 這部摩登樂集早期委託創作的作品顯示出當代音樂創作的另一種可能性,雖說這種型態的創作在歐洲已經司空見慣,但是對亞洲的愛樂者而言,想必仍然是個新鮮的經驗,如同其他場次的音樂會,作曲家梅森本人也將到場與觀眾們分享他的卓別林歌聲。
嚴謹的策畫奠定良好基礎
精采的作品、優秀的演奏者、密集的音樂會,這些元素若沒有相當傑出的計畫統籌都可能使音樂節付諸流水。亞洲破天荒的第一次現代音樂節,為其策展的即是在一九八○年創立摩登樂集的卡斯登‧威特(Karsten Witt)。威特曾經創立了三個樂團,為保守的維也納成功策劃出令許多國家艷羨的維也納現代音樂節(Wien Modern),音樂會加上作曲家本人的說明,即為維也納現代音樂節節目重要的一環,威特將此模式帶到台灣,顯示出音樂節長久耕耘的企圖,也相信台灣的觀眾將感受到聆聽當代聲響的趣味,進而享受與時代同步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