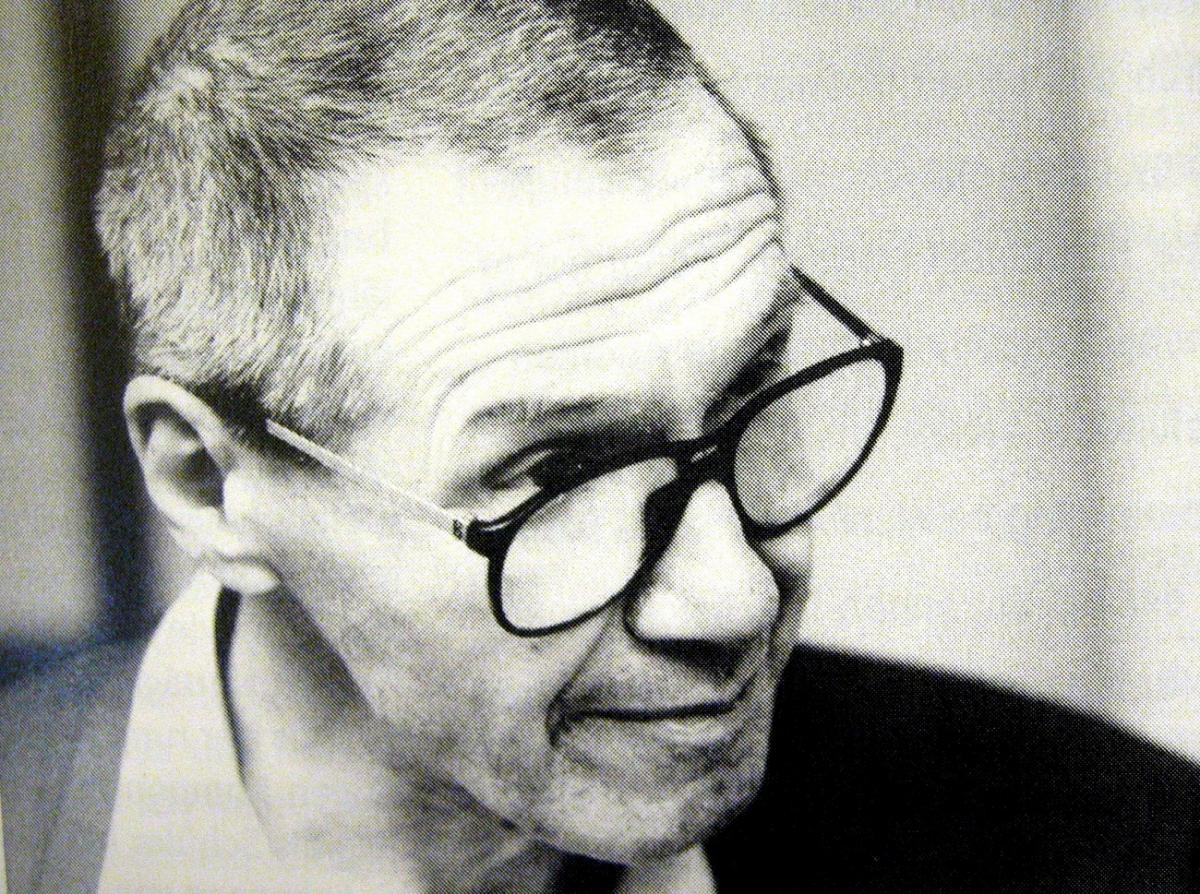黃梅戲《徽州女人》豈能為地域特性所局限?湘劇《白兔記》之動人,又豈在於宋元南戲的存古性?當戲曲已失去流行地位時,劇種特色應當「內化」為整齣戲的基調內蘊,不必強調不必外顯,運用多元技法觸動現代人心靈,讓古典和現代接軌在「感動」的情緒裡,這是《徽州女人》為當代地方戲的處境指點出來的一條途徑。
民國八十五年國家戲劇院和周凱劇場基金會主辦「戲曲現代化」兩岸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中提出〈戲曲現代化風潮下的逆向思考〉論文(編按),指出在戲曲改革過程中,編劇中心確立,導演中心也隱然成形,樂隊編制擴大,序幕曲、尾聲合唱、幕間曲、襯底音樂等的重要性幾乎超越演員的演唱,原本以「腔調、唱功」為主體的傳統戲曲質性改變,劇種之間的差異逐漸泯滅。這個說法當時引起不少討論,與會者多認為地方戲劇種特質的淡弱是戲曲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不過我所提的是整體戲曲發展大趨勢中的遺憾與失落,如果將討論焦點集中在台灣,我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所有戲曲劇種在台灣是命運共同體
具體說來,對於大陸地方戲曲在台的演出,我並不堅持劇種特色是首要前提。我曾在多種場合中一再強調,台灣的戲曲觀眾人口或許有限,但是「藝文愛好者」卻十分普遍,許多人把「看表演」當作生活必須的一環,他們的生活可能是:「第一個週末聽蘇州彈詞,第二週看雲門舞集,第三週看歌仔戲,第四週看表演工作坊,第五週看莎妹,第六週看京劇」,戲曲和所有藝文活動是並列的,它們在台灣的環境,不是「豫劇跟河北梆子競爭、歌仔戲和崑劇競爭」,而是「所有的傳統戲曲」同為生命共同體,一起和「賴聲川、李國修、林懷民、劉靜敏」競爭。觀眾進入藝文場合就是尋求情感的宣洩和文化的陶冶,戲曲是抒情達意的載體之一,在古典和現代都已混血交融的時代,地方戲劇種特質是否能彰顯,至少在台灣的環境裡,我不覺得是最令人憂心的事。本文願以近兩年內的演出為例,表達我的看法。具體舉證的劇目是黃梅戲《徽州女人》和「兩岸戲曲大展」的秦腔、湘劇。
兩岸開放以來,大陸地方戲來台數量甚多,包括漢劇、越劇、黃梅戲、河北梆子、豫劇、淮劇、川劇、徽劇、評劇、曲劇、潮劇、秦腔、湘劇、梨園、高甲、莆仙、薌劇以及一些地方小戲,票房有起有落:演傳統老戲時,觀眾以鄉親和戲曲研究生為主;演新編戲時,觀眾層面比較不限特定觀眾群而能吸引一般藝文愛好者。回響最大的,早期有漢劇《求騙記》、《美女涅槃記》,後來川劇《荒誕潘金蓮》也因復興(現已改名戲專)京劇版的轟動而受到注意,而近兩三年來最能突破「戲曲特定觀眾群」限制的,則是黃梅戲《徽州女人》。
《徽州女人》以視覺意象戮弄觀眾
我本來並不太喜歡這齣戲,總覺得劇本並不很細膩,許多重要的轉折關鍵不具說服力(例如月光和小青蛙對女子的啟示),可是一進入劇場,就被整體氣氛征服了。所謂「氣氛」,包括一開幕的舞台景觀,以及觀眾在還沒開演之前已經「就位」的情緒。這戲最成功的是「選材」,對台灣觀眾而言,不太會聯想到什麼封建舊社會,關心的只是古代女子的命運,「曾有一個女子在等待中過了一生」,這樣的宣傳基調,吸引了很多不看戲曲的女性觀眾進入劇場。性別意識高漲之後,為女性(尤其是反面壞女人)翻案的作品已經看太多了,很多觀眾很期待拋棄一切「解釋、新詮」,單純地進入古代女性的世界,分享她們的心事;《徽州女人》給人這樣的期待,因此許多觀眾一坐進劇院,還沒開演就先「自顧自地」感動了起來。題材選準了,觀眾情緒已經醞釀到發酵的邊際,只要稍稍「戳弄」一下,便足以引爆強烈的共鳴。這是編導成功的第一步,而接下來更令人驚異的是:這戲戳弄觀眾的手段,不是唱唸做打,而是傳統戲曲一向並不重視的「視覺意象」。
戲曲的抒情手段一向放在演員的表演藝術上,對於舞美、服裝等,雖然越來越有「整體劇場不可缺的一環」的認知,但是無論如何,其作用終究被視為輔助烘托,而《徽州女人》竟然反其道而行,觀眾對唱腔身段並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津津樂道的反而是某幾個畫面,尤其是靜態畫面。例如:男人有音信傳回時,重新燃起希望的女人,穿起嫁時衣,端坐喜床上,喜床先在舞台前靜止數秒,而後緩緩推移往後消逝,這個「被等待框住」的畫面,前後好幾十秒,「喜悅的凝滯」傳遞給人深沈的傷痛,這已經超越了「走位、舞台調度」的範疇,導演像是以舞台為畫板,以演員與服裝與道具為彩筆,推出一幅幅精心雕琢的「塑像」。畫面構圖是這戲的主體,取代了演員表演。大家對女主角韓再芬的印象不在某一句唱腔的轉折,而在她某一個凝神遠眺的身姿形影。這當然和戲曲的亮相不一樣,像是停格,是構圖的一部分,整齣戲就由這些動人的「剪影」堆砌出震撼力量。
最震撼的一幕是終場前半小時,戲進入最後階段,進入暮年的女子坐著看領養的兒子上學去,兒子長辮子一甩,雨傘一撐開,畫面竟然出現了當年女子出嫁時走過的蓮葉田徑!就在蓮葉何田田的景觀開展的瞬間,時間的捲軸倏地翻轉回頭,像是回到生命的原點,四十年辰光,就這麼無聲無息地在布幕一張一閤之間流逝了!《徽州女人》的舞台上有塑像、有情感、更看得見時間,看得見時間的流逝,也看得見時間的凝滯!這感覺令人悸動,逝者如斯,原是不捨晝夜的,而有時,時間竟也可以靜止不動,四十年如一瞬,動與不動間,無情總一般,這樣的感悟不是來自唱詞唱腔身段做表,竟來自「視覺意象、畫面處理」,這是《徽》劇的創意,這不是戲曲的手段,這是現代劇場的技法。
誰想從《女駙馬》聽正宗黃梅唱腔
這樣的觀賞經驗竟與香港導演的現代戲劇《張愛玲,請留言》有些類似。戲演到最後,多層透明景片佈滿舞台,一抹如煙似霧的浮雲緩緩流蕩,張愛玲臉龐的圖像以拼貼的方式交替出現,在奔騰逝水的多媒體影片穿插中若隱若現,這張臉永遠湊不齊對不上,人生多少失落?多少偶然?多少擦身而過?幾許滄桑陡上心頭。此刻,語言退位、情節不再,導演運用的是光影和色澤構成的「意象」。《徽州女人》不也是如此嗎?畫面取代語言、意象營造氛圍,這是現代劇場的處理手段,《徽》劇因此而能觸動現代人的心靈,而能與現代接軌。
或許我對黃梅戲不內行吧,所以只「看見構圖」,沒「聽見唱腔」;可是,這個年代對黃梅戲內行的又有幾人?尤其是在台灣。戲曲要面對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觀眾,新觀眾看電影電視、玩電腦電動,卻未必有戲曲歷史的積澱,要「戳弄」他們的心靈首先要抓準「情緒」,而手段呢,可能要利用一些「非戲曲專業」的元素。果然,不久之後,當韓再芬頂著「徽州女人」的光環帶來黃梅戲經典代表作《女駙馬》時,觀眾就沒有絲毫興趣,沒什麼人想聽正宗黃梅唱腔,這跟韓再芬唱得好不好沒什麼關係,只是《女駙馬》的故事顯然和現代人的情思有距離。
這使我想到去年的「兩岸戲曲大展」,這一系列重要地方戲的展演非常有意義,可是劇場效果卻值得思考。就以打頭陣的秦腔來說,秦腔在中國戲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許多劇種(尤其是梆子腔系)的原始源頭,地域特性非常鮮明,足以與古書燕趙之聲的記載相互印證。引介秦腔來台,當然是一重要舉措,所有的宣傳焦點也都集中在劇種的重要性、歷史意義與劇種的特色——尤其是「絕活特技」之上。不過,如果主辦單位希望這次的觀眾群能在「鄉親」和「戲曲研究生」之外另闢票源,所選的戲就必須在劇種的重要性與特色之外,更具有深刻動人足以引起共鳴的情感力度。
太學術專業的「兩岸戲曲大展」
可是以個人看來,整個系列的設計都太「學術專業」、太戲曲「局內觀」了,強調的盡是劇種的價值、劇種的特色,可是,劇場不是教室,觀眾不是學生,觀眾進劇場要尋求的不是戲曲知識,而是情感宣洩,而秦腔那許多戲,卻顯然技巧掩蓋了情感的本質。像是重點劇目〈鬼怨‧殺生〉,只看到一再重複的「噴火」絕活,卻無法讓人感受到李慧娘對裴舜卿一心呵護的濃烈情意。我曾看過許多其他劇種的李慧娘,也有噴火(技巧不遜色,只是次數較少,只是穿插,不是重點),而全劇在唱唸做打的均衡表現之下,體現出的是李慧娘的懇切情意,因此我心目中的李慧娘一直是一曲動人的詩篇,而秦腔這般「噴火復仇女神」的形貌,卻使我對這齣戲和這個劇種的印象停留在技術的層次,完全無法走進心崁裡。
另一齣《朱痕記‧放飯》裡朱春登正在妻子靈前痛哭悼念時,卻驚覺蓆棚外的討飯婆可能正是其妻,此時演員用了「耍紗帽翅」的技巧,表現內心的疑惑猶豫思索。這套技巧要用頸部力量,難度很高,最初在蒲州梆子〈殺驛〉裡大放異彩,很多劇種很多戲都用過,成為一套戲曲手段,可是〈放飯〉裡面的使用,卻讓人覺得過於炫奇。以現在觀眾的審美需求來說,有時越貼近生活越感人,高度程式化、規範化、技巧化的動作,對於情感的抒發表達,不見得處處合適。
「兩岸戲曲大展」最後一檔是湘劇,共演出四場,兩齣古典名作(《白兔記》、《拜月記》),兩齣得獎名劇(《生死牌》、《馬陵道》),但只有《白兔記》一枝獨秀。
「感動」是劇場裡唯一的情緒
不過《白兔記》的成功絕對不是文宣上說的「湘劇的存古性、宋元南戲的遺留」,而是當代劇作家改編的成功。當代優秀劇作家對於每一個人物的內心都有深入的刻劃,尤其是岳氏夫人。岳夫人是劉知遠投軍之後另娶的妻子,丈夫在沙場征戰,岳夫人在家中擔憂不已,終朝每日盼望丈夫歸來,而盼來盼去,竟盼到了丈夫與前妻生下的小嬰兒,被老僕人送來給她撫養。乍聞丈夫有原配的當頭,她當然不想接下這嬰兒,然而,嬰兒的啼哭勾起了女性特有的母愛,「是喜?是憂?是拒?是收?」猶豫掙扎之際,看到嬰兒依偎在老僕人懷中,「老背小、小倚老,煙硝萬里,飛度關山」這樣的情景打動了她,終於接過了孩子,在「我就是妳的親娘」唱腔裡,嬰兒在夫人懷中止住了啼哭。當燈光凝聚在岳夫人懷抱嬰兒搖哄入睡的場面時,淚水滿溢在台上台下戲裡戲外所有人的眼中,此刻,管他什麼宋元南戲、劇種特質,「感動」是劇場裡唯一的情緒,古典與現代,接軌在情緒裡。
其實演員倒不見得怎麼出色,尤其女主角李三娘,演唱功力顯然生澀,但動人的劇本使她不費力地和現代觀眾取得共鳴;反之,該團資深一級演員左大玢在《拜月記》裡展現了堅實的唱功,卻因劇本太陳舊、人物太刻板而「白唱了」。當戲曲已失去流行地位時,當代的觀眾進入劇場絕對不只是為欣賞演員的唱唸做打——能分辨得出唱腔韻味醇厚與否的觀眾能有幾人?大部分的觀眾根本不管今天看的是什麼地方戲(尤其在台灣,所有的方言反正都聽不懂),只想要看「能觸動情緒」的戲。敘事技法可以盡量多元,無論是京是崑是大戲是小戲是傳統是現代是電影還是動畫,只要不相互扞格,只要能動人,觀眾絕對歡迎。
《徽州女人》不正是如此嗎?雖然劇本有明顯的不足,但導演的確抓住了觀眾,這一點就足以為地方戲在當代的處境指點一條途徑。很多觀眾哭著出場以後只記得曾有一個女子這樣活了一生,不太記得黃梅戲,不會想在這裡尋求什麼劇種特色,更不會期待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徽州女人》和黃梅戲的關聯在哪裡呢?應該只在「通俗的唱詞、旋律以及生活化的身段作表」,而這些劇種特色已潛在融化轉換為整齣戲的基調內蘊,不必強調不必外顯,女人豈止在徽州?西遞村不是一個特定的所在,它的意義是普遍性的,是中國古代封閉村鎮的代表,《徽州女人》豈能為地域特性所局限?運用多元技法觸動現代人心靈,劇種特色「內化」為美學基調,這或許是地方戲和現代接軌的一條途徑吧?
文字|王安祈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編按:
論文收入會議論文集,山西《中華戲曲》21輯轉載,相關論述參見王安祈《當代戲曲》(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