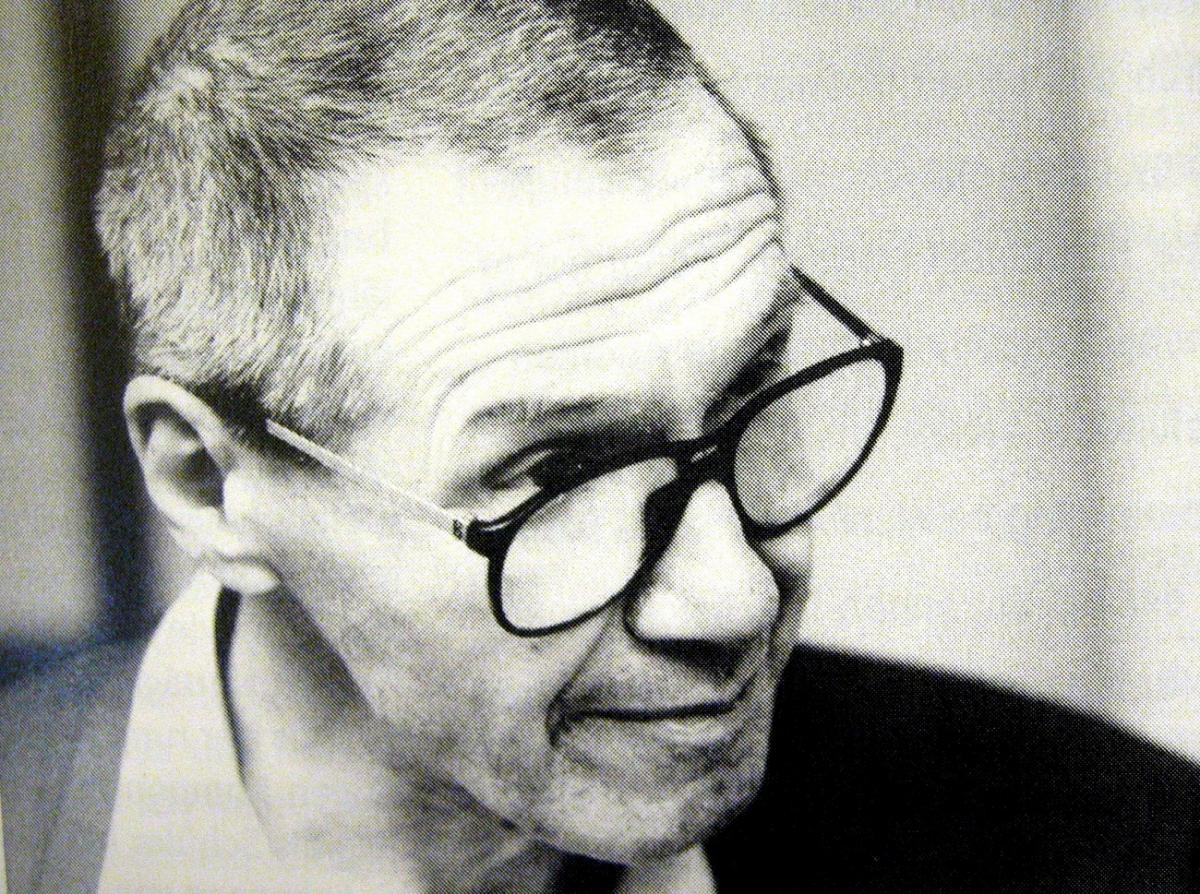面對大批要從情節、劇場視覺氛圍來接受感動的新觀眾,新編戲的編法體現了新的美學,但《王熙鳳大鬧寧國府》卻讓編劇、導演隱身於後,讓我們重新看到「演員」在「編、導」的保障鞏固之下如何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線的位置,演員絕對不是編導手下的棋子。
前陣子聽「豫劇天后」王海玲私下說起:「我最怕被問這齣戲的人物是如何塑造的!我實在說不上來,還不就是『練』嗎,不斷的練反覆的練,唱著唱著韻味神情就都出來了。」她囁嚅地說著,有點不好意思,我卻覺得非常有趣。
這套「理論」並不是我第一回聽見,前幾年在香港見到河北梆子國寶裴豔玲,她更直率,會議當場被問到如何塑造人物時,大辣辣地說:「塑造什麼塑造?『拉山膀』胳膊抬得位置準確就是有人物,偏了低了就是沒人物!分析什麼?回去練功!」
老戲以特定的人象喻普遍的人生情境
台灣四大鬚生之一周正榮先生生前接受訪談時,聽我轉述裴豔玲的話,非常高興地笑著說:「內行話!」接著周先生很詳細地舉例說明「老派」的人物揣摩法:
我們是不講究什麼「人物分析、性格塑造」的,沒那麼多說頭,還不就是不斷唸不斷唱,有時連戲詞都不是十分瞭解,但是唸著唸著就能體會出感情了。光是「分析」絕對不夠,紙上談兵而已,分析出了情緒還得用自己唸白的抑揚頓挫表現出來啊,如果唸得不確實,什麼都白搭。譬如說吧,分析出了人物要莊重,也不是繃著臉做出一副目不轉睛的樣子就真的法相莊嚴了,台上要「眼神」哪,台步一走,要是腳底下功夫不夠,渾身的衣飾、袍角、腰帶都跟著亂晃動,莊嚴立刻就破功!像《搜孤救孤》吧,程嬰勸妻子捨親生子的心情我也能分析出一大篇,可是「性、聽、命、冥」幾個字唱起來音「送不遠、發不亮」還談什麼呢?
像我這麼喜歡《鼎盛春秋》(全本伍子胥),可是我就怕人家問:「請問您是如何塑造伍子胥這個人物的?」我還真怕,不是騙人的!為什麼呢?傳統老戲的劇本並不很「嚴實」,很多地方鬆散、拖沓、重複,不過我要說的不是結構不緊湊,所謂「不嚴實」主要指的是劇中的感情。戲裡的情緒通常很「寬廣」,不一定完全扣緊住劇情,經常是以主要劇情為核心而鬆鬆寬寬地向四周蔓延,有些情緒是「溢」出於劇情之外的,這些地方看起來像是「多餘的枝蔓」,其實卻可以觸發更多更寬的人生感悟。譬如我唱《鼎盛春秋》的〈文昭關〉時,我心裡想著的未必是「伍子胥這一個人」(特定的個人),我想的是「遭遇人生大難的人」,是普遍的人生情境,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處境,也就是人類普遍的情感反應。我盡可能地唱出「危急困窘」的情緒,可是我未必完完全全想著伍子胥。我唱戲的享受就在唱出一股人生況味,希望我的唱有撫慰、宣洩的作用,至於是不是只限於伍子胥,我並不那麼在意,因為劇本本身也就不著重在描寫他所遭遇的具體事蹟,只是藉大段唱讓他抒發情感而已。(註)
新編戲的編法體現嚴實的新美學
幾位藝術家真切地說出了老戲的特質,這不只是演員揣摩人物的特質,更是劇本編寫的特質。不過新編戲就不可能這樣處裡了。新編戲通常都嚴嚴實實,邏輯脈絡一丁點兒都不能錯,演的是實實在在的劇中人,不再是以一個特定的人象喻整個人生情境。就拿紅樓戲《葬花》來說吧,民國初年梅蘭芳演黛玉時,重心就在出場的「西皮倒板」、「慢板」,葬花時的「二六」和後面聽曲時的「反二黃」,沒有什麼情節事件,甚至身段也不多,就從唱腔音樂裡傳遞一股飄零的意態。文獻裡記載當時一位觀眾說,他每聽葬花,心情就要鬱悶好幾個月,一股說不出的抑鬱壓在心頭,久久不得紓解。這股動人的力量,並不是來自劇本的情節(根本沒有情節可言),而是演員的唱工。所以梅派《葬花》一直是名貴的,唱不出這股神韻的演員通常不敢動此戲。不過那是民國初年的事,是京劇以流行音樂身分通行全國的時代,到了近幾十年,京劇音樂明顯地退流行,觀眾根本分辨不出韻味了,進入劇場也不為聽唱;面對大批要從情節、劇場視覺氛圍來接受感動的新觀眾,新編戲的編法體現了新的美學。
新編戲的性格塑造是從「人物面對事件的反應思考抉擇」中呈現,不能再以大段內心獨唱「自剖心境」了;抒情唱腔的分量不能多過敘事唱腔,「點線結構」(線是情節推演、點是抒情重點,傳統戲藉唱抒情時情節往往停滯不前)的傳統特質也漸次打破,「嚴嚴實實、邏輯分明、曲折變換的情節」是新編戲的根本,由「衝突、懸疑、逆轉、發現」所營造的必須是「情節高潮」而不是傳統戲唱腔所傳遞的「情感高潮」,所有情緒的抒發都包融在情節轉折中,不可能單獨抽離表現。仍以「葬花」為例吧,「葬花」絕對是純粹抒情的段落,但是筆者在一九九○年新編《紅樓夢》時,就不敢把「葬花」當作單獨的抒情重點,而是把它放在連串的情節中包裹處理,即:以透紗天幕分割前後兩層舞台,黛玉(魏海敏飾)在紗幕後以慢動作葬花,寶釵(朱傳敏飾)以正常速度在前面正場撲蝶,而後交錯王熙鳳和賈蓉的不軌情事,再以寶釵的嫁禍接回黛玉葬花唱段。程序如此複雜,戲才不覺單調。一九九一年馬蘭主演、余秋雨藝術指導、陳西汀編劇的黃梅戲《紅樓夢》也沒敢把「葬花」放大成抒情重點,簡單數句淡掃輕描,隨即轉入「敲門不開就踢、就砸」,作為和最後寶玉哭靈時捶打棺木「重拍門板都不應」相呼應的情節伏筆。
王熙鳳的戲劇性恰好對上新編戲的特質
不過,以寶玉、黛玉為主的紅樓戲,無論如何都還很在意維持《紅樓夢》的「詩意」,免不了用大段留白、抽離的唱,表現「由情悟道」的過程。王熙鳳卻不同,這位戲劇性強得不得了的人物,恰恰對上了新編戲「以情節高潮取代情感高潮」的美學。逼死尤二姐一段原書的故事就就足以佈局成戲,編劇紅樓老作手陳西汀的《王熙鳳大鬧寧國府》一劇最突出的表現在語言,韻文唱詞寫得機鋒銳利,看似明白如話,其實卻是深厚的文學功底孕育而出的,而這是戲劇的語言,不是學者作詩填詞,節奏感十足,戲劇感十足。憑藉著這樣的語言功力,一個個鮮明的人物活脫脫地躍上了舞台,其中「秋桐」的人物塑造甚至強過原書。
對於王熙鳳,編劇並沒有用「表面化的女性主義」為她加一些空虛寂寞的感嘆——這些在京劇裡其實是很好加的,「點線結構、自剖心境」都是現成可用的理論,可是陳西汀老先生沒有這麼做,倒不全為著戲劇結構的嚴實,而是從人物談人物,大鬧寧國府的王熙鳳機關算盡勝券穩操,忙著出招攻擊的人哪裡來得及寂寞?整齣戲飽滿到了極點,「蒼涼」是從滿座笑聲的背後悄悄透露的:舊社會一夫多妻制度下強悍如王熙鳳都只能以吃醋為手段確保家族中的地位,女性的悲哀何須多言?
這齣戲於一九八二年在香港首演之後,主演者國寶級藝術家童芷苓即轉往美國定居,一九九○年來台演了一場,不久即過世。如此精采好戲豈容戲隨人亡?國光劇團即將由魏海敏主演王熙鳳,王海玲客串老祖宗賈母,讓《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重現舞台。劇團排練此戲的過程刻意「反現代」:先直接練唱練唸白,表演熟了之後再請紅學專家來作人物分析,演員再從細節上調整。魏海敏這十幾年來潛心學梅,功夫下足了之後,這回從梅派劇目中翻騰而出擔綱新戲,梅派的「大方、派頭、貴氣」內化在舉手投足一身氣韻之中,而「京白」與「演技」不僅是荀派的、童芷苓的,更是王熙鳳的,魏海敏將以較她在「當代傳奇」飾演馬克白夫人時代更為成熟的姿態,施展覆雨翻雲的伎倆手段。這次演出,不僅是這位傑出演員心防的突破,更是藝術層次的躍升,同時更可以讓觀眾重新看到「演員」在「編、導」的保障鞏固之下如何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線的位置。
演員在編、導保障下再度站回舞台第一線
二十年前海峽兩岸都有很多精采的新編戲,當時展現的是編劇的新技法,而近十年來導演的手法越來越多,隨著科技的進步,劇場的「玩法」也越來越讓人目不暇給。在這樣的趨勢下,產生了很多好戲,然而,每當夜闌人靜獨自靜聽老唱片時,卻不自覺的興起一份「慚愧」的感覺,當視覺氛圍快要取代演員表演的時刻,戲曲的本質在哪裡?導演精心構設的Pose畫面經常與戲曲身段無關,演員的唱腔韻味更無足輕重,那麼,幾十年練功為的是什麼?
《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或許是我們徘徊在「傳統、現代」甚至「編劇、導演」的時刻可以提供思考的一個實例吧。《王》劇希望清楚純淨地呈現劇本和演員,導演則隱身在後,不企圖以視覺效果取代文本價值,「看不見的導演」應該是最優秀的導演吧?至少對戲曲而言。其實這齣戲的編劇也隱身在後,大量精采的唱詞唸白不是編劇文辭的展現,而是提供演員充分發揮的機會,劇本保障了品質,卻把演員推在第一線,演員絕對不是編導手下的棋子——不用任何手法掩蓋表演的本質,這是深切體會戲曲特質的編劇所做的處理。
註: 王安祈《寂寞沙洲冷——周正榮京劇藝術》,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編印中。
文字|王安祈 清華大學中文系所教授
吃醋,秀出了什麼?
談「王熙鳳」的戲弄與假扮
康來新(中央大學紅樓研究室主持人)
吃醋無疑是王熙鳳的招牌戲碼,首先,量就驚人,再來就是不斷工研,每多創發,與尤二交鋒,尤其渾身解數,特別是假扮賢良,秀出了《紅樓夢》「假作真的真亦假」的弔詭曲折,稱得上是獨家絕活。
吃醋,嗅出了什麼?除了「酸」以外。
吃醋,秀出了什麼?除了「妒」以外。
王熙鳳吃醋的力道演出並非個案
因為吃醋,王熙鳳不惜教唆訴訟、偽造官司,使青天所在的都察院黑幕重重、無中生有、暗盤交易、以假為真,刺鼻可聞,自是婚姻危機下的強酸四溢。此外,嗅覺可感的還有:司法病變的「腐」味外泄。是的,惡質的金權,勢力太壯大,弱質的正義只好被戲耍、被玩弄。
司法病變,那麼立法健康嗎?健康的精/卵結合本是受孕、懷胎、傳宗、接代的首要,然而,以前的醫學不這麼認為。孕或不孕,有子或無子,責任全在女方。所以,相對而言,婚姻之法較保全於男、較欠缺於女。自《禮記》始,在一男多女的設計下,便明令前者可以主導後者的「七出」之條,其中「無子」與「妒嫉」常互為因果。所謂「妒」,乃特指為人妻者對丈夫納妾權的侵犯,而妾之所以可納,是為了宗法家族的繁衍擴大,「妒」則妨之害之,故有罪於夫家,妻因妒被夫掃地出門,具有百分百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換言之,立法和司法差不多,腐矣、病矣。正是這不健不全的結構,加速惡化了有瑕有疵的人性,乃至「妒」的人口激增,「吃醋」形成的隊伍,每多形象鮮明的力道演出,《王熙鳳》並非個案。
〈跪池〉的柳氏值得另眼相看
在戲曲的表演藝術中,崑曲的〈絮閣〉、〈跪池〉堪稱吃醋檔案的代表作。《長生殿》裡,環「肥」的楊貴妃排擠梅「瘦」的江采蘋,不僅是權力的較勁,所涉造型兩極的審美之爭,也每每成為醋事妒史的不可或缺。至於罰跪花心丈夫的柳氏,更是「妒」之所以為「醋」的由來。蘇軾取笑好友陳慥好佛,只可惜獅吼力度的如來正音聽不到,時時灌耳的卻是柳姓妻子高分貝的妒悍訓罵。於是,柳女妒聲與陳慥好佛與獅吼佛音,誕生了「河東獅吼」的典故(「河東柳」是不忘本的「姓」表述,就像「隴西李」、「魯國曾」)。又據說獅子嗜酸,每天必喝酸奶、酸醋各一瓶,於是,妒婦與獅子,獅子與嗜酸,又誕生了妒婦吃醋的說法。
其實,獅子吼功未必是柳氏吃醋的稱道處,相較於女吃女的妒婦行徑,如呂后之於戚夫人,潘金蓮之於李瓶兒……,例子不勝數,柳氏直接挑戰第一性,頗有捋虎鬚、批龍麟,與父權怪獸相搏的匹婦之勇,值得另眼相看、別有評價。
從《金瓶梅》的西門慶到王熙鳳
王熙鳳無疑是舞台型的人物,麥克風聽她的,聚光燈看她的,她呢,台詞輪轉,走位自如;或搞笑或催淚或爆料,樣樣精到;要喜要悲要鬧,都難不倒這位水晶心肝、玻璃人兒。
吃醋無疑是王熙鳳的招牌戲碼,首先,量就驚人,賈璉恨不得打爛這「醋罐」,小廝興兒更以「醋缸醋罈」喻之,以別於一般容度的「醋甕」。其次,濃度足以致命;再來就是不斷工研,每多創發,與尤二交鋒,尤其渾身解數,較之於多姑娘、鮑二家的前例,且精進多矣;特別是假扮賢良,秀出了《紅樓夢》「假作真的真亦假」的弔詭曲折,稱得上是獨家絕活。
小說《紅樓夢》結晶了詩歌文學的「抒情」唯美,入敘事傳統的「世情」微肖,當搬上舞台,梅派〈葬花〉屬於前者,里程碑的越劇《紅樓夢》也偏愛抒情國度的寶、黛,戲劇張力則在於「世情」介入的掉包之計,鳳姐的關鍵作用大矣哉。
劇場畢竟不同於書齋,「期待」不同,「接受」有異,所以「抒情」會淡出,「世情」能當道。《紅樓夢》中「金瓶」屬性的人與事,往往一演再演,二尤與鳳姐最足說明。王國維視《紅樓夢》悲劇為慾望美學的演繹,而人欲與天理的辯證,《金瓶梅》可謂淋漓盡致矣,慾望城國的天王是西門慶,到了《紅樓夢》,則變性為天后王熙鳳,她擔綱了世態、人情、金錢、權勢、風月,好戲連連,比三綱五常下的女範好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