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舞者的樂章》抽離了兒子拍攝母親的角度,以全觀歷史還原了林絲緞的傳奇與時代性,從日本父親返回日本,母親未婚生子,從小受盡嘲弄,鍛鍊出她的頑強性格;在保守年代擔任人體模特兒並開先河舉辦人體畫展與攝影展;婚後轉往舞蹈演出、進修與多元的舞蹈教學生涯都勾勒出林絲緞在台灣的美術史、攝影史與舞蹈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性與獨特感,但卻好像被歷史遺忘般的忽略,透過紀錄片的客觀陳述,讓所有人重新認識了林絲緞,在那保守年代的異樣眼光,以及她對舞蹈的終身熱愛。

一年多的疫情環境也讓全球不少觀眾日益習慣透過網路平台欣賞藝術展演的模式,甚至喜歡其廉價與便捷。當日新月異的人工智慧和虛擬科技逐漸攻占視覺、聽覺,甚至嗅覺與味覺的表演領域,滿足人類在這些感官享受的需求後,觸覺上的回饋或將是數位世界仍待突破的終極門檻。換言之,連結於指尖和大腦頂葉間的千萬個神經元,將成為人類傳統感官世界的最後防線。

評論通常預設是給親臨過現場的觀眾看的,可是啟發我們的那些思考和書寫,有一大部分是為了沒看過戲的不在場者而寫的。這樣的話,評論應該包含一種「不在場性」才對。先問你:為什麼沒去看這次人力飛行劇團的《感傷旅行》?

最近,小提琴家們在德國的海關遇到了很多問題。原來,一些小提琴家在抵達法蘭克福機場後被無故攔下,他們甚至不居住在德國,或只是來轉機而已!可是他們的樂器居然被沒收或是扣留,這下子引起不小的爭端。

安德烈.巴贊說過「電影家如果忠實於原著,自己也會獲益匪淺」,我想他講的一定是羅伯.布列松的《鄉村牧師日記》。只有刪減不做傳統的戲劇性改編,大量的日記旁白跟畫面交錯,鏡頭緩慢地貼近臉像凝視受苦聖像,演員不表演只念出小說的日記體跟對話,強調「貼近原著」,風格獨特。

聲韻學《玉篇》註記:「旁,猶邊也,側也。」旁白的「旁」,不在其位,注定了偏離的出身,是旁觀、旁聽、旁敲側擊,旁系姻親,指認了置身事外,抽離、拉開、隔岸觀火的位置。旁白雖是熱鬧的語言,但不處於正室,旁言旁語,難獲得重視和矚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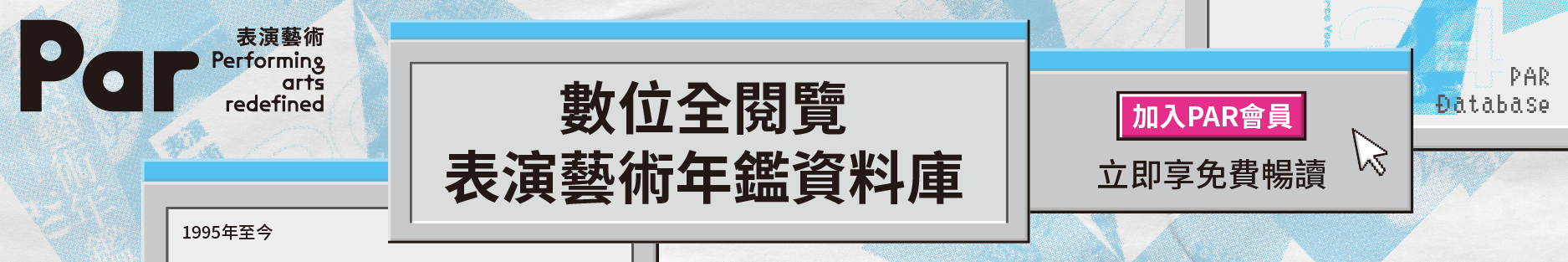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揚聲器也可以製造出不同空間,例如明明就是中性的電影院、劇場,隨著音質改變,就可以變成市場或是空曠的荒野。

啟動快樂熱點的關鍵元素,是大腦所分泌的多巴胺:這種物質常和快樂、愉悅的感覺相關。

一首歌,一個深藏內心的秘密。夏天中,離過兩次婚又經歷情人自殺的34歲女子,邂逅了一個剛滿18歲的義大利學生,意外地懷孕、墮胎,造成日後的不孕。

或許是因為是劇場,所以即便是一個倉庫般的地下室,都能夠是一個無限擴張的宇宙現場。是因為這能夠在劇場中發生所以我覺得美好,還是那本身就是個美好的發生;或之所以我覺得美好,是因為這裡是劇場,這與劇場關聯,還是,這本身單純就已然是美好的。有的時候我分不清楚,很多時候,我都分不清楚。

對於藝術家來說,所謂挑戰,在於如何創作出概念和思想碰撞衝突,卻又兼容並蓄的作品,進而將我們從每天的日常中,提升到不同的層次。作為劇場吧檯的調酒師,我們如何使觀眾能夠同時品嚐到威士忌、麝香葡萄、香蕉、白可可、牛奶?而同樣重要的是,是如何建立足夠的自信,以及對觀眾的信任,提供充足的空間,讓他們在獨特而複雜的劇作脈絡中理出頭緒?

目前Netflix的原創電影中,缺乏傳統片廠的商業大片,破億美金的製作偏少,Disney+ 擁有皮克斯、星戰、漫威系列等影片,未來絕對是Netflix的強勁對手。相較於影視的商業化程度,表演藝術演出的影像記錄,會不會是門生意?還是只是延續朝生暮死的火花,Marquee給了表演藝術一個可能的嘗試。


有趣的是,帕羅曼本身更喜愛流行音樂,對古典音樂興趣卻不大,曾力主讓流行樂重登卡內基廳舞台而引人側目。2015年他初升任卡內基廳董事長後才8個月,就因內部紛擾請辭,一度讓美國樂壇為之震盪。更有趣的是,有生意機會就不放過的帕羅曼,過去居然也曾經手過蔚為美國通俗文化經典的漫威漫畫公司!但那是漫威歷史上最黯淡的一頁,直到脫離帕羅曼的髒手,漫威才開始邁入近十餘年的光輝歲月。

分享幽默笑話一則:一位正在學中文的外國人,在一次參加朋友婚禮時,很有禮貌地讚美新娘非常漂亮,一旁的新郎聽了謙虛地代新娘回應:「哪裡哪裡!」,外國朋友聽了一驚,想不到籠統讚美竟不過癮,還要說明哪裡漂亮?!於是硬著頭皮用生硬的中文說:「頭髮、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漂亮!」,語畢引得哄堂大笑,好不滑稽。

劇場裡,總有股心照不宣的壓力,促使作品演出長度維持在70至150分鐘的規範內。遵循「長度攸關」的結果是,一些劇團將原本可以是美麗詩篇的作品,膨脹成了小說。對演出而言,並沒有所謂單一標準的適當長度,作為藝術家,我們必須具備捍衛作品真實性的能力。即使初吻和流星轉瞬即逝,它們也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剛開始時,黃明川其實先找了表演藝術領域,卻連續被兩個團體拒絕,之後接觸視覺藝術圈,卻得到藝術家熱情的擁抱,因此他才轉往視覺藝術領域。這答案對我而言並不意外,那個年代,許多表演藝術家認為他們的作品是立體存在於在舞台與時間上,無法以影像的平面與語言再現,更不適合剪接的斷章取義。我尊重這樣的想法,但時代在變,這麼多年過去了,表演藝術留下什麼?只存在少數觀眾的回憶中嗎?

漫威影業自成一格的拍片文化也有其問題,就是導演無法全權掌控影片風格和劇情導向,多受制於上級機關迪士尼公司和部門總裁費基的想法。導演因意見相左而求去,甚至臨陣被開除的情形時有所聞這也讓筆者非常好奇首次拍攝超高成本科幻片,大量以綠幕取代她原本所擅長野外實景的趙婷,在導演《永恆族》的過程中是如何調適和因應漫威影業的幕後牽制?

好的劇作家不會隨意安排登場角色,再沉默而卑微的角色都有其辯證存在的意義。創作從來都在處理當下的歷史命題,每個細節都應精實推進。


小提琴本身圍繞著許多傳說:許多人認為好聽的小提琴,彷彿地獄的魔鬼出來誘惑;有時它又被賦予童話般的魔法,因為「每一把在唱歌的小提琴,都伴隨著一把才要起舞的Fidel」。

形塑出來什麼樣文化,進而影響到人與人的相處、社會氛圍的構成,進而影響到形形色色的創作成果。刻板印象最簡單有效,最後,形塑出來的「故事」,會奪去人們的尊嚴。

對白,作為表情達意的媒介,關乎角色之間的相遇、意願和揭露。關係是需求,更是意義所在,說了什麼,沒說什麼。

我們都是從現實生活中透過劇場的門,進到另一個想像世界。若把門的組成拆開來看,門需要一個門框,而加上門板前的門框也只是一個通道,門框下方如果高一點,就變成門檻,再高一點就變成窗框。

當我們的耳朵接收到音樂,刺激進入大腦,腦部的不同區塊便開始處理訊息:旋律、音準、音色、節拍等元素,會由不同腦區負責。大腦將這些元素分析完畢後,會重新組合成完整的體驗,讓我們有所感受。

身體是柴,愛情是火,人不是畫個道德框框就可以完了的,往往計算機按爆了,一加一還是不等於二。說穿了不就是為了一點溫暖?你嫌它猥瑣,上蒼用石塊懲罰,布爾喬亞去教堂告解,五百加一千種懺悔的方式,然而無悔,生命才能代代傳遞。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