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是一個可以把環境暫時分開,分隔成內外的一個生活空間,家也是一個可以休養生息,凝聚自我跟親人的生活空間。回到家,睡覺都睡得不想起來,所有的事情可以暫時「不視」、「不想」,其實又都「視」都「想」過了,因為輕鬆了,意念更可以集中了。

我們可不可以跳開來看看通盤的畫面,那些不安與焦慮真的有必要嗎?還是只因為身陷在單一思維裡而有的無明。重點在我們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和對別人有沒有信任?解開這些信心問題,我們是有可能讓孩子快樂地玩耍長大,讓工作有充分的授權,事情做得少而美,然後不怕輸,不怕錯!

音樂節結束後,我到巴黎去走走,還去了拉雪茲神父公墓──那是個埋葬了超過七萬人的巨大墓地,在門口可以買到墓園地圖,你可以循著它找到最愛的「死」明星。當時,我想找的是我最愛的「死」蕭邦,但在發現它時,我感到非常地震驚,因為那和我想像的很不同。他的墓不但不孤獨,更不像是他奏鳴曲中那被遺忘的墳墓一般淒涼。

誰不想要格局大呢?誰不希望作品大器?蔡明亮的《愛情萬歲》、侯孝賢《海上花》、李安自己的《斷背山》,在製作過程中有想過格局要大這件事嗎?有可能因為想要格局大,作品格局就會變大嗎?曾經在過程中作了格局要大的決定後,有效嗎?結果是不是格局反而小了?一直蓋「大」劇場,劇場生態、格局、票房、觀眾就會變大嗎?政府期望國際化的文化政策,是否反而削弱了文化的根基和成為所謂國際化的創作潛質?

演員都會希望自己所演出的東西,被人看懂,被人喜歡。但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的現象有的時候也會很長,所以包括老演員在內,至今還不會演喜劇的也不少。想學演戲的年輕人不少,也不多,學得順利而又能成家的人當然相對地減少,都想突出,都想成名但是,「佛渡有緣人」,電視、電影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學習表演的地方。

情感畢竟是非形體的存在,它靠體會與感受去發現它的蹤跡,任何一個打算把它描繪個究竟的努力都極有可能是徒勞的。所以情感無形,它是圍繞在形體四周的空氣,但也因為有賴以駐留的形體,所以如空氣般的形體能有所聚集不會消散開來。但什麼樣的形體可以留給情感空氣更多圍繞的空間?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特別身為運用形體表現的舞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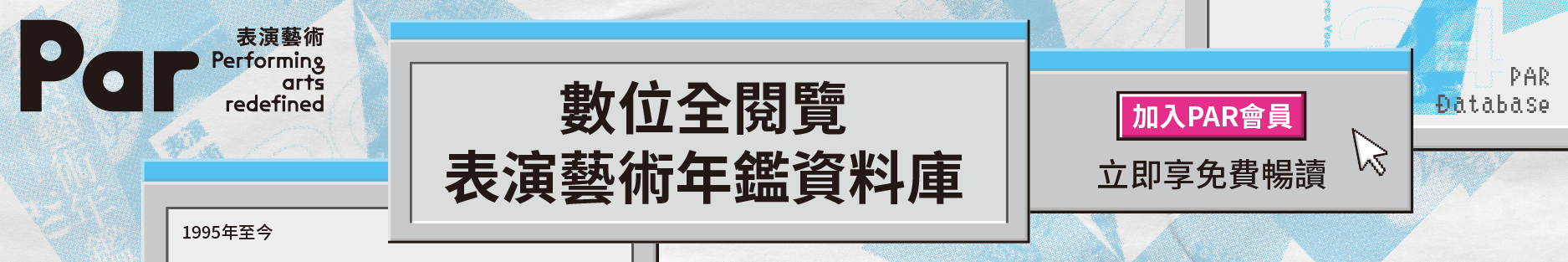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當我正在浴室水槽中洗衣服時,我聽到廣播正好播放了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幾乎是瞬間,音樂的能量進入到我的身體,我洗衣服的節奏開始搭上樂曲的韻律。搓、揉、搓、揉、沖、擰,再重複。不僅工作變得容易,我開始又有了洗衣服的熱情。

將英文音節式的語言轉成中文音韻式的語言,要參考的不是成語字典或詩詞,而是林強的《向前走》。不過若真的要將莎劇變成流行歌曲或是音樂劇,又太我會尊重的。再回到莎劇原點/典,莎劇原本就是演出本,那我們應該尊重莎劇劇本裡的文字?還是尊重莎劇以文字聲音給觀眾punch的能量結構場?當然,對於莎劇專家的觀點,我還是會很尊重的。

他只扶著我不到十秒鐘吧!手就鬆開了,人也不跑了,就在後面叫:你會了!你會了!我一下子覺得:這不就是會騎車了?會騎大人的腳踏車了!這莫非是太幸運了!我會騎車了!春天來了!說著說著,不會轉彎的我,煞了車人就落地了,沒跌到,算是軟著陸,又給我興奮地騎了幾圈,會轉彎了,莫非是天晴了?樹上的鳥叫聲都跟著繁雜了,我的春天算是來了。

在宗教中的求善應是不容魔鬼存在的,而在藝術的追求中,善與惡的界線就不是以二分法可以名狀的。也許天使的面具下隱藏的是魔鬼,在魔鬼的試煉下為的是分辨出天使的面貌。而這都是人對待自身生命問題的求解路徑。有答案嗎?不得而知,因為生命就像一個無始無終的段落,每一個生命只能在其有限的時空接觸下,得到他所能應證的面貌。

無論是彈到哪種爛琴,都是痛苦的經驗,都很難讓人真正進入音樂、享受音樂。因此,鋼琴家只好在此尋找一個平衡點。因為,通常鋼琴家是沒辦法帶著自己的鋼琴到處去演奏的。你,有辦法嗎?

「一」不理解「多」的遊戲是有規則,關係是為了他人,反而因為二元的理性想像,開始害怕遊戲的失控和關係的雜交。「多」理解「一」的二元,但不同的是中間那一槓的擺法:不是/,是 。電影的focus也不同,不在對立的兩端,而在對話的之間:是男女之間的彩虹、自然人的樂章、對錯聯結的地景、多一交互華麗的編織。


原來表現的另一層意義,就是要被知道、被鼓勵、被欣賞,然後,才接受被批評、被責備。那還等什麼,該告訴誰就趕快告訴誰吧!只是別說謊,別把不良的「表達習慣」,放在舞台上,浪費時間。因為「表現」並不是可以被無條件地欣賞或讚美的,跟阿諛或自戀更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問題根本不是在有沒有國家舞團,而在於什麼是「我們的舞蹈」,台灣的舞蹈?天啊!這問題能有一個出口嗎?所以在一九八○年代末小劇場運動開始蓬勃時,舞蹈人如釋重擔地開始了做自己的舞蹈這條路。現在有更多的舞蹈人口只願提當代舞蹈,至於這個當代到底是什麼的混血也不用追究了,重點在於要跳自己相信的舞蹈。

那種風的強度不僅像颱風,也讓溫度似乎又少了廿度,而且它輕易地就穿透了我的四層衣服,就好像刀子在切豆腐一樣容易。當我跑向一個蒙古包時,我又想到了德布西的曲子。風在空曠的草原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礙它,堅毅的風絕不可能從草原上消失。

多不像一,隨時會失控大罵很正常,隨時準備接不知從哪兒出現的招很必要,得隨時訓練自己能夠在人性的深海裡浮浮沉沉而不沉沒滅頂,「一」如果是公子哥兒,「多」則是俠客。

她的黃山,看上去,近處有兩棵黃山典型的倒掛松,工筆完成,遠處、中處、近處,就是黃山陡峭的山峰,沒有什麼墨,整張畫紙就像一座明朗的大山叢中,淌滿了雲海,雲海不過是濃淡相間的數筆,就覺得大氣磅礡,比「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還要開展,還懾人心魄。我問她:你是怎麼會畫成這樣的?她說:我親眼看到它們的瞬息萬變過。

往往當我們的身體出了狀況時,才體會到肉體的存在牙痛時才感受到牙齦,扭了腳踝才感受到自己的重心,生病了才知道原來精力能量是這麼一回事。當還來得及時,身體的微恙能讓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更有感覺,似乎也不是那麼壞的一件事。


我經過大廳旁的餐廳,聞到了海鮮味,突然想起,這是一首我曾在海鮮自助餐廳彈奏過、賺過慷慨小費的聖誕歌曲。這首歌結束後,接下來播放的,居然還是聖誕歌。雖然現在才十月,但我的腦子裡已經湧現了滿滿對小時候聖誕節的溫馨記憶。

字的聲音與意義在行為的河流中彼此相依、相怨、相思、相沖,愈想說清楚卻愈說愈曖昧,愈說愈糾結。再加上一串中文字鍊成了一排咒語,念咒聲喚起聲前肉身的幻影、迷戀與迷惘,這是為何崑曲一個字可以唱這麼久,也是為何崑曲如此迷人與迷幻之處。

如今,我都過六十了,看看那個時代的人,那個時代的藝術,風塵僕僕而又帶著浪子的慈悲,獨立蒼茫而又瀟灑地從世人身邊走過,他,主唱者,Freddie,把他自己充滿痛苦和驚豔的人生遭遇,通過努力學習、反省、團結、表現、藝術加工以後,美呆了!若說人生有何意義,這不就是一種意義?

我手執必要的工具,就像打網球般地對準飛向我的球迎面回應,有的球回得漂亮,有的差強人意,三不五時難免也會揮拍落空,這絕對跟球技有關。但一路就已無閒情餘力去張開這個不超過六個人就可以和世界上所有人連結的大網。 本來是一路只管往前迎去的,直到來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回頭一看,才發覺原來背後跪了一排的人,這些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貴人。

他就是那種會不顧自身危險縱身跳下馬、帥氣地往泥地裡甩出他的外套只為了不讓要拯救的美女弄髒小腳的人。這本小說是部喜劇,描寫唐吉訶德努力嘗試維持這些當騎士的準則,但他總是陷入荒謬、弊大於利的狀況中。實際上,這本書是在取笑老掉牙的傳統騎士精神,就像個高中生在笑自己祖父母的老舊觀念一樣。

一個人的自我中心不是錯,本來就會這樣,或是說,從這基礎點該如何往下走才是重點。所以,用「自大」或「自我感覺良好」解釋一個人的行為或一齣戲是無效的,因為可以通用於每個人和每齣戲,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論述和更多細節的探討,就是廢話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