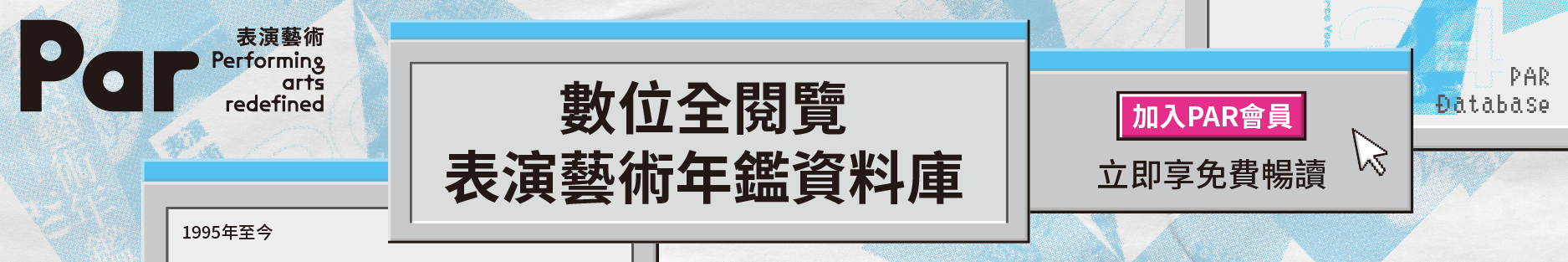以藝術點燃人權之火
記巴西劇場大師波瓦94歲冥誕與「316被壓迫者劇場日」許多年以前,我們一群戲劇、教育界的師生,在波瓦工作坊的休息時間圍著他提問。那是個沒有AI、就連維基百科都還不風行的年代。我問波瓦,「為什麼你的任何一本書都沒有提到你的生日?我翻遍了好多的文獻資料才找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是啊,的確都沒提到,到底是哪一天?他邊喝著咖啡邊笑著對我說,那你現在知道了嗎?我很驕傲而大聲地回他:3月 16日! 1931年3月 16日是提出「被壓迫者劇場」理論體系的劇作家兼導演波瓦(Augusto Boal,1931-2009)的生日,2017年12月 21日,巴西政府正式簽署法令,明定3月16日為國定「被壓迫者劇場日」(Dia Nacional do Teatro do Oprimido),以紀念這位在戲劇界奉獻超過半個世紀的巴西劇場巨擘。曾與波瓦共同創辦「里約被壓迫者劇場中心」(CTO-Rio)的杜爾勒(Licko Turle),近幾年為了在學院推廣被壓迫者劇場,成立「被壓迫者劇場學會」(GESTO),今年正逢《被壓迫者劇場》一書以葡文在巴西出版 50周年,於是學會成員於3、4月間,在全巴西各地自動發起慶祝波瓦生日暨「被壓迫者劇場紀念日」系列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