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囝仔轉大人
歌仔戲如何演繹史詩悲劇《秋風辭》顯然有龐大的企圖,企圖把史實點滴一一交代,卻囿於支線太多,敍事凌亂,無法像《曹操與楊修》簡明暢快,大切數塊。在試圖用人物獨吟、唱唸之中交代內心情緒之矛盾痛苦時,又無法像《金龍與蜉蝣》賦予凝聚的畫面。所以,用內容演繹悲劇,《秋風辭》劇情還有待爬梳簡化,用形式塑造悲劇,《秋風辭》導演手法差強人意。

《秋風辭》顯然有龐大的企圖,企圖把史實點滴一一交代,卻囿於支線太多,敍事凌亂,無法像《曹操與楊修》簡明暢快,大切數塊。在試圖用人物獨吟、唱唸之中交代內心情緒之矛盾痛苦時,又無法像《金龍與蜉蝣》賦予凝聚的畫面。所以,用內容演繹悲劇,《秋風辭》劇情還有待爬梳簡化,用形式塑造悲劇,《秋風辭》導演手法差強人意。

對孩童而言,「傳統」根本是一個遙遠的名詞,所以,在劇作品質的甄選上,應該更嚴謹審愼的篩選把關,透過孩子的眼睛來看戲,不要扼殺小觀衆們享受「童趣」的權利,但是又需要具有超前的意識,深入淺出地設定主題立意;再者也能巧妙組合各種藝術手段,從傳統中蛻變創新,讓舞台投射出各種能量。

《騷動的靈魂》呈現出的精緻性特質,可證明藝術家們同步成長是重要的,缺一環則很難成爲一件好作品。

編舞家通過生命中最激奮的記憶,創作出她心目中的《黃河》,我們寧願相信劉鳳學是爲了找回某種在這個時代已經失去的肉體力量,更是她以這樣古典意味的肉體禮讚,歌頌她對生命活力的崇拜。

當馬友友面對極艱難技巧,或突然轉變爲如歌般的對比樂句時,他靠著敏感的肢體反應,表現得毫不紊亂,也不會有脫節的情況。

幾位出身上海的名家,在不同的器樂領域創造了演奏風範,雖然都五十好幾的他們演奏技術已過了年輕時代的最高峰,但洗練的風格,沉穩的氣度,對樂曲深刻的理解,仍是後人學不完的。

雖然黃英是一位典型的花腔輕女高音,卻有著這一類聲音少有的低音,展現了她音域的寬廣和戲劇性。


從節目的安排上,我們可以淸楚看到這是按照道敎「洞經」科儀的演出,只要樂聲揚起,一種說不出的氣氛立即感染全場,大家似乎已忘記是來聽音樂的,當潛心進入納西古樂樸實無華的樂聲中,只覺整個身心受到一股難以言喩的洗滌。

與其將《露露聽我說》解釋成婚姻的第三者,筆者寧可將之視爲現代人的心靈失衡。許多人在世紀末的光怪陸離中失去了自己,期望透過別人的經驗、算命、風水、心理分析等方式,找到一個可以依循的方向。

上、下舞展在室內、戶外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條件下,不同的視覺穿越層次,表現了舞台空間的多元深度。編舞者突破傳統舞蹈窠臼的用心淸晰可見,但若能更強化肢體動作間的聯結與美感,激發互動辯證的能量,這實驗性的步伐將走得更穩健。

同樣是以精緻文化的提煉爲信念,以新古典折衷主義的手法創作舞蹈,兩位編舞家儼然把劇場舞台所賦與的性別角色,作了一番明確且肯定的詮釋。如果說季利安這三個舞作是嵌陷於西方傳統的性別衝突之中,則劉鳳學的《起手板》卻有意爲中國傳統女性建構一個平和的風範。

全劇的基調是輕鬆詼諧的,散發出濃郁質樸的生活氣息。雖然就劇作的深度而言,沒有歷史劇深沈的人文底蘊,也沒有公堂戲鮮明的政治嘲弄,但卻體現出市井百姓掙脫禮敎規範,主動追求情愛的眞實情感,也側面地表露了客家性格的堅韌與執著。

調笑戲弄、諷刺滑稽,一向只求效果,不究邏輯思維。然而受制於寫實風格與傳統嚴謹的編劇手法,這兩齣「滑稽戲」原本擁有的一雙超現實的想像翅膀,不但中途折翼;與其他正統的戲曲劇種較之,它更顯得貧弱蒼白。


許多嚴謹的考慮,在歌仔戲表演中變得無關緊要,這是否意味著進入電視界的歌仔戲,終究已經像電視劇一樣,日益地商業化、商品化,以觀衆的口味做爲製作的標竿,以通俗有力的趣味,得到雙向的滿足,即使回到專業的表演舞台上,亦不能改其「本色」。

舞評要讓舞作與其表演的可能意義可在不同的劇場與國度中釋放,並與不同觀者產生更多的意義交織,而不是讓來自舞評者、編舞者、表演者或記者的某種權威式評價,壓縮意義的生存空間。

西哈諾有個大鼻子,他嗅到了詩歌的美與愛的眞諦。觀衆也帶著靈敏的五官來感覺西哈諾的魅力。而觀衆除了在視覺上了解劇情之外,也會期待在歌聲裡感覺到十七世紀的文化感情。

劇場效果不必然等同於美學效果。更改的如果是標題,影響所及可就不只是語義的表達。台灣藝術學院戲劇系的《亂事家人》,改編英國劇作家考爾德的喜劇《乾草熱》,就是個例子。

崑曲命不該絕,或正是它具有每一種偉大藝術必備的多重性。而做爲舞台表演藝術,多重性指的不單是不同主題、不同風格的劇本,更是各項劇場要件的個別高度發展與互相糾葛。決定崑曲命運的不僅是劇本的文學或社會價値,也是它的音樂、表演形式和演員。

魏明倫以其一貫喚醒女性意識、尊重女性社會角色的關懷與省思,創造出狗娃與水上漂這一對祖孫,其實也是另一場男女議題的爭辯。只不過他將重心從男女關係轉化成爲祖孫情感,更符合傳統苦情戲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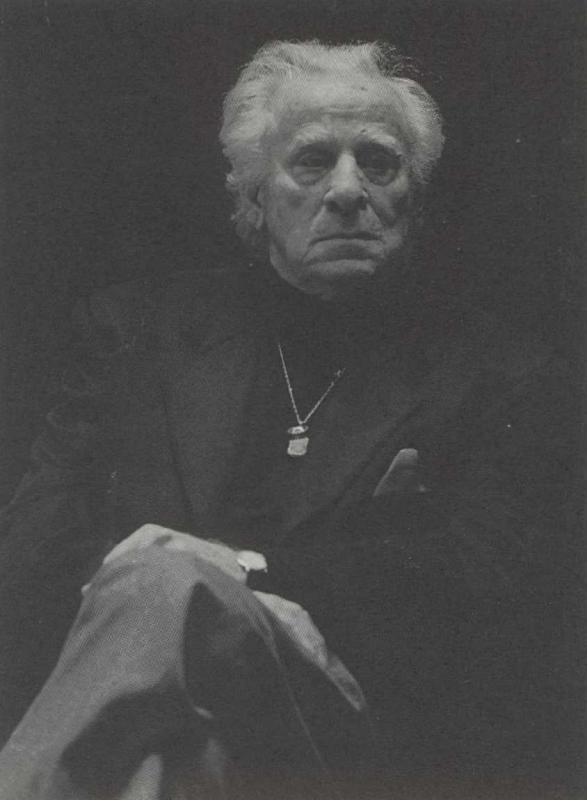
陳宏寛充滿豐富個性的鋼琴彈奏,早已跳脫出一般人所習慣性期待的聲響技巧展現與感官愉快的追求;當他單獨彈奏時,讓人聽到鋼琴家獨特的彈奏個性與非比尋常的藝術特質。

他是一本文法大辭典,一個個音符聽來都對,譜子上一個個連線符號,一個個強弱標記都亦步亦趨忠實於原作,但連起來一聽卻什麼都不是了。現在的他是「廉頗老矣」,他的疲倦是從心底裡透出來的身心俱疲。

今年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根據他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京劇《駱駝祥子》,在年初北京舉辦的「第二屆中國京劇藝術節」上,獲得頭名金奬。一些戲曲界的專家紛紛高度評價此劇是「本世紀京劇現代戲的壓軸之作」。

由香港進念.二十面體策劃,海内外不同領域華人藝術家「同台獻演」的「中國旅程」,已經進入第三年。 演出部分今年請來了北京的孟京輝,上海的張獻,台北的魏瑛娟,澳門的李銳俊,香港本地的陳炳釗和榮念曾。其中半數(張獻、魏瑛娟、榮念曾)爲去年「回鍋」的客人。這種組合,持續交流的意義遠大於「競技」,雖然兩者並不牴觸。

一直以來葛羅托斯基被套以不同的思想主義解讀,不同的文本呈現不同的葛氏說法,以及隨即而來的爭議,「葛羅托斯基」已然成爲一個複合名詞,定義隨著文本而漂浮。大師已故,如歐忍辛斯基語重心長地說:「豎一座紀念碑將是讓他眞正死去的鬧劇」。

導演爲本地示範了前衛活潑的高難度劇場作品,然而也在如此複雜的語言指涉裡,犧牲了觀衆對這齣戲及其原典中淋漓挖掘的人性往復的期待。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