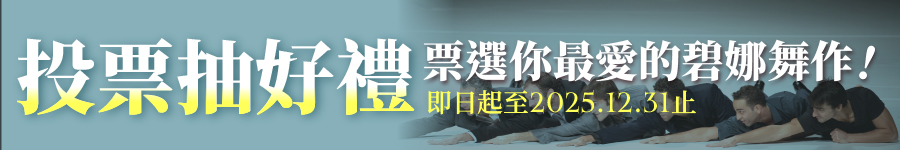王安祈
-
 戲曲
戲曲如何才能「人間情根仔細栽」?
演員表現精采,水準整齊,舞台極富詩意,水墨和窗框,就像這整齣戲,給人餘味不盡。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卸下傳統包袱 注入青春秘方
傳統產業講求改造升級,面臨老觀眾凋零的京劇也得找尋第二春。卸下傳統的包袱,擺脫LKK的印象,國光京劇團為老劇種注入還魂丹,不管在劇目創新,或是行銷手法上,都頻頻向年輕觀眾招手。二十一世紀的京劇,正煥發著青春味。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後宮女子的孤寂與哀愁
《三個人兒兩盞燈》以陳美蘭、朱勝麗和王耀星演出禁錮後宮,三名各懷情事的青春宮女為主軸,交錯對應出寂寞主題,加上多情天子盛鑑,及收到征衣塞外戰士戴立吾和孫元城。男女情愫不說,女人堆裡暗暗流動的曖昧情誼,更是考驗傳統京劇的道德尺度。
-
戲曲 古代呆伯特智慧1─如何不得罪老闆又要說真話
《李世民與魏徵》寫君臣間的愛恨糾纏
有沒有搞錯?怎麼會有人用「戀人」來形容唐太宗和魏徵?不是應該用「千里馬與伯樂」來形容嗎?他們倆又不是同志!不過,在王牌編劇陳亞先的眼裡,他們的君臣關係恰如男女談情,一個欲迎還拒,一個欲去還留,相互愛慕欣賞。於是他把這番男人之間的糾纏加以描寫,並在治國宏願中摻入深層隱私,成為新編京劇《李世民與魏徵》最引人入勝之處。
-
戲曲
休妻羞妻‧休戚與共莫相欺
國立國光劇團以「京劇小劇場」為號召,強調京劇現代化實驗與顛覆精神,由藝術總監王安祈根據傳統京劇《御碑亭》的情節為藍本,新編為《王有道休妻》,在滿場觀眾的期待下登場。 突破行當形象,著墨人物性格描寫 該劇演出形式並未過度偏離京劇表演規範,新編聲腔時而溫婉動人,時而鏗鏘有力,就聽覺而言,依然「京味」十足。表演程式擷取京劇的身段原則,根據情節發展與人物心理重新組合,適度彰顯了京劇傳統身段的美感,但在腳色行當上,則能突破老生、青衣的固定形象而著墨於人物內在性格的描寫。 例如:王有道老生形象的道貌岸然卻身陷男性封建思想的迂腐可笑、孟月華青衣端莊嫻淑且仍保有慾望波動的真情刻畫,御碑亭丑扮但冷靜旁觀地看盡人間風華,都是新編版本具備「嘲弄」的重要現代感表現。而盛鑑、陳美蘭與謝冠生三位年輕演員的表現相當亮眼,適切地切割出生、旦、丑不同的角色形象,都是令人激賞之處。 與傳統版本相較,最大顛覆與實驗之處在於將孟月華的內心掙扎予以形象化,由陳美蘭和朱勝麗兩位演員同台同飾一角,隨著劇情的發展,代表理性禮教的陳美蘭,與代表感性慾望的朱勝麗之間的兩極對比逐漸模糊,在編導相互合作下,企圖將孟月華「精神出軌」的微妙情愫更加立體化。 但是,姑且不論前兩場朱勝麗彷彿現代舞的動作表演,如幽靈般出現在上舞台簾幕後的尷尬突兀,僅就表演本身而言,如此兩人同飾一角的處理,明顯削弱了單一演員千迴百轉心理流動的表演可能性,唱詞和說白雖然保有含蓄美感的想像空間,但是女性主題的「重探」反而失之過白,失去了女性意識控訴的力道與深度,倘若能夠運用王有道與孟月華的夫妻情感基礎作為解套的技巧,當能化解說理過白的迷障。 「御碑亭」擬人扮丑角,輕快且意味深長 另一個與傳統版本不同卻相當成功之處,在於「御碑亭」這座彈指間看盡人間悲歡喜樂的亭子,以擬人化的丑角形象出現在舞台上,對比於孟月華的角色創作包袱,御碑亭顯得活潑輕快且意味深長,時而評論說理,時而嘻笑戲謔,穿梭在戲劇情境的現實與想像之間。其作為旁觀者的身分,代表著創作者對戲劇人物的疼惜,更替代了觀眾對劇中角色投注了關懷,若說實驗,御碑亭顯然更加收穫了實驗的成果;甚至,御碑亭與孟月華若有似無的對話,實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特別企畫(二) Feature台派京劇這樣走出來
不同於中國大陸京劇的流派根柢深厚 台灣的京劇發展出了獨特的表演美學 一代代的演員, 植基於角色情感,超越行當派別,揮灑出明星丰采 日前,有「戲包袱」之稱的京劇界前輩馬元亮先生辭世了。 身兼演員、主排、教師身分的他, 在京劇扎根台灣的過程中, 作育許多英才,也間接打造了台灣京劇的獨特路途。 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特以專文 從馬元亮先生談起,探討「台派京劇」的成形, 也向半世紀前篳路藍縷深耕厚植的京劇前輩藝術家致敬。 另一方面 年輕的京劇演員們,也藉著近來「武戲」的製作 重新喚起觀眾的熱情,綻放出明星的魅力。 這是否是台灣京劇發展的新契機? 我們也藉此機會, 探討這個風潮下可能打造的未來遠景
-
戲曲
小戲好風景,老酒漾新香
有沒有搞錯?勞勃瑞福與黛咪摩爾所演的電影「桃色交易」,百萬美金一夜情的故事原型,原來京劇二百年前傳下來的劇目〈借老婆〉早就演過了。 「三小系列」召喚年輕觀眾 位於台北木柵區國光劇校內的國光劇場,最近推出由年輕演員挑樑的「三小系列」,掌握輕、薄、短、小的現代行銷思維,把傳統戲裡的前衛因子翻出來,讓「小劇幅、小玩笑、小人物」的優秀傳統劇目也有出頭天。不信年輕人喚不進戲曲舞台下。 「三小系列」的構想來自藝術總監王安祈,「年紀越長,越喜歡足以表現京劇多面向和人生智慧的生活化小戲。」王安祈說。於是,她將它們總括在「京劇小人物」的名號之下,並結合電影和劇場對年輕人的魅力,借力使力,聯合拉抬,「三小系列」的第一「小」是三月底打頭陣的《王有道休妻》,第二「小」是《荷珠配》,第三「小」則是《借老婆》。 《王有道休妻》去年底在西門町紅樓的第一屆「國際讀劇節」中獲熱烈回響;八○年代台灣現代劇場先驅作品《荷珠新配》,骨子裡的 DNA就來自《荷珠配》;看不過好萊塢電影《桃色交易》獨領風騷,《借老婆》一戲也要一爭長短。依此構想,《荷》演出前,將由《荷珠新配》編劇金士傑聯合國光導演李小平,示範京劇素材在現代劇場被重新創作的過程;《借》劇演出前,則由綠光劇團總監李立亨擔任導讀人。 小人物狂想,也是生存伎倆 小丫頭荷珠麻雀也想變鳳凰的故事,一窮二白的張古董為騙錢混飯,想出把老婆借給拜把兄弟李成龍(還煞有其事地叮嚀:不准過夜)的招數,對這類的小人物狂想曲,「以荒唐的手法解決荒唐事件」的安排,王安祈認為,人物「既有幾分得意,也有幾許無奈」。 例如《荷》劇中僕人趙旺對荷珠的冒名頂替,本就沒想拆穿,只想藉機佔點口頭便宜,自己開心,也逗樂觀眾;《借》劇中,張古董為了老婆後來假戲真做,一狀告到衙門去,縣官判他敗訴,張古董正拉扯不休時,卻才發現縣官竟是驢夫,(劇本指定這兩個角色由同一人兼代),原來張古董借妻時向他租了驢子沒還,這種結局收束法,頗有「一報還一報」的意味。 王安祈表示,中國人的戲劇觀是「不管是演戲還是看戲,都是討個皆大歡喜」。當這些素材被當代劇作家重新處理時,文化差異和不同的創作旨趣便明顯地突顯出來。編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新生代京劇演員「硬」起來,打出全武行!
國光劇團一齣《嘉興府》打出武打新秀的知名度,京劇導演李小平認為好作品可以建立品牌,將年輕的優秀武戲演員推向主角位子的時機已趨成熟,他鼓勵他們「把握眼前的階段,讓生命不要留白」。
-
 古意
古意巧描君臣間的「戀人」情致
《李》劇是一部從「小」處著眼的抒情小品,氛圍淡雅而空靈,唐太宗和魏徵的心靈深處,一個是欲迎還拒、欲拒還迎,一個是欲去還留、欲留還去,君臣兩人對彼此的欣賞愛慕「竟如此相似於男女戀愛相交」。
-
戲曲
商人本事,文人本色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長生殿》裡的唐明皇與楊貴妃的千古愛情,由人間而綿延至天上。一千多年前的帝妃之愛,因為崑劇之傳唱,容顏不退。在兩岸攜手下,二月十七日,《長生殿》將首度全本登台。 這個製作由一生浸淫崑曲的江蘇省崑劇團創辦人顧篤璜擔任編導,設計家葉錦添挑起舞台與服裝的美感大任。而結合兩岸的戲曲精英與設計大家的幕後推手,則是因為研究明清書畫,而愛上明代崑劇的企業家陳啟德。 繼承家族營建事業且發揚光大的陳啟德,商人本事自不在話下;但現在,風華依然絕美但生命垂垂老矣的崑劇,成為佔據他每天三分之一時間的新「事業」,他說:「如此燦爛典婉的藝術結晶,是明清文人共同參與的結果。時代能不能留得下它,我沒有答案,但我想為傳統戲曲做一些事。」
-
專輯(一)
戲曲人作主,小劇場有大用
由戲曲人主導、在小劇場空間中進行的「小劇場戲曲」,在台灣的確是少見。《王有道休妻》在紅樓劇場引起年輕觀眾的熱烈回響,為這種創作模式博得了好頭采,未來,尚待每個劇種、劇團和創作者以各種企圖心的實驗去賦予小劇場戲曲在台灣的現時內涵。
-
戲曲
排戲目提兵調將,眾演員博命上場
國光以往經常支援台北新劇團演出,但都是邊配武行,綠葉的層次。今番出動主將,短兵相見,讓魏海敏與李寶春演「對兒戲」,讓唐文華和李寶春在同一齣戲中先後飾同一角色,這卻是破天荒創舉。加上另幾齣自擔綱、卻明顯有較勁意味的大戲,對觀眾來說,都有極大的欣賞誘因。看來兩位舵手的精心「提調」,已為這次「既競爭又合作」的「分進合擊」,奠下可樂觀的基礎。
-
 最PAR!
最PAR!劇之本不在,戲根著何土?
台灣從未認真培育過演員之外的戲曲人才,環環相扣的惡因,導致我們現在正在吞忍本土劇作成熟度不夠的惡果;劇團製演大陸劇本遭質詰,答以:「上哪兒找好的本土劇本呢?」聽起來也是理直氣壯。對岸又添了個層級很高的「精品工程」,劇團若沒有認知到本土劇作和劇種乃唇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大陸編劇台灣製演」的模式只怕更要演變為台灣戲曲的常態了。
-
 最PAR!
最PAR!祈—京劇不悶,國光發光 專訪國光藝術總監王安祈
被京劇界尊為亦師亦友的王安祈剛接任國立國光劇團藝術總監一職,本刊特地專訪她,請她暢述未來領團的理念與方向;在文化官僚主導的行政系統下,學者出身的王安祈能否落實理想,帶領國光開創出新局面,需要我們持續的關心和檢驗。
-
戲曲
濃鹽赤醬與蛤蜊之味
而在編劇環扣緊密、發展有致的劇情發展之中,在導演濃鹽赤醬的表現手法底下,演員應該要如何定位自己?或導演應該要如何定位演員?演員如果能堅實地在唱唸做打揚袂轉身顧盼呈現人物,則或許「能夠」被看見,否則,可能就是劇場上共同呈現的諸多元素之一,在導演的整體處理下,可能可以讓觀衆因為看戲而滿足,但卻不一定可以讓觀衆是因為看戲曲而滿足。
-
戲曲
戲夢,循環在今古遐想的新思維
《閻羅夢》之所以在前人的架構中另闢蹊徑,表現在劇本裡的,其一是項羽化身關羽、關羽轉世李煜、李煜再請託生項羽的情節想像;其二為夢醒之前衆鬼魂對司馬貌所唱的書生自況;其三也是最令人激賞的,則是司馬妻的人物塑造了。
-
深度藝談
翻攪一筆輪迴的糊塗帳
在親睹《閻羅夢》所謂「新舊意象並陳,古今時空疊映」的舞台表演之前,國光劇團特地邀請文化界各領域的菁英,根據《閻》劇文本,為觀衆深掘當中多層次的文化議題,以及所彰顯的京劇現代化的可能方向。
-
研討會
差異可觀.猶是本來面目
此次的論文,台灣學者較講究田野調查、直接證據,大陸學者多有寶貴的個人實務經驗。台灣研究領域和成果的躍升,令人欣慰;雖然兩岸學者對彼此資訊的掌握度、學術訓練明顯不同,卻不乏精闢之論。整體看來,這第四次的交流,已更充分而全面地展現了彼此的歌仔戲隊伍和研究狀況,影響更擴大。
-
研討會
戲劇研究回歸原生脈絡
對關心戲劇的人士來說,研究素材俯拾皆是,試著放下身段做田野,將是改變對既定戲劇史看法的開始;尤有甚者,還有必要敞開心胸,多觀看別的領域,嘗試把戲劇放在儀式或社會環境中討論,讓戲劇研究回歸原生脈絡。
-
劇場對談
從〈蘆林〉到〈癡夢〉的表演心路歷程
素有「張三夢」美譽的崑曲名伶張繼靑,去年隨同江蘇崑劇院二度來台,演出包括〈驚夢〉、〈尋夢〉(《牡丹亭》)、〈癡夢〉(《爛柯山》)和〈蘆林〉(《躍鲤記》)等著名戲碼。兼具傳統戲與現代戲表演體驗的張繼靑,是如何創造並豐富了「崔氏」、「龐氏」等膾炎人口的崑曲角色?透過這場張繼靑與國內戲曲學者王安祈的對談,不但反映出崑曲表演者琢磨角色層次的細膩與深刻,也呈現了崑曲劇種的獨特藝術之美與人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