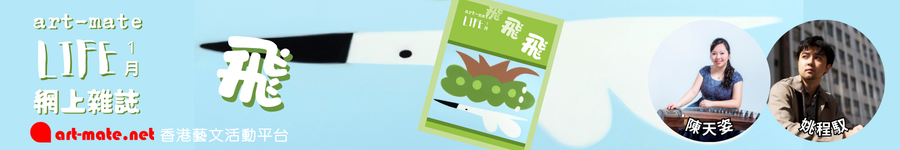身为肢障者,人称「阿忠」的郑志忠,独特的身体姿态让他如同一个能够操纵自己这个偶身的傀儡师,而在这个看似正常,但所有人的眼光却都围绕在他身上的怪奇世界里,他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生活就是剧场。而他的剧场也来自生活,沉潜多年之后,柳春春剧社应邀再现该团旧作《美丽》,这个被剧场人鸿鸿视为「残酷剧场」的作品,对阿忠来说,其实「残酷」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现代剧场大补帖
4/29~30 19:30 4/30 14:30
台北 牯岭街小剧场
INFO 02-23893625
当你走在街上,或是进到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空间。看见一个拄著拐杖的小儿麻痺患者,你的目光总是会停在他身上。这种感觉就像看著一个穿著清凉,身材如魔鬼的超级正妹走进来一样。那样不可忽视地,不敢让她发现地偷偷看著她。只不过,这超级正妹胸口的那一条事业线,化成坚挺的两根拐杖;白皙且穿著红色高跟鞋的一双诱人大腿,化成两根因重心而自然垂下且晃荡的细脚。
对我们来说,那是多么地特别——别于常人的步行节奏,上下半身完全断裂的违和感,双脚细得简直就像个只有下半身的悬丝傀儡;既不像人,又不像偶,既是人也是偶,整个就像一个能够操纵自己这个偶身的傀儡师。
郑志忠,剧场人都叫他阿忠,有些人也叫他主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傀儡师。在这个看似正常,但所有人的眼光却都围绕在他身上的怪奇世界里,而这怪奇世界若说是舞台一点也不过分。只要遇见人,就像彼得.布鲁克(Peter Blook)说的,这舞台立刻搭起,上演傀儡师的剧码。每天都这样上演著,生活著。
田启元的影响
曾是「临界点剧象录」团员的阿忠,提到该团编导、已故的小剧场导演田启元,他说,田启元是爱滋病带原者,而存在他这位小儿痲痺患者身上也有一种相通的境况,因此,相较于其他临界点团员,就更可以理解,当你因为一种疾病,而受到他人歧视或者是差别对待的时候,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在作品里面,或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么样反应,又或是如何说出来对这个社会政治基本的态度以及看法。
阿忠认为,如果田启元对身旁周遭的团员有所影响,比较会是在他过世之后的那段时间;就好像一棵树,以前还是一株小树苗,根本长不出果实,到现在,不但已经长出果实,而且往后延续了。阿忠强调,田启元就像一棵超大的大树一样,如果有一棵大树在那里帮你挡风遮雨,你要选择自己长成大树超越他呢?还是就直接在他的庇荫之下?不同的是,这颗树已经倒了,要不要继续长大,每个团员的选择都不一样。
然而,田启元对阿忠后续的影响,并不是阿忠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导演方法论或技巧,比较多的反而是怎样作为一个人,以及接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差异性,去更理解别人。阿忠认为,这是做剧场更为重要的事情——人。
风格化的柳春春剧社
阿忠在田启元过世之后,成立了「柳春春剧社」。这个由田启元命名的剧团,曾经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是在二○○四年之后,便开始进行内部团练及实践生活,没有再推新作品。
同是剧场人的王墨林说,他看不到柳春春的任何一个成就,但他强调,成就并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潜行;整个来看,他认为柳春春是非常风格化的,然而,这个风格化不是在美学上的,而是属于剧团本身的风格化,例如从最早的不申请补助,所呈现的压抑与悲壮。但王墨林也提到,不同于常被放在体制外非主流脉络来谈的海笔子帐篷剧场,柳春春很少被认为是一个体制外、非主流团体,他认为,若要下一个结论的话,柳春春还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然而这是一种修行。
牯岭街小剧场馆长姚立群就很直接地认为,阿忠没有推作品,人们把柳春春忘了就是天经地义的;他认为剧团还是要做戏,不做戏,就什么都没有。
然而,阿忠很了解一个剧团是因为作品才存在的,就算讲得再多、想得再多,都还是要用作品来印证。他于二○○三、○四年之间,在短时间的大量挤压之下,剧团成员被逼著往前走,整个剧团产生了一种因为活动、作品的关系,看起来是成长了、或是膨胀的外相。可是就驻团编导的身分来看,在这样模仿一般演出团体的操作过程下来,他发现里面是空的。
因此,阿忠重新省视自己,开始团练生活、生活团练,简单地把一件事情做到。这几年的团练当中,每次团练他们都会画图,并且一直不断地在讨论,柳春春应该会是怎么样的经营方式。而且愈到团员们已经不是学生的状态之后,他们反而可以更理解,柳春春当时停下来,以及后来做的团练,每个月固定交团费,及不是固定每年一定要有作品的运作方式,都变成可以理解并且接受的。
沉潜多年后再现《美丽》
在这样多年的沉潜后,却在今年被剧场人鸿鸿挖了出来,在「现代剧场大补帖」中重现柳春春首演于二○○○年的《美丽》,这个被鸿鸿认为符合残酷剧场要件的一个演出。
只是站在创作者角度的阿忠来看,人们也许会因为「残酷剧场」这新鲜又恐怖的语句而感到突兀,进而更想接触它。就像人们看到了正妹、残障一样地突兀。但是,他却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人们在叙述亚陶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做出他要的残酷剧场,那么《美丽》到底符不符合「残酷剧场」呢?
对阿忠来说,那些都是存在日常当中,把生命本来就有的东西拿出来,一点也不突兀,是再平常也不过的。只是,当我们亲眼见到时,才会惊吓于,原来这些残酷早已深植在日常的行为里面而不自知。
只是之后,阿忠还是一如往常,每天上演著傀儡师的剧码。无止无尽,直到彼岸。
现代剧场大补帖 三样革命生猛再现
文字 廖俊逞
想要了解现代剧场如何演变,不用上补习班,不用猛啃教科书,走进剧场,一目了然!资深剧场导演鸿鸿策划「现代剧场大补帖」,邀集港台小剧场的前辈后浪,将廿世纪的三次剧场革命,在廿一世纪的剧场里再现其生猛精神。
一九三二年,亚陶(Antonin Artaud,1896-1948)的《残酷剧场宣言》,开启了现代剧场与文本间的爱恨情仇,「残酷剧场」以意象式的表演语汇,仪式般的纯粹力量,达到意识清醒的诗意。八○年代台湾小剧场运动重要人物、「临界点剧象录」编导田启元的嫡传创作者阿忠,在作品《美丽》中,以非语言的缓慢凌迟,彻底实践亚陶「剥露日常生活残酷性」的剧场美学。一九五○年,旅居巴黎的罗马尼亚裔作家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1909-1994)从英文教材中得到启发,领悟了世界的真理原来如此滑稽荒谬,于是写下「荒谬剧场」代表作《秃头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半个世纪后重新搬演,时空转移到当代台北,看看究竟是剧场还是人生荒谬?一九六六年,首演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冒犯观众》Offending the Audience,横跨小说和剧场的实验先锋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以直接对观众发言乃至辱骂的方式,泯消了戏剧扮演,泯消了台上台下的界线,也改写了剧场史。观众成了演出主角,不断被分析和嘲笑,这出戏却变成大众趋之若鹜的热门事件。这次,五位新锐导演要以更疯狂的手法,还原《冒犯观众》现场的骚动与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