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時是針對音樂、有時是劇中人物,有時表現方式,在眾多可能的改變中,他至多只會擇兩個關鍵點來討論。太歲頭上雖可「動土」,但不能動大土!什麼是關鍵?什麼是可行的關鍵?是提出一個方向?還是有一定要改變的點,羅勃總能分得清楚,作品也往往在他的「提點」下,將製作人與創作者的距離拉近,也就擔保未來與觀眾的距離更近了一些。

追求「不可勝數的多與新」之下,有可能只是「無可承受的少與輕」嗎?就像拙政園的景色,只能欣賞卻無法購買,這不只是如桑德爾所說的「錢買不到的東西」,而是「不能用錢去購買的東西」。搞不好這種看待文化與藝術的方式,就像是一隻蜘蛛蟹,忙著把海藻碎屑黏在身上、四處爬行,除非你硬掰說它也有靈魂悟性,否則少了心領神會、偶拾的美感,其間又有多少差別?

歐斯特麥耶的《義大利之夜》在我看來很有意思的,是四個女性角色所反映出的一個共通點:男性和他們想像中的自己,與女性在跟他們相處之後所認識的他,可以不是同一人。而「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不止存在於兩性之間,也是政治常常面對的無解,甚至虛偽所在。

持之以恆,恐怕是紀律中我們最需要努力的一項。讓自己有堅持的動機,持續探討的不是答案,而是因時因地因人變動可以產生的各種可能解決方案。將好奇心、好勝心、競爭力轉化成積極態度,延續地、不推諉地,有需要就做,起而行,做對、做好為目標,將所說的實踐與所做的一致!

每年的城市文化會議都是由各城市依主題報告近況與發展,大家除了要提供最新的資料外,也難免會各有心機地運用在地特色來「宣揚國威」,短兵相交的較勁有時不知不覺會讓彼此的關係有些緊張,但南方大師總能以一個漂亮的總結將會議重新定調。他「要緊張,又不要太緊張」的態度,多年來成為會議的核心精神,讓大家在面對新議題及挑戰時找到動力及方法,也能夠體認「掌握」會議的結論是在開幕的「面子」後,更重要的「裡子」。

K-POP其實又有多少韓國成分?只是唱歌跳舞的剛好都以韓國人或東方面孔為主,歌曲是從全球徵選來的,以強力訓練、訓練、製作與行銷,為韓國塗抹上時尚魅力。在去年公布的百大品牌中,韓國有三個品牌擠入,台灣沒有半個;把「內銷」概念轉成「外銷」,把「鄉土」變成藝術家的責任與使命,希望能代表台灣出國巡演,以達成藝術的「外交使命」,但這樣是不會有產業的!


情懷背後,是自己不需改變。唱一千首失戀歌,心也不是為了改變,只是要被安慰被認同。但情感背後,是下定改變的決心,並且身體力行,相信總有一首歌不是換了歌名不換精神,換了唱詞但不換心態。而唯有它才明白我所有的經歷,也唯有把它寫出來才能令人知道,我是怎樣一首歌。

我可能沒有遠大的志願,但我知道我不要什麼。不是因為單單的不喜歡而不要,而是因為它不能讓我專注在自我的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跟自己相處好的人,價值觀不被物慾而牽引,也就會做對的事,做對的選擇。

面對這一連串的辯論,我其實還想插話:「我們每一場活動都會事後用照片做人數確認?參與人數較少的活動可能可以計算出來,幾百人參加的能算出來嗎?」我們的「研究」方式要如何可以精準又省力?但這個項目有必要那麼錙銖必計嗎

「藝術」的最高目標是引領我們從滾滾紅塵抬起視線,仰望繁碩的億萬星空,俯察人世悲歡離合,驚鴻一瞥宇宙有無之妙;陳義過高?那就先多花點心思好好演出、復活、講究一下我們身邊久故、新古作曲家們的曲子,唯有這些才可能會是我們的,也終將會是我們所共同所有的。

觀眾歡迎「議題電影」,有可能是基於在這多事的時代,看過這些電影後,會令人覺得對某些問題的無力感,得到了力量。當多數人指望藉著認同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複雜性其實還是沒有被正視。是以認同的需求愈大,「議題」的問題性只會更被外在化,代表它跟個人的直接關係(例如思考),可能更疏離。

勇敢的領導,跨越階級(師生、資歷、年齡)的平等溝通是極其重要的第一步。以專業對專業、就事論事。將專案制度以及重點期程,做一個完整的說明與對團隊的要求配合期許。針對不熟悉制度的參與者,給予時間理解與反應。這絕不能受限於「在當下」的靜默。


除了不斷想辦法精進演出前後的「說」,今年我們還有個特別的機會,把舞作從頭到尾以口述影像方式「說」給視障者聽,準備素材的過程相當不易,但結果是意外的「甜美」。口述老師將看到的畫面,透過耳機以好聽又適當的速度娓娓道來,不僅聽障生覺得「非常豐富」、「看得很開心!」,連一起前來的明眼人,也有不少表示受惠良多,確實因此看懂了更多的細節!

台北市並不是沒有表演音樂的地方,而是缺乏一個有別於國家音樂廳歐式濃郁渾厚、咖啡色彩,偏日式純淨的「新」音樂廳;台北更需要一個「音樂藝術之家」,咖啡廳典雅溫馨的氛圍讓愛樂者可以聚首聊天、享受難得的悠閒;大廳更不必氣派地鋪滿白色大理石像是偉人陵寢;各種動線、管制區的設計必須以降低管理人力需求作為基本準則;缺乏鄰街門面就絕對需要建築師的天才靈感,將之轉化成令人讚嘆驚豔的地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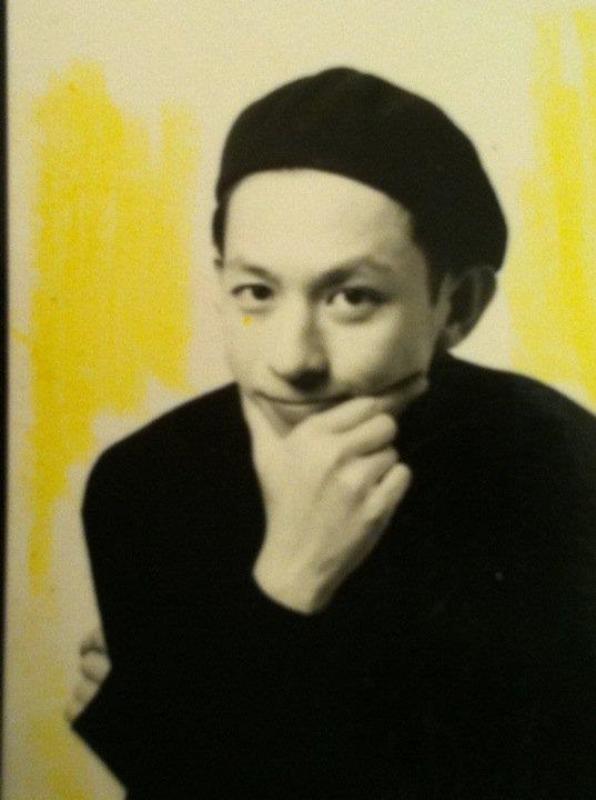
《亂世佳人》的主角被詬病的原因,一是以愛之名,不理他人觀感。二是以「明天又是另外一天」為座右銘,什麼事都好,先做了再說,天掉下來當它是被子拿來蓋。 自我中心一向被認為是一個人自私的禍源。不管今天追求明天更是好高鶩遠的惡習。但放在創作過程來看,擁有自我但又無畏別人的評斷,那樣的分享可以很無私。敢去提出未知而不是緊緊握著已知,也可以讓人看到明天。

起始於對創作主旨的建立及敦促,到當創作主旨在過程中,產生偏頗時的提醒、建議,有時甚至是看守原主旨的必要動力。但當若創作主旨的變動之必要,影響製作最大利益時,原製作架構的調節與支配策略的檢視與更新布局,更是製作管理者必須要具備的活用、應變、彈性的承辦能力。

今年,我們更大的挑戰則是在新竹美學館的支持下,舉辦一場給「視障者」的專場演出。演出進行時,視障觀眾會帶上單耳的耳機,一邊聆聽著口述影像老師的敘述,一邊聽到音樂、想像舞蹈。我們沒有任何先備經驗,原本想得很單純,以為只要提供演出劇本,讓影像口述老師們來看看彩排,他們就可以把看到的內容說給學生聽了吧!沒想到想到這才是一連串費心費力溝通的開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終於要落成啟用了,從二○○三年我還在高市交擔任團長時,當時行政院游院長與文建會陳主委親自來到高雄,在公園的榕樹下宣布興建計畫,到現在已過了十五個年頭,預算也從當初的六十六億變成現在的一百零七億,在這喜慶的時刻,的確有點百感交集。


幻覺,即是把想像看成了實體。例如,只為展示某一部分而呈現的「自己」,會被誤以為那就是「我」的觀點和感受。最常見者,是經過修圖的照片看多了,便把它植入腦海中,覺得真人看上去就是一樣。Selfie(自拍)大受推崇,或手機必須擁有鏡頭,是切合這時代需求的例證之一:我們不相信鏡子的那人是自己,我們選擇了把鏡頭當作鏡子,由於它才是可以由自己來決定「我」將怎樣被看見的「眼睛」。

在此呼籲,台灣的表演藝術界,請正視對表演藝術應有的專業尊重!一齣製作該有的分工,正確的職責,與對應預算分配,是製作人起始企劃時就應該做對的! 在排練時,舞監必須要發揮眼觀、手記、耳聽得一心多用才能!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創意的想法不能只是說出來,還要以不同的行動去落實!有時我們會先做工作坊,增加前置的心理及身體準備;有時則是要辦個讀書會、討論分享,讓舞者們跟上編舞家的內心世界。「攻人要攻心」從來就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何況每一代的舞者、每次合作的創作者都不相同,所以我也只能在「挑戰」中緩步累積經驗。

我真心地認為,還有什麼比音樂劇這個融合戲劇、歌唱、說白、肢體、美術的項目,更能夠讓孩子們體會美感的多面性與整體性?並且為台灣音樂劇未來的創作、展演、欣賞、推廣奠下堅實根基,但這需要表演藝術與教育體系的共識,讓它成為學校課程、社團活動項目,進而成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團體項目,形成一個深遠的政策,提升下一代對於表演藝術與文化創意的投入與欣賞。

藝術作品如果不是直接陳述答案,就會被認為曲高和寡。不過,它的可貴性,亦可以在於觀者在觀看時,從外在世界所看見的現象,找到回歸內在的路徑。也就是說,別人的病反射出自己的病,自己也從旁觀變成介入,介入變成當事人,那些別人的問題亦因此成了自己的自覺,那麼,更多有關自己的問題的誕生,實在就是一人兼飾醫生和病者。

台灣的文化機構常年不斷狹義地,專注在推動年輕的創作力。現在也因國家條件堪憂,所以積極推動國際共製。但國內面對製作的成熟態度是值得質疑的。是目前文化機構所提供的機會以量為主,並未有質的看守。顯現出來的,是公機關年度績效數據的亮眼。而實質上的切實成績,真正作品製作面的檢討往往被輕視。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