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光劇團今(2025)年3月「春分」4場傳統京劇,好幾齣都曾遭遇意識形態強迫改編的命運,《鎖麟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與《奇雙會》都有自己的「故事」。 《鎖麟囊》演富家千金出嫁時春秋亭避雨,見另一乘花轎殘破,心中不忍,將鎖麟囊贈予哭泣的貧窮新娘。劇情溫馨感人,唱腔風靡大眾,誰知1950年代竟遭禁演!為什麼呢?罪名很多,不只是善有善報封建迷信,更嚴重的指控是:階級本該對立鬥爭,此劇竟然貧富和融,向地主報恩,分明反動思想,怎能再登舞台? 程硯秋心急如焚,這是他最受歡迎最賣錢的戲,不演損失可大了。一身傲骨的程硯秋只好改編,保留春秋亭精采唱腔,窮新娘接受餽贈,卻掏出所有珠寶,只留空囊!只收紅包不收鈔票的概念,今天看來十分可笑,但我不敢想當時的程硯秋有多委屈。更屈辱的是,「空囊新版」演出數場,結果仍是禁演,直到程去世都未能翻身。而這只演幾場的空囊版竟還留下完整錄音,被配成錄像,永久流傳!(註1) 「改革開放」後,《鎖麟囊》重登舞台,愈唱愈紅,至今益盛,當然演的都是原版,空囊版銷聲匿跡,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卻不同,目前兩岸演的都是意識形態改編版。 京劇劇情源自晚明短篇小說,篇名就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書生莫稽凍餓昏倒,金玉奴好心相救,金父將女兒許配,父女沿街乞討送莫稽進京趕考。沒想到莫稽一高中就長了官威,嫌棄乞丐父女低賤,赴任途中竟將金玉奴推入江心。到任後長官欲將女兒許配,莫稽歡喜入洞房,不料新娘竟是金玉奴。原來金玉奴落水未死,蒙大官搭救,收為義女。如果小說寫到洞房棒打結束,讀者一定大快人心,但結局竟是二人和好,重入洞房,據此編成的京劇也是如此,棒打痛斥之後又結婚姻。我小時候看台灣的京劇團也都是團圓,直到1959年,荀慧生才改結局為不團圓,法辦莫稽。 古代女性忍氣吞聲,南戲《張協狀元》的貧女(對,她就叫貧女),救了張協,張協得中狀元後拔劍殺妻,而最後,貧女還是再度嫁給張協,永嘉崑新版還由參透世態人情的老人說出:「我有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再嫁給他。」(註2)古代女性的無奈有其時代背景,一旦演成傳統,若要翻改需要勇氣。荀慧生為何有此大動作?原來是當時服膺「戲曲改革」國家政策的「揭發封建醜陋」,理直氣壯

我的老師會以啟發式教育,鉅細靡遺點出我的不足,給出方向,提供方案,掰開揉碎把戲情戲理清晰闡述,直到我理解,我實踐,我到位。如今輪到我身兼業師了,回望老師們對待我的教育方式,深刻體會到與其說名師出高徒,不如說是明師出高徒更為貼切。

大伯公被我們砍半了。 在這篇文章刊出時間點,我們應該已經人在美國,正在與紐約觀眾直球對決,而台灣的觀眾也應該在1月的遊心劇場看過全新的外百老匯版本。我們預期大家會有些不一樣的感受,卻還不知道這些差異是好是壞。無論如何,這些回饋都將成為我們面對國際舞台的珍貴經驗。 在文化轉譯的過程中,有很多選擇要做,再不忍心也要下手。我們在和美國製作團隊一次一次的討論中,重新釐清了劇本還可能讓人迷糊的地方,特別是當遇到需要解釋的文化橋段,若一次、兩次無法說明清楚,那我們就會開始思考可能那是一道壁壘。不管是大家族裡的人物紐帶關係,甚至「靈魂過橋」對我們來說這麼簡單一個概念,可能都會讓國外觀眾產生更多與情節無關的疑問。 來自百老匯製作人丁墾有很清晰的訴求:「故事情節如果讓觀眾停下來思考為什麼,背後更大的隱憂是出戲。」 每一次的開會,都會感受到他並非在挑戰創作者的創作意圖或世界觀,而是將自己放在最直接的觀眾視角、提出一道又一道的各種疑問「周文王和彭祖」這個符號有必要嗎,有沒有其他說法?這段卡拉OK的戲,要交代什麼?台灣的鬼怕不怕日光,美國的鬼會在意這個嗎?角色口中的「時辰到了」又是指什麼時辰? 討論到大伯公這個角色,非鬼非人的彌留狀態,和已經成鬼的角色產生了不同狀態的疊加,再加上這次需要有個英文說書人來協助串接劇情,原本大伯公在一旁說書講古的功能也會被取代,因此幾經討論,最後忍痛降低了這個重要角色的台詞量,也希望這樣的決定能更幫助我們更聚焦在女主角與父親的關係上。 我看著下半場開頭的劇本,宋國珍、宋家姊妹和大伯公在半夜惡闖街里的一段華麗冒險,歌隊精采的演出搭配著華麗的詞曲:「獻紙來你也燒錢去呀,獻紙燒錢是要買路去喔!」突然莞爾一笑,真的是燒錢買路!當初寫出這段精采歌曲就已十分銷神,但就因為這樣一個決定,可能即將會面臨不小的調整,除了感謝創作夥伴,也好在我們都依然為了創作這件事而感動不已。 我只願這樣的開發環境和溝通方式有一天在台灣也能成為日常:一位經驗豐富的製作人,敏銳地從觀眾角度發現創作中的盲點,準確地提出挑戰,但卻不刻意指引方向,給予創作者最大限度的自由,讓他們在創作中裡恣意揮灑,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作品。並且投資方與團隊都能有共識將作品打造

裂縫是一道界限,光芒穿越其間,記憶與未來的交錯結構。每一處破碎,都是同時存在與不存在的界門。 風穿過老樹,葉片盤旋落地,留下無聲的痕跡。一雙手拾起地上的玻璃碎片,那些碎片反射著殘存的光芒。身體的彎曲像一條流動的河,與裂縫交織,試圖將時間拉直。每一個動作改變空間的輪廓,這片空間隨呼吸起伏,如同無邊的織布機。 [ □ = ┼ + ]:眼睛是感知的窗口,視覺的清晰度與對連結的渴望交匯,成為理解的起點。 [ ∆ = ⋄ ∿ ]:裂縫是一種過渡,⋄ 象徵破碎,∿ 象徵流動,它們共同構成變化的場域。 手指掠過碎片,光線彈射成弧,旋轉後消散,殘留靜止的餘波。每一道光芒指向不同的過去,試圖拼接時間的圓環,卻始終無法閉合。眼睛捕捉的不僅是光線的輝映,還有那些被折射後的記憶,它們在裂縫中迴旋,重組成未曾存在的形態,像在未完成的軌道中尋求終點。 老樹下,裂縫的光分割世界,形成一個重力扭曲的焦點,試圖修補被遺忘的記憶。空間開始旋轉,像一條被時間撕裂的布料,在動態中尋找新的平衡。 指尖劃過光影,碎片映射殘存的記憶,交錯著未解的謎團。 將最後一片玻璃嵌入拼圖時,世界凝滯了一瞬間。光芒從拼圖中心爆發,撕裂了時間的帷幕。土地隨光影顫動,湖面浮現,映射無窮的變化。 [ ╋ = + ║ ]:手臂,行動與互動的工具,壓抑的符號與支撐的力量交匯,開啟未知的方向。 [ ✧ = ◇ ]:湖面映照的可能性, 為無限的延展,◇ 為重構的框架。 湖面上,破碎的記憶漂浮,被時間遺棄的碎影,在靜止與流動間懸置。手臂觸及湖水,振動擴散,記憶分裂又聚合,一張無邊的光譜無聲地編寫著一個不屬於此世的敘事。 天空的光芒暴漲,地平線裂開成為無盡的閃爍。湖面不斷翻湧,吞噬影像又重新排列,無法解讀的秩序,腳下的大地如同巨大的織布機,光與影在它上面織成一幅無邊的圖紋。 語言是時間的疤痕,切割空間的連續,在裂縫中迴盪。 溪谷無聲延展

我們處在這個空間當中,故意或是不小心,常會交替扮演生命的啟動者或是毀滅者;而拍打著從高處落下的文字「雨、風、火、虹」來召喚出各種自然現象,又像是掌控了操縱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有時停下腳步,放眼看著各種影像在他人不經意的行動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都讓這個觀展過程充滿了未知數與獨屬於自己的特別體驗。

前次文章講到監製下令廠房停止拍攝,把我召喚到廠房外,同時,劉紹銘老師亦靜靜地飄出來,跟在我們附近假裝抽菸。可能他見我身型高大,監製身型矮小,又擔心我性格衝動,不知會發生什麼意外吧。 一開始我已心知不妙,當年,監製停止拍攝,召喚演員談話是嚴重的事情,我們稱之為「照肺」,我不斷告訴自己一定要冷靜。 到了門外,監製便像機槍發射一樣連珠砲發,我完全沒有插嘴的餘地。可能我早有心理準備,或是擁有某種性格特質,平常遇到小事情會情緒激動,一但發生嚴重事情,便出奇地冷靜。我輕輕地靠在門邊,看著監製青筋暴現,但忽然有種神遊物外的感覺,像有另外一個我,觀察著事情的發生。原來,這是演員的本能,每個演員都應該有的第3隻眼,戲劇術語叫作「超我」,不斷監察著自己的行為和情緒,特別在情緒激動或遇上異常事件的時候,這超我便把所有狀態記錄下來,像畫家的掃描一樣,留待日後作為創作的素材。 看著他頸部跳動的青筋血管,嘴巴一張一合,我又偶爾瞄一眼明仔(劉老師喜歡别人叫他明仔),看他在我們左近不太自在地來回遊走,裝作若無其事,然後我又把注意力拉回監製身上,這時他大概已經一口氣講了5分鐘,其實在這段時段中我真的沒有留意他在說什麼,只是斷續地聽進兩三個字:我早跟你說過我看了片不可以繼續這樣演呵呵 老實說,我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麽激動,臉上的充血讓我開始擔心他會爆血管。可能他見我沉默無言,又沒有什麼表情,加上他往前直衝了5分鐘,以他的年紀來說已是極為難得,他剛想停下來呼吸換氣,我的頑皮人格便跑了出來,心想,不可讓他停下來,於是用手輕輕按著他的肩膀,親切地,温柔地說:我不可以。 這句話對他來說簡直是魔咒,話音剛落,他便像受了電擊一樣繼續往前跑,不斷提高音量,青筋爆裂地又說了5分鐘。在他下一次的停頓喘氣時,我用了另一種方法。 那時電視台的廠房建在郊外的一個山上,除了古裝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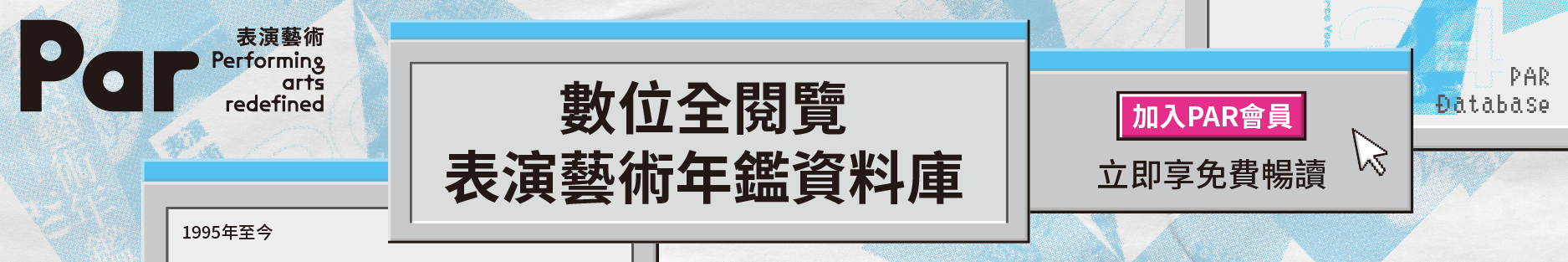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我喜歡看戲,每次看戲都會有好多不同的得到,可以讓我思想許久,「人生如戲」這樣的觀後感更是常常。但那個瞬間,我既是觀眾,也是演出者,我馬上要演出的,就是幾分鐘前身為觀眾的時候所感受到的。這對我來說是很奇特的一個經驗,因此無法忘記。每次想起來都感覺自己還是當時那個坐在側台樓梯上,抱著水瓶等待上台的我。台上燈暗,換景。當燈再亮起,就是我的場子了,不管準備好了沒有,不管你再不想,就是得要開演。

在音樂劇《勸世三姊妹》中,編劇詹傑與作曲康和祥攜手創作了一首動人心弦的歌曲。這首歌巧妙地結合了傳統牽亡儀式中的〈遊花園〉,以及劇中主角多年來無法找到生活與愛情重心的心境,成為一首關於含苞待放卻未被重視、在靜默中訴說心聲的非典型情歌。歌詞是這樣寫的: 「花長在土裡等待春天開,等待一個有緣人來。」 這段歌詞,不僅深刻反映角色內心的掙扎與盼望,也彷彿道出了我們作為創作者和劇團在面對作品時的戰戰兢兢。 這次到紐約進行演出,對我們來說是一項嶄新的挑戰,希望透過這次的測試,為進軍國際音樂劇商業市場邁出第一步。在這消息出去前,我始終擔憂外界誤解我們此行的目的,認為我們只是去進行文化交流,或者單純試圖將原本的版本推出去。因此每次受訪時,我也不由得反覆強調:「我們幾乎是要打掉重練!」 為了讓作品在國際市場中站穩腳步,我們不僅需要提煉原本故事的核心,還得調整敘事節奏,讓它更符合國際觀眾的期待。同時,我們也試圖從中學習更大規模商業製作的運作邏輯。這樣的轉變,或許與重新打造一部全新且成功的作品同樣艱難。 好在在這次在創作團隊的共識下,作品再次經過精心調整,濃縮為時長110分鐘的外百匯版,並加入了一位英文說書人,不僅是為了串聯故事,還希望這個角色能使劇情更貼近美國觀眾的文化背景。 在與製作人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重新審視了劇中多種文化元素的定位。例如,牽亡儀式不僅僅是人鬼之間的溝通媒介,更是一場深層撫慰家屬心靈的旅程這段台灣傳統應該如何以最有力的方式傳達給國際觀眾?此外,台語依然是劇中的重要特色,但我們也在思考,如何讓更多外國人體驗到這種語言的美感?是否應在適當的位置更強調台語的吟唱韻律?還有那首串聯起台灣人情感的經典歌曲〈天天想你〉,我們試圖思考:外國觀眾該如何理解這首歌在台灣心目中的地位? 這些來回的討論,既充滿趣味,也讓人備感忐忑,彷彿是第一次約會前的緊張與期待。我們深知,這樣的首次亮相,攸關留下怎樣的第一印象。 《勸世三姊妹》在台灣市場迎來它的花期,卻也開得不易。我們自疫情前便開始創作,經歷無數次修訂、讀劇和演唱會,若非團隊的堅持與眾志一心,以及各式機緣運氣,這部作品或許無法被有緣人看見。 然而,我始終相信,是

真:你應該有印象,在你很小的時候,每次我們要出國,你媽媽都會在家族群組裡面記一個「NOTE」,記錄保險櫃放在哪裡、什麼的密碼是多少各種瑣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怕發生什麼意外。 她過去是護理師嘛,各種狀況看多了,相對務實。但其實我這幾年也有類似的感慨人不應該只是準備好我們的生,也應該思考著死,才不會留下太多麻煩。 謙:你也知道,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好像與各種死亡為伍。小時候經歷阿公的那件事情也是他在加護病房虛弱地喘著,到後來你們到家接到電話,得知他離開的事實,甚至是戲劇也是。 我人生第一次導演的作品就是綠光的《出口》,描述一對夫妻如何面對孩子意外逝世的傷痛,我當初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就非常動容,總覺得死亡雖然是一個我們始終無法解開的答案,但卻不能因而停止去探求,好像一生都要花力氣把這個死結打開一樣。 老天爺好像總是給我很多緣分,讓我從不同角度去思考這件事情齁? 真:不過這幾年,我又不得不更認真思考此議題。你剛剛說到「接到阿公過世的電話」,我也忘不了,他是自殺的。但身為長子,我當下其實沒有多餘的時間悲傷,我得在一天之內處理他的後事,很多情緒都是在後來幾年才慢慢整理清楚的,甚至後來我還拍了《多桑》這部電影,都是因為如此。 事後留在我腦袋中有幾個清楚的畫面:第一是你阿公在病房,用力揮手不讓你進來看的樣子;第二就是讓我確信,未來如果輪到我走向終點,無論如何我不要跟他一樣撒手一走,會給活著的人非常大的打擊,那種痛無從想像起。 所以等到我確實意識到年老的逼近,我第一時間做的就是慢慢整理與收拾,包括收掉公司、清點財務狀況,盡可能不要給你負擔你看,我們連「預立醫療遺囑」都簽好了。我不覺得這是在放棄什麼,反而是對生命一種積極的態度,很多事情你不能放任自己乾等,而是要趁有力氣的時候多做一點。 謙:這真的了不起!負責!我可能也是因為從小經歷了這些,所以即便過去曾陷落低谷,也不會興起結束一切

慌張惶恐,極度需要鎮定心神時,你會怎麼做?吃甜食、去散步,還是睡一大覺試圖忘記一切?有個獲得放鬆和平靜的秘密神器聽威爾第! 耶誕節前夕旅行到義大利北方的城市帕馬(Parma),這裡好吃的東西特別多,不管是色澤美麗的生火腿、跟車輪一樣大的乳酪、包了各種餡料的餃子,還是剛起鍋熱呼呼的炸雙胞胎都是不可錯過的美食。帕馬也是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的故鄉,歌劇大師威爾第則誕生在距離城市不遠的小鎮隆卡萊(Roncole)。 我不由得想起一個和威爾第有關的研究計畫!英國牛津大學的大腦科學家與生理醫療團隊曾經發表一項非常有趣的實驗:研究人員發現,如果想聽音樂鎮定心神,比起流行音樂、搖滾或爵士樂,古典音樂更有穩定血壓、平靜身心的功效;其中最好的選擇,是19世紀義大利歌劇作曲家威爾第的作品。 主導實驗的科學家指出,威爾第的合唱曲、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的慢版,還有浦契尼歌劇《杜蘭朵》的詠歎調,都列在最能安撫身心的音樂選單中,因為這些作品中出現最多「10秒波」,與人類心血管系統的節律波動完美相合。 什麼是「10秒波」? 在大腦與心血管醫學領域,這10秒為一週期的波動變化,被命名為「梅爾波」(Mayer waves):簡單來說,人類的心臟每次跳動後,生理數值都會回送到大腦,但大腦卻會透過兩條以不同執行速度的神經,將控制資訊發回心臟,不同步的狀況每10秒為一週期,正常狀況下,人體的血壓就是循著這10秒週期的節律在波動。 研究團隊將24位健康的年輕受試者等分成兩組,其中12位是職業合唱團成員(3年以上的經驗),另12位則是沒有受過音樂訓練的人,並以隨機的方式讓他們收聽不同類型音樂,除了爵士和流行音樂外,還有知名的管絃樂作品(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第三樂章慢板)、情緒逐漸推高的歌劇詠歎調(浦契尼的《杜蘭朵》中的〈公主徹夜未眠〉)、風格統一且平穩的宗教歌唱作品(巴赫的清唱劇〈只有上帝才能擁有我的心〉)、頻率近似「梅爾波」的威爾第的歌劇詠歎調(例如,《納布果》中的〈飛吧,思想,乘著金色的翅膀〉及《茶花女》中的〈飲酒歌〉);受試者也會聆聽靜默無聲的片段當作為對照基準,研究人員則在受試者聆聽各種音樂選段的同時,記錄心律、呼吸、血壓和血管舒張與收縮等生理數據

作為觀眾,我們該如何以能被接受的方式提供回饋?又該如何以提問代替命令式的建議?作為藝術家,我們該如何練習這種「傾聽的藝術」,面對感覺讓人難以承受的大量回饋,從中篩選出那些真正能推動作品進步的建議?

一個蘋果放在高山上,如果沒有人說,那裡有一顆蘋果,蘋果就不存在。 就像《PAR表演藝術》雜誌跟我邀稿,而且得是放線上,如果只是存在紙本,我敢打賭絕對不會有人看到這篇文章,我也不可能在忙碌的行程中記錄下自己點點滴滴對內容產業的觀察。 內容太多了,市場太小了,這是廣泛內容從業者正在面臨的問題。 2010年,Google的執行長施密特就說過,過去兩年人類生產出的資訊量,超過過去兩百年的總和。到了2024年,已成為前執行長的施密特,在一場史丹佛大學的演講(已被YouTube下架),提出了,TikTok並不是一個社交媒體,而是一種電視形式,美國用戶平均「每天」使用該應用程式90分鐘,製作200個短影音。現在人人都能生產內容、資訊,取得的成本還極為低廉。 學生時代,週末排滿就差不多看完該週的演出、上映的藝術片,買到一張專輯,就好好地從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還要攤開歌詞本努力鑽研它的設計跟每首歌串連在一起要傳達的意義。但現在,選擇太多以致難以選擇,有些以為有意義的事情,會否根本就沒有意義?現在,一首歌的時間愈來愈短,「出專輯」早就不是一個回收成本的商業模式,實體演出才是。所謂「影集」,也進一步出現更短的形式,不只集數更短,很難再見過去動輒60、70集的大長篇連續劇,在廣泛的平台上也出現了把角色動機說得非常清楚,5分鐘、3分鐘甚至1分鐘的豎屏劇;漫畫媒材,手機方便閱讀的條漫崛起,與頁漫分庭抗禮,成功的條漫每回解鎖的金額可以帶來比頁漫更多的收入。條漫在韓國,成為一種內容的載體獲得許多巨大的改編成功,某些分鏡與畫面的細膩作為傳統頁漫讀者在意,但對僅僅只是想在通勤的路上得到撫慰的許多人(這一切並沒有對錯),可以很快地沉浸到另一個世界,了解一下主角的歷程,就夠了。而不同形式的漫畫也發展出不同美學,只是評論體系來不及跟上。至於「看電影」,過去對我們來說電影院是看電影的唯一途徑跟體驗,但現在家中可裝的巨大螢幕早就替代原本電影院的功能,就像線上會議,我們都知道實體肯定會更有效率,但線上的便利讓我們早已回不去。要付出的時間成本、移動成本難以估量;今年日本出現了58分鐘的電影《暮然回首》,創造了超過10億日圓的票房,1小時不到的電影,以前難以想像,但當我自己走進電影院買票的那刻,想到電影只有1小時,鬆了一口氣,得到的體驗也非常滿足。


有一年中國京劇院來台的預售不佳,經紀公司央請于魁智貼出拿手戲《打金磚》,果然奏效,迅速客滿。演出氣氛熱烈,觀眾情緒高昂,謝幕更達沸點。坐我前面的6、7位年輕同學,一邊起立興奮跳叫,一邊圍著帶他們來的老師,想要一起歡呼。但老師很嚴肅,頭搖得像波浪鼓:「不合史實,不合史實!京劇這個劇種,就只是演員會翻翻摔摔而已!」同學們不敢繼續興奮,我很不服氣,很想趨前拍肩勸導:「放輕鬆,來點幽默感好嗎?」 的確,《打金磚》劇情扯淡,演「漢光武劉秀好酒貪杯、迷戀女色,把滿朝功臣殺得精光,最後自己在太廟仿佛見冤魂索命,驚嚇而亡」。 不合史實的戲為什麼能成為經典傳唱不歇?表演太刺激了,邊唱邊摔邊翻的高難度表演,絕對是觀眾激賞的第一要件,但我想若要說服這位老師,必須說:劇本道出了觀眾的共同心理普遍渴望。 民間戲曲直截了當演出市井小民對於現實人生的看法,人民心目中的帝王,就是「好酒貪杯、濫殺功臣」,誰當皇帝都一樣!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小老百姓能怎樣?只能在自己編的、自己演的戲裡罵皇帝幾聲髒話而已!要罵,罵誰呢?撿秦始皇、隋煬帝來罵算什麼過癮?史書上都罵過了,罵這些公認的暴君有什麼意思?挑一個沒人罵過的漢光武劉秀到戲裡來痛扁一番,那才過癮! 編劇真是高招!打蛇打七吋,擒賊擒王,直指核心。 我猜當初《打金磚》的編劇構思劇情時,心裡一定這樣想: 「史書上說劉秀是零缺點好皇帝,誰相信?我們小老百姓不懂文字、不信文字,史書怎麼寫不關我事,帝王有的是權,我們有的是戲,不在我們自己的戲裡過過癮,更待何時?」 這樣的想法有點阿Q,但不這樣還能怎樣呢?於是,漢光武帝的「暴行」傳唱數百年。而這就是民間戲曲的創作動機,怎一個「爽」字了得! 看這種戲,千萬別從「史實、本事、音律、用典、文辭」來嚴肅分析,請試著「透視」文字和情節背後的「文本潛意識」,才能將劇本置於生成的文化脈絡中,精準觀察,自在享受。戲裡的劉秀未必是歷史上的劉秀,他只是百姓心中君王的必然形象,觀眾在為演員叫好時,早就忘了他演的是哪個皇帝。 再舉個京劇《大劈棺》(莊周試妻)例子,記得前輩名丑吳劍虹老師曾說,劇團貼出《大劈棺》,觀眾如果問「誰演莊妻?誰演莊子?」那就外行了。這戲主角固然是莊妻,另一大看點卻不是

YC, 開始聊之前,想對自己吐糟一番。這陣子寫作,爬梳過往港片觀影經驗,難免有種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感慨,顯得不合時宜,究竟此舉與現地當下的連結關係何在?只好來個夫子自道,追述無意懷舊,知古有意鑑今。 上篇曾提到喜劇需要有情境脈絡、結構、對手和身分設定。我想到了1970年代的《72家房客》,故事描述一幢舊式庭院大樓,住著72家房客,皆為勞動窮苦大眾,心地樸實善良,個個相濡以沫。包租公包租婆則是惡形惡相,聯合貪小便宜的刑警不斷壓榨他們。典型的正邪兩立,富人都是壞的、好人都是善的,於是各種情境衝突就在每次爭執嬉鬧中鋪展開來。比如因為房客們無法繳出租金,包租婆限制他們每天只能用兩桶水,於是洗澡洗衣刷牙等糗事層出不窮,咦!是不是似曾相識?沒錯,周星馳《功夫》的豬籠城寨。再來某位上班族每天穿著西裝上班,回家後,外套一脫,赫然發現內裡的白襯只是掛在脖子和手腕的各別碎布,外表風光內裡滄桑。而多年以後一直有印象是某段諧音哏,因為誤報火災,消防員來到,趁火打劫:「有水有水、冇水冇水,要水過水,冇水散水。」粵語「水」有多義,亦代表「錢」,到處找錢叫「撲水」,希望對方退錢叫「回水」。所以上半句意思是:「有錢就有水,沒錢就沒水。」下半句「過水」是「拿錢過來」,「散水」是「各自散開」,既「有錢拿過來,沒錢就收隊。」言語趣味令人莞爾。 回想年少時期的喜劇啟蒙,不得不提許冠文。第一印象來自他演出的《大軍閥》,扮演目不識丁又好大喜功的軍閥,頂著光頭、留著仁丹𩬅,一臉滑稽,形象逗趣,果不其然,甫一出場,因為向龍王祈雨不成,便下令對天空開砲,結果天打雷劈,下起雨來,荒腔走板,歪打正著。70年代的香港喜劇得算上許冠文、許冠英、許冠傑,簡稱許氏三兄弟一筆,代表作有《賣身契》、《半斤八兩》、《摩登保鏢》等,多描繪小市民的苦中作樂和反敗為勝。許冠文身兼編導演,多扮儉嗇刻薄又自作聰明的老大,很多處境笑料基本上圍繞著他的自以為是反而出糗來堆疊;許冠傑則帥氣、身手矯健,負責與女主談戀愛,單飛後的《最佳拍檔》系列延續了這種形象,但其實他更大成就在歌

第一次知道吉賽兒.韋安(Gisle Vienne)是在法國演員阿黛兒.艾奈爾(Adle Haenel)2023年的一封撻伐法國影視圈縱容權勢性侵犯的公開信裡讀到的。 阿黛兒在最後一段寫到:「自2019年以來,我一直與吉賽爾.韋安的戲劇與編舞合作中追求我的藝術作品。她是一位藝術家,創作了我見過最強大的作品之一。面對電影業樹立的不屑、空洞、和殘酷的運作原則,她讓意義、作品和美不斷地發揮作用,如同一盞明燈,讓我對藝術強大的力量保持信仰。」 當時我沒有去細究在這嚴肅的政治宣言裡,占據一整個段落的藝術家究竟是何方神聖,因為我對這篇文本的表演性深深著迷,準備開啟一系列「退出宣言」的實踐創作。阿黛兒的公開信正好迎接當時台灣的#Metoo浪潮,「取消、退出」是我抓取出的核心。接著我在空總C-LAB開設了幾場工作坊,帶領參與者寫下自己要退出、取消的身分與處境,並拍攝錄像宣讀,簽署宣言等行動,最後階段展演得到的一種回饋是:退出然後呢? 我總不小心被這句反問給惹怒。「然後呢」完全戳刺到#Metoo運動最深層的無力感,許多案例發現往往到最後退出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又或許,更讓我痛苦的是關於藝術無用的無解辯證。後來我認清「宣言」是一種感性的政治革命,其中所碰觸的「壓迫」沒有所謂的本體,因為壓迫是一種關係。 這個後來就是現在,讀到阿黛兒公開信的一年後,我在柏林親臨了吉賽兒.韋安的展覽:「This Causes Consciousness to Fracture-A Puppet Play」,回國後的隔天立刻在國家劇院看了她的舞作《群浪》。神秘的共時性,讓我在最短時間見證了阿黛兒所言,並讓那所謂強大的藝術力量的源頭也穿越過我。 在柏林駐村期間,我看了超過20檔展覽,吉賽兒的人偶展絕對是體感深刻經驗的前三名。一進展間,我就被高坐在展台上駝著背的長髮女孩嚇到。當你順著動線經過她時,會有些不好意思但依然忍不住想彎腰看清楚她的臉。你知道她是個偶,你可以稱她娃娃,可是很想開口問她叫什麼名字?此刻已進入序場,別忘了這是一齣「木偶劇」:A Puppet Play。

近期即將上映的《幕前幕後:范克萊本鋼琴大賽》已掀起一股熱潮。原訂於2021年舉辦的大賽因疫情肆虐延宕一年,沒想到2022又碰上俄烏戰爭爆發。范.克萊本大賽秉著音樂不與政治並論的信念,扛下輿論壓力,一舉創造出來自俄國的銀牌與烏克蘭的銅牌得主,更由來自南韓尚未出國深造的任奫燦(Yun Chan Lim)以非人的12首李斯特超技練習曲及累積至今1600萬次觀看的「拉三」演出殺出一條血路,勇奪金牌,成為現今最閃耀的新星。不得不說,這等拍案叫絕的好萊塢級實境鉅片那裡找?而誰又不會為了這些用生命創造音樂的演奏家們動容共情? 實際上,這等千鈞一髮的實境片其實屢屢在近乎所有比賽中上演。早在1958年,來自美國的范.克萊本(Van Cliburn)即於冷戰時期拿下首屆俄國以宣揚國威之衷舉辦的柴科夫斯基大賽金牌,成為美國民族英雄,舉國歡騰。眾人矚目的華沙蕭邦大賽也成為實境電影《Pianoforte》,下一屆2025蕭邦大賽更是於現今(一年前)即完售近乎一整個月的大賽場次。今年的巴黎奧運更以整個城市為舞台開幕,以不可能的任務匯集巴黎鐵塔、塞納河、地下墓穴、流行、古典音樂、文學、繪畫、品牌行銷了整個法國文化。比賽已不單純是比賽,不論你是參賽者或觀眾,從你接觸起的那一刻,它即是世界的中心、全人類的舞台,更為主辦國帶來強大的文化外宣及經濟效應。 難道台灣就不能有屬於自己的國際大賽?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藤田梓老師及2003年的陳郁秀主委均舉辦過台灣的國際鋼琴大賽,可惜自2003年就絕後了。想來實在非常不容易,舉辦國際大賽的成本實在太高。從國際轉播,大賽評委的旅運與評審費,為期至少1週、3輪共10場以上的國家級場地租金,決賽賽事的樂團及指揮費用,還有國際行銷、網站架設、行政人事、鋼琴搬運調律、比賽獎金(國際規格通常為第1名兩萬美金,第2名一萬五美金等往下類推),以至參賽者的旅運費(國際規格中能通過預選輪的參賽者通常會有機票補助及免費住宿),實在非常地驚人。 話雖如此,事在人為,於2020年疫情前的2月首屆「國際大師鋼琴大賽」(International Maestro Piano competition)於台北登場。所有賽事於國家音樂廳舉行,決賽邀請了國家交響樂團,並國際直播,成為國際比賽聯盟會員,集結國際知名評委及參賽者。2025年1月,「國際

紐約氣候宜人到讓人有點羨慕,秋季此時盛產蘋果,還記得以前學生時代,超市裡的蘋果各個爭奇鬥豔,甚至到了傳統市場,時常一逛就出不來了。 但此行來紐約行程滿滿、無法那麼悠閒,除了為了明年即將去到紐約演出的《勸世三姊妹》演出作前置作業,更是為了趕上一年一度、由美國音樂劇場聯盟(NAMT)舉辦的「音樂劇新品節」(Festival of New Musical),考察最新音樂劇的趨勢與作品風貌。 為期兩天的活動,主辦單位安排觀眾坐在《戲啊!出包惹》(The Play That Goes Wrong)平時演出的劇院中,趁著沒演出的空檔,以坐讀的方式看完了8齣來自全國各地的創作。創作者上台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自己的故事,讓台下觀眾都很清楚知道故事的賣點與核心,接著便是45分鐘的讀劇呈現,沒有燈光沒有走位,僅靠著紮實的創作打動人心。 這些作品中,有些已經在地方場館的支持之下發展超過5年,也有的作品曾經參加評選,贏下第一筆可投入製作的資金。現場也有來自各地的超過500位製作人或單位,包括韓國的投資公司,都坐在台下準備與作品展開直接對話,討論未來繼續壯大作品的方式,不論是邀演或是入股,每日節目後的交際應酬宛如小型的華爾街。 據主辦單位說,本屆光收件就收了500多件,可想整個市場環境背後的能量如何撐起個商業金字塔,但明顯地,他們也更願意花更多的時間等待作品長成,從這樣的環境中彷彿看到百老匯對作品的共同態度:嚴謹耕耘才能期待碩果累累。 每看完一部作品,我便和《勸世三姊妹》的美方製作人 Ken Dingledine 與 Barbara Darwall 一起討論、交換對作品的想法,並且交換著對明年製作的共識,他們指出,專業製作人的工作不僅是尋找資源,更是要能夠在文化差異與語言隔閡中,找到讓作品生存的關鍵點。 音樂劇不僅是藝術表達,更是一種與觀眾建立聯繫的方式。我們的作品應該如何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必須得先深入了解目標觀眾的期待,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作。也因此在TECO(註)的協助安排下,我們趁著會議間的某日空檔,和在紐台人與劇場工作者進行了一次深度的對談,並且接受各方回饋。這些行程都在在提醒著我,尋找那個「鉤子」

這片古老的山林,似在晨霧中緩緩吐息,微光與陰影糾纏,將難以捕捉的脈動散播於空氣。靈魂隱伏在土壤之下,無形的回聲迴盪著,低語著遠逝的記憶,宛如不可言說的景色,徘徊在時間之外。這片土地或許被稱作森林、海洋,亦或有著更古老而無聲的名字。 「他們來到陌生的土地,手中是利器,眼中是冷然。而在他們看不見的陰影裡,土地的靈魂沉默注視,如隱約低語般,等待著自己的聲音響起。」 晨曦剛剛透亮,島嶼的山巒似乎在霧中沉浮,微微地顯露形體。松柏的枝葉緩慢地交錯,彷彿在輕輕低語,隱藏著無法名狀的呼吸。這片靈韻隱約而幽遠,彷彿每一片葉、每一寸根,都在說著不曾傳出的言語。老榕樹的根深深扎入地底,無聲地交纏,像在握緊什麼,不肯鬆手。無聲的顫動掠過枝葉,如隱約的告知,帶著一絲靜靜的、不易察覺的警示。 老榕樹:「靜寂的時光已然短暫,枝頭上的小鳥啊,你察覺到了嗎?他們的步伐將擾亂這片土地的脈動,把那鋼鐵的冷意推進土壤之中,把我們深深的根脈剝離、撕裂。」 雄鷹(掠過的影子):「他們無法看到翅膀的閃動,感知不到我在風中的行跡。他們追尋的是無形的掠奪,彷若這片地的呼吸只為滿足他們的無窮渴望。」 蘚苔(似喃喃夢語):「若他們聽不到晨曦中的微響,這片地將在寂靜裡慢慢變質。我們的存在無聲而深沉,靜靜地盤踞在陰影裡,孕育出未曾出口的回響。」 「大地吞沒一切,記憶如同幽光流淌,在無人之境輕輕滲透。他們的手指觸及殘破,卻無法觸到無聲的脈動。」 根脈的靜待,黑熊無聲地穿行,耳朵大而圓,吻部長而形狀似狗,他的眼睛小如深潭中的微光,冷靜而幽邃。他並不急於現身,這片森林便是他的隱秘之地。百步蛇悄然滑行,蜷縮盤踞,翹起的吻端,像在等待某個時刻,無聲而寧靜。每一片陰影中彷彿都流動著無法察覺的氣息,靜待著未曾降臨的瞬間。 黑熊:「這片土地是我們的歸宿,而他們卻帶著鋼鐵和火焰來到這裡。他們的手中握著冷硬的利刃,若他們留下痕跡,我們的聲息便會沉入泥土,成為無聲的隱喻,靜靜潛伏。」 百步蛇(冷冷低語):「他們的腳步註定迷失,鋼鐵也終將銹敗。若他們踏進我的境地,將見識到這裡從未出現的惡意,這是我對不速之客的回應。」 <p


「新」編舞家的定義頗難拿捏,什麼是新?何時才算「不新」,並非指年紀,可能是綜合作品的數量、規模與所獲資源。近期看到黃騰生、郭爵愷的作品都好喜歡,但也許我錯過的更多,個人觀點難免偏頗,個人的視野與經驗絕對有限,但透過不同平台,不同網絡,不同評審的專業與角度,也許能找到最大公約數。

關於洪席耶的美學理論,我想最大的誤解在於以為這位哲學家反對「政治藝術」。於此,引號裡的政治藝術指的是狹義的政治藝術,即直接處理政治相關議題的作品,例如這幾年台灣藝文界患了流行性感冒似的「白色恐怖熱」。 洪席耶認為藝術與廣義的政治遙相呼應,因為兩者都和「分配」有關,而且很多時候,尤其是保守年代,藝術不自覺複製了社會的分配,包括音量的分配與能見度的分配。雖然底蘊互通,藝術畢竟不是政治。政治利用藝術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當藝術自甘為政治服務,自然是時代的悲哀。 反觀批判藝術,它的理念是藝術應和現狀作對。然而就洪席耶而言,它的問題在於目的性太強,使得藝術淪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 「政治藝術」 洪席耶對當代「政治藝術」有不少批評。他批評的面向和題材無關:誰說白色恐怖不值得書寫?誰說環保意識、抗爭事件、性別議題、種族歧視不值得呈現?問題不在題材,而在創作者的意圖、手法和視野。 自1990年代已降,西方「政治藝術」已深陷窠臼。第一,它意圖過於明顯,簡直是一翻兩瞪眼:例如「萬惡的資本主義」,或如「控訴戰爭、堅決反戰」。第二,說教意味濃厚,藝文已淪為發聾振聵的工具,也因此把受眾當作需要教育的對象。如此一來創作者自居「知」的位置,而受眾設定是「無知」;第三,立場鮮明的結果就是犧牲了藝術、屈就了政治,導致藝術淪為政治立場的肥皂箱;第四,藝術之為工具也好,之為肥皂箱筒也罷,創作者誤以為意圖等於效應,因而高估了藝術的能耐,低估了受眾的智商;最後,一味的批判降低了藝術的層次,因為只要涉及批判必有對錯之分,但美感體制的可貴從來不在於指認對錯,而是提供抽離自慣性思考的美感經驗。 是不是不批判就好一點?答案是更糟。舉個極端例子,台灣劇場所有關於近代歷史人物的呈現大都乏善可陳。它們是狹義政治考量的產物,一味的歌功頌德。在這些呈現裡,政治正確是必然的態度,歷史人物的純潔無暇是必然的人設。創作者簡化了曾經有血有肉的人物,簡化了曾經複雜的人生與歷史背景。 《我們》 「政治藝術」本身並無基因上的缺陷,有些作品其實境界頗高。 美國導演喬登.皮爾(Jordan Peele)的《我們》(Us)既是一部精

有一次在整理過去零星照片時看到一批精采的戶外演出畫面,卻突然捫心自問,看表演的過程我只顧緊盯著手機面板,深怕漏掉精采鏡頭,但當時我有真正以肉眼直接體驗、好好觀賞現場瞬息萬變的實境全貌嗎?雖然保存了照片或影片的記錄畫面,聊供日後回味,但明明曾置身表演現場的我,在欣賞當下其實失去了某些獨一無二的現場感受。

在所有演技怪招中,最難以參透的算是「化屎大法」了。所謂化屎大法者,便是把自己化為一坨屎,然後種出漂亮的花朶。這怪招的出處是有個長篇故事的,若大家不嫌棄我囉嗦,請聽我道來。 當時我還是無綫電視的合約藝員,在那競爭劇烈的年代,算是演出機會比較多的男演員之一。那時剛接到一部新劇,演的是男一,看過劇本後,也非常喜歡角色及故事,有很大發揮的空間,但總覺得,太像周星馳了,簡直是同一個版模。於是去打聽,原來劇本真是為他訂做的。 當年周星馳的演出方法非常新穎,充滿喜感,又荒謬,從來沒看過有那樣的節奏和演繹,因此人們無以名之,便稱之為無厘頭,其實這是句粗話,意思是沒有道理,分不清楚的意思。 當時電視台分配工作可說像奴隸工廠制,當紅的演員可同時分配兩部劇集的主角,周星馳便是其中一位,演員當然也可以拒絕,但這不健全的行業有個不成文的規則,叫做雪藏,你拒演,好!便把你放進冰箱冷藏,待你人氣下滑,看你如何?除非你在電影圈已站穩腳跟。 周星馳便是站穩腳跟的一個,雖然當時他還在拍攝另一部劇,但已在電影界中獲得堅實的演出機會。無論最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反正他就是把為他訂做的那部劇推掉了,我是頂替的一個。 大家知道日本漫畫《城市獵人》主角冴羽獠吧?劇中人的描繪和冴羽獠十分相近,若細心分析周星馳的演戲方法,你會發現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便是來自漫畫,特别是前期的演出。 當時在影視圈中可大概分為3種演法。一是傳統的、技術的、工整的,在年輕人眼中可能認為是死板的、固化的。第2種是年輕演員向外國演員學習和模仿,自然的、生活的,所謂方法演技,但這方法只能算是皮毛,沒有方法的系統和深度,因為當年根本沒有人教授和懂得方法演技,所以大家只可模倣及從經驗中自我探索。第3種便是周星馳的方法,内中包含了多種源流,從前面提到的漫畫,還有粤語長片的古典和自由,及至吸收了好幾位喜劇泰斗的風格,當然還有其他,但在這裡不詳述了。反正我看完劇本,獲得的第一印象便是周星馳,再四處打探印證,果然是周星馳,結論是,唯一的方法便是模仿周星馳。 模仿他的動態和聲音節奏不難,難的是知道他處理劇本的方法,幸巧當時我們就在相鄰的廠房拍攝,有空檔我便去找他請教,後來演出的效果我是很滿意的,同劇的其他演員也認為很像。但問題來了,拍了三兩集,

真:說起死亡,因為我從小在礦區長大,礦區經常有災變發生,只是報紙不會寫,也沒有人會跟你講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死亡這種事情最親近的例子,就是當時早上才摸摸我的頭、要去上班的叔叔,下午就被通知發生意外。跑到坑口去看,他已經躺在那邊了。然後,看到他的孩子跪在旁邊,在燒腳尾錢。 我在旁邊看了一直哭,大人看我哭那麼傷心,就說:「那個叔叔疼你疼得很有價值。」但事實上,我不是哭泣死亡,而是為活著的人難過他們還那麼小,就跪在那邊燒紙錢,那個畫面讓我覺得很難受。而且,我的經驗告訴我:再過一陣子,這些孩子就無法跟我一起念書、上課了,因為經濟支柱沒了,他們可能會需要到外面去當童工。 後來當兵的時候,看過更多。不過那種「前幾分鐘還好端端的人,沒多久就再也救不到了」,這種感覺無論如何都非常衝擊。 謙:這樣說起來,我覺得死亡的記憶可能也是有著時代差異的。到我這個世代,面對死亡的啟蒙相對沒有那麼殘酷。即便我年紀蠻小的時候,外公、阿公相繼過世,也參與了葬禮。但,什麼是死亡?這概念還是蠻懵懂的。 倒是,有個片段不知道為什麼記得非常清楚。大概是國小四年級的暑假吧?當時我很著迷各種天文科學的知識,某次跟媽媽一起搭公車,坐在最後一排模模糊糊睡著了,在夢中,我把當時讀過的東西好像都真實經歷了一遍包括太陽原來是有壽命的,到最後它有可能吞噬周遭的一切,也就是我們建立起來的所以事物都會有消失的那一天⋯⋯儘管它可能是千萬年以後我被這個夢嚇醒了,本想試圖跟媽媽表達這種恐懼,可是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過去曾經在某本書中讀過:人其實會誕生兩次,一次是從母親的子宮出來,另一次則是你意識到死亡的存在。這樣說起來,我的第二次誕生大概就是國小四年級的那個夏天吧?而且那種恐懼反而讓我興起一種:「既然最後一切都會歸為無,那不如現在活得開心一點。」的意志。 如果死亡,只是一種「轉變」的形式 真:到我這個年紀,就覺得死亡好像隨時都會出現。以前還沒有這種感覺,倒是現在連醫生都常常提醒:你已經70歲了,動作要放

YC, 這次來聊聊喜劇吧,一個我覺得很不好談的題目。前陣子意外在YouTube發現很多網紅談論著周星馳的電影,可惜捕風抓影的八卦成分居多,再不然直接封神,把許多過氣、新人或載浮載沉的演員成就於他的發掘與力捧,幾乎變成了香港電影工業的金手指,被他欽點之人,命運隨之起舞。可是周星馳為什麼「好笑」?這裡頭究竟發生什麼事?這些博取流量的影片在一輪嘴砲之後莫衷一是,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 影星毛舜筠曾在某次訪談,聊起曾志偉和周星馳的差異。她說曾志偉很搞笑,但不見得擅長於喜劇,他在台上當司儀、主持,腦筋很靈活,應變能力極高,言語之中戲弄、揶揄,常天外飛來一筆,正中要害,讓你猝不及防,要嘛愣在當場、要嘛只能傻笑。有句粵語「執生」很傳神,既見機行事、隨機應變之意,跟曾志偉搭檔,就得強大自己的「執生」能力。相反的,她說周星馳沒有急才,無論表演誇張與否,他都需要仔細計算過、思考過,不是胡謅亂道,而是雕琢得很仔細。我們在螢幕看見的無厘頭其實是深思熟慮。所以在訪談中的周星馳不那麼好笑,有很多空拍,甚至接不上主持拋過來的球。我想在這裡,毛舜筠無意間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喜劇會搞笑,但搞笑不是喜劇。搞笑只有一瞬,不在乎過去未來,當下爽快,效果就算達成。而喜劇在乎情境脈絡,前面怎麼過來,後面跟著怎麼走,需要鋪墊,前後呼應,喜劇需要有內在結構的生成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很多演員想走周星馳路線卻畫虎不成反類犬,以為引發觀眾笑點是唯一結果,便扮鬼扮馬,卻落得裝模作樣的印象。 再則就是對手。毛舜筠形容和周星馳對戲像打球,球打過來打過去,愈打愈起勁,才發現原來需要這樣的節奏,演到哪要快一點、要慢一點,演到哪要停一停、等一等,力道有輕重,節奏有緩急。說到這裡,相信你會馬上想到周星馳的最佳搭檔吳孟達。的確,在電影中觀看兩人你來我往的演繹就如同一場精采絕倫的球賽,高手對決,淋漓盡致,享受的不是結果的輸贏,而是相互成就,貢獻了一場又一場回味時嘴角會揚起的場面。兩人從電視劇《他來自江湖》到電影《少林足球》,合作10多年,默契自然不在話下,彼此相輔相成,如同相聲的捧哏和逗哏,卻又不拘泥於既定程式,在套路之中不按套路出牌,自嘲娛人,以詼諧燃點莊嚴,以戲謔撫平難堪。</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