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茲與許多偉大的作家一樣,都是無可救藥的偷窺狂,《點歌時間》的誕生也是出於偷窺欲及幻想。他關懷女性和中下階級人物是出自真心,而非他的社會屬性,幾乎有布萊希特的高度,只不過他沒有布氏那麼有名,他也有海明威的氣質,男性、陽剛、永不妥協,只不過他沒法把自己一槍射死。

一晚上的仗,就只有這幾個人在打,其他的幾十口子,全都趴在掩體後面,不讓他動,就一點都不可以動,免得礙事。對方一個營的日軍擦完槍,抹完了刀在「閉目養神」,似乎已經感覺到橋對岸的支那軍,缺乏裝備、缺乏歷練的一股貧血味。

只有高明的鼓掌人才知道,在什麼時候該大叫bravo,什麼時候該連續呼叫,如果呼叫和鼓掌的時間點不巧妙的話,明眼的觀眾馬上會看出破綻。還有,鼓掌人如此精通歌劇,不但對歌唱家的好壞看得清楚,也知道他們的弱點和優勢,最厲害的鼓掌人看得出來演出者什麼時候安全上壘,什麼時候漏失,他們在安全上壘時大聲呼叫,肯定能使演出者再加分。

常楓常爸爸,孫越孫大哥,在表演領域裡,早就經驗豐富,弓馬嫻熟。他們的做人處世,又聰又明,對世俗的認知和寬容力,我根本無能揣測。我想多拜望一下他們的基本願望,是想去細細地聆聽他們的沉靜,從而得知當年的喧嘩;去慢慢咀嚼他們曾有的虛空,卻可讓我自己飽餐一頓。

談起他們自己,眼神又亮了起來就是他們那種人的眼神,一個經過了大時代的生離死別,多災多難的動盪環境裡,才有的一種「情緒記憶」的眼神。如今雖然時光已舊,但是在我心裡記憶猶新,那一張張來自大江南北不同的臉,卻有著相同的一種眼神,反映著那個不知道要怎麼過、可是又得過的時代,一樣的迷茫。我大概還能演得出來,但是沒人寫這種劇本了

七年前德國文化部決定把柏林劇院讓三位新銳出來執掌,今年卅八歲的歐斯特麥耶是其中一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他在西邊長大,從小在軍人家庭是個平凡小孩,他哥哥是演員,他們喜歡玩傀儡戲,他從小經營家庭小劇場,從來就是一個自己創造世界的人。他一直覺得社會不公正,他反對全球化運動,他從西柏林望向東柏林,捲著草煙,不疾不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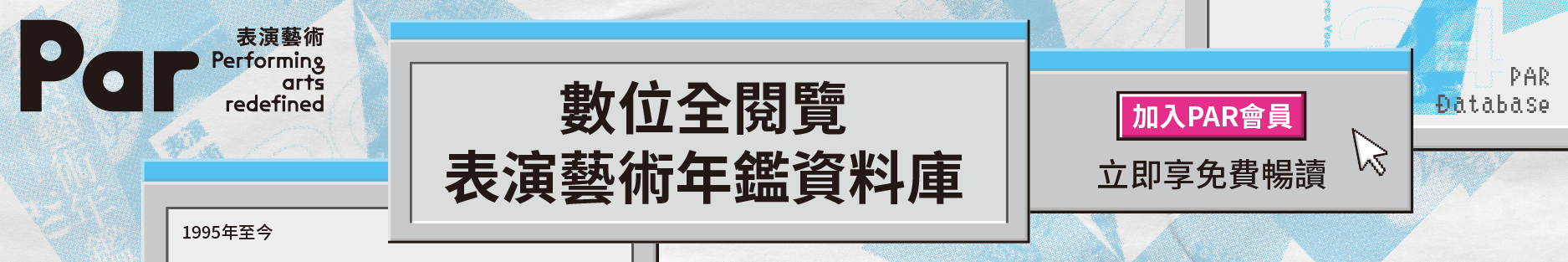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還是那一棟一棟的石山堆,堆出來的氣勢和質感,秀美、壯麗、古樸、雄渾這些中國的古美學詞兒,總覺得都還不夠形容得準確。大概以前就不該瞭解,或不瞭解它太多,結果一見面,心裡準備好的黃山沒看見,沒準備好的黃山,反而看到不少,這還真奇怪!

邁入第六十屆的亞維儂藝術節今年由南斯拉夫籍的旅法編舞家喬瑟夫.納許主力策展。從一九九二年迄今,納許已在亞維儂藝術節發表過七支重要作品,每次都會選擇命題做跨界嘗試。新作《嬉戲》Asobu運用俄國作曲家塔拉索夫的音樂與他自己的編舞對話,以音樂為色彩,舞蹈為畫筆,在想像的畫布上編織了一幅北方大地的人文風景。

字是載具也是意象,在舞台上不太碰觸,他們超越性別,跨過愛欲是非,他們排列,延長,呈現,組合。他們各自呼吸,各自伸展自己的生命,在動與靜之間找到和平相處之道。在書寫的國度,你寫故你在,舞者讓我們明白,無論是書寫或者運動只因紀律而生,美便是武器,美學成為對無聊及貪腐的最高抗議。

去了一個月的喜馬拉亞山,回到台北,很清楚地覺得自己內心中有一份空前的寧靜,過去的是是非非紛紛擾擾,就真的不再影響我了,像得到過一次大山的恩寵,看什麼都是好的,看到自己有個家,房子還是自己買的,還能有一輛燒汽油的車,哇!我太幸福了,我太滿足了。

王爾德在他最著名的小說《格雷的畫像》中說:生活才是藝術的鏡子。而我們在鏡子之前,總是會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就像那晚在舞台上那群隨著燈光顏色換不同舞衣的熱情舞者,跟著變化不大的音樂隨著起舞,他們要撩起的是我們那份要再一次好好在鏡子前望著自己的勇氣啊!

相較於劇場圈內人通常經由口耳相傳,蒐集情報決定欣賞菜單,一般觀眾則是多靠大眾媒體,獲得新作資訊。如今少了報紙大篇幅的報導,大眾如何從新的媒體通路中,接收到沒有八卦渲染、專業不變質的演出訊息與評論,已是一項有趣的挑戰!


佛洛依德揭發歇斯底里症的根由,在那個枯燥難耐的維也納時代,社會秩序仍嚴守著舊式價值,把此病與父權侵犯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相提並論,簡直是自找苦吃,但他成功了,至少有不少人贊成他的說法,當然反對者也視他如洪水猛獸,社會逐漸接受佛氏學說,女人不必再緊緊束腰,性解放才有了可能。

從雪巴族客廳的大長窗戶看到這麼活生生的大自然畫面,在我心裡久久地、自己來重播著,雖然它發生得安靜,我回想起來總感到豪華壯麗,那印象的發生與結束,雖然不能像一篇動人的文章,我想起來,卻能覺得它擲地有聲,好像還悟到什麼道理。

熱情是看不見的,就像那位也許你覺得很悲哀的古董收藏者,但也許是那份熱情讓他在亂世中給他一個每天起床的理由。 人類之所以偉大,因為我們可以有無限的想像力,然後有熱情, 付之行動, 就像法國詩人科克多的名言:Love is Action!

策展人除了靠自己努力學習、開發企畫外,同行之間的情報也不可少,這就是「Gossip」的重要!通常「Gossip」會有加分效果,讓策展人在短時間內,看到自己想看的,也挑到更切合自己需求的節目。

我還在熱那亞的街道行走,港口傳來聲聲催去的汽笛聲,我回頭望去,只看到一艘艘的豪華遊輪和運貨的貨輪,當今的世界涇渭分明,冒險的人都到外太空去了。這個港口跟任何港口都一樣,只剩下消費,再消費。

我們不敢怠慢,有人又拿出好幾包泡麵,煮了一大鍋與他們分享。在上百年但是非常堅固的木屋裡,奶茶、咖啡、泡麵的香氣,瀰漫在兩國的話題之間,融洽、歡喜。


紐約是個不會被討厭或被喜歡的城市,因為她的速度太快了,當你要感覺任何痛苦或歡樂時,下一刻的感覺又擠進你的身體要來挑戰。她也不會要你將她當成一位超級巨星或是高雅的貴婦來對待,她只是擁有一大群充滿生命力的人急著要在老天爺給的框框裡過最充實的生活。

多年前於澳洲阿德雷得參加一場節目經理人的國際交流活動,場內來自新加坡、韓國、歐洲等世界各地人士,談起工作都是抱怨連連。「你們真是一群幸運兒!」這時,新加坡Esplanade濱海藝術中心代表Mr. Benson丟出這句話,「你們抱怨的臉上,充滿了對表演藝術的瘋狂喜愛,滿是自信與享受。」

我如果去看戲,還遇到那種要求觀眾參與的情況,也會不耐煩。我深知,若無必要,最好不要撰擇這種被評論員所稱的「無法無天」的戲劇形式,除非這位演員是達里歐.佛。

我們那次的目標不是聖母峰,而是「遙望」一下聖母峰,目標是喜馬拉雅山脈中一個叫GOKIO的湖,海拔是四千七百米,旁邊有個獨立的山堆,海拔五千四百米,爬到這裡算結束。

去年秋天《歌劇魅影》啟售,六十三場次九萬多張票迅速銷售一空,許多民眾因為《歌劇魅影》第一次走進兩廳院,生命中留下美好的藝術回憶,是我們所獲得最珍貴的禮物。

除了舞蹈,他可以在同一時間裡創作幾個不同領域的作品,他是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動的人,當他不動時,便是在思考動與不動的關連,身體與空間甚至身體與記憶的關連。比爾從來不想下一秒鐘,常常,他的世界秩序只剩下呼吸,他的舞者或穿襪子或穿舞鞋,但都有無窮無盡的身體想像,舞蹈的狀態便是宇宙的狀態,從來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只是活著,跳著,甚至於安靜,再安靜。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