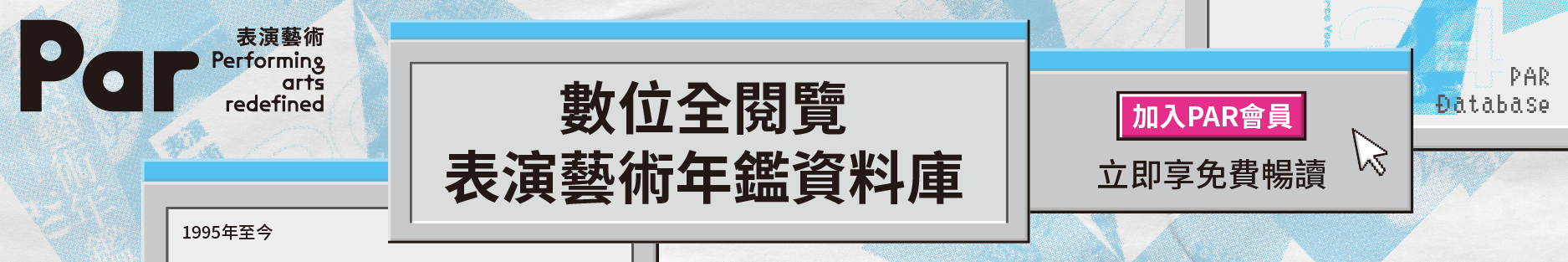賴翃中 我偏偏喜歡矛盾、喜歡衝突,「張力」正是創作最需要的能量
2025年,賴翃中帶著翃舞製作與《推拉》(Push and Pull)橫掃歐洲兩大賽事,並以《BIRDY》席捲北美,主導的「漂鳥舞蹈平台」也邁入第7屆,在國際舞台展現強大韌性,確立了獨樹一幟的美學語彙與國際串聯的行動能力,獲選為2025年《PAR表演藝術》雜誌年度人物。面對創作瓶頸、資源分配乃至外界流言,他展現出獨特的生存哲學。本篇QA,他直面讀者犀利提問,親筆剖析如何在制度與現實的縫隙中撐出張力,尋找空間,將生活的阻力化為舞台上動人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