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舞蹈的「接班人們」
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舞蹈類年度觀察報告近年來「跨領域」的趨勢似乎讓「身體論」成為上世紀的論點,以「跨領域」作為護身符,舞蹈似乎不必再去琢磨身體,而更去強調所謂戲劇化的暗示或影像的加持。

近年來「跨領域」的趨勢似乎讓「身體論」成為上世紀的論點,以「跨領域」作為護身符,舞蹈似乎不必再去琢磨身體,而更去強調所謂戲劇化的暗示或影像的加持。

在一般民眾認為聽音樂會很無聊、所有補助與獎勵也偏向五光十色的綜合藝術的當下,跨領域製作儼然是音樂節目的必備條件。當然,藝術的領域本無疆界,但目前音樂類跨領域製作卻常常忘卻自身的立足點與專業力,更忘卻在與他領域合作之前,必須先對他領域有相當的了解與內化後,始能談合作。

今年的戲劇和戲曲類製作,嚴格來說並未出現指標性或真正原創、令人期待的大規格製作。即使要從過去一年的中、小型作品中挑出特別精緻且完整的入圍作品,也並不容易。難得的是,這一年來各劇團展現了傑出的企圖心和實驗精神,幾乎到了令人歡欣鼓舞的程度;尤以戲曲界的突破最為亮眼。

壓軸好戲為德弗札克E小調第九號交響曲《新世界》,波西米亞鄉愁的揮灑,似乎並非呂紹嘉對這首耳熟能詳名曲的詮釋重點,他主要聚焦於全新觀點的節奏與動態解析,將全曲演得充滿力與美。

對的曲目、對的演出者,是這兩場音樂會最成功的地方;呂紹嘉端出台灣首演曲目,讓觀眾長見識、讓樂團往上攀爬,是這兩場音樂會的意義所在。但這個「對」,需要企畫者縝密的思量與寬廣的眼界,需要樂團日復一日地磨槍待陣,否則,意義,也只不過是白紙上偶然出現的名詞罷了。

這是一齣「沒有明星、只有演員」的全表演呈現。演員黃健瑋、謝俊慧與謝盈萱的許多表演細節,展現了角色的深度與說服力;而全體演員誠懇、真摯和自然的詮釋,讓這一個看似簡單卻關係複雜的故事,完全立體。

華文戲劇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形式上,已經很先進地使用了「扮裝」。 內容上,則是緊抓時代潮流,直接翻譯改編當時的暢銷小說和歌劇。 至於台灣的現代劇場發展,更是經常和「時事」與「時尚」結合在一起。 若要問,華文的現代劇場歷史有多久?答案是:到今年,剛好一百年。 相較於中國大陸大量的研討會和展演活動,台灣可以思索的是什麼呢?


管你喜不喜歡林奕華的戲,他的最新作品《水滸傳》,毫不掩飾地把這個消費社會最時尚的「身體主義」,轉化為一種文化產業式的「豪華」場面,用來阻截原著強烈的傳統意識,你就不能不承認,「非常林奕華」的想像力較台灣同世代的劇場導演實具有更敏銳的「現代」感。

《水滸傳》是一個林氏商場體驗的過程,在全劇真實與扮演的交錯中,小至賣笑與娛樂、他對經典的拆解、他在劇場創造出的時尚幻象,大至論述裡對消費主義的回應(他只是回應,並不是站在不同陣線上),讓觀眾在其中各取所需。他改變了台灣劇場向來習慣尋找精神依歸的表達方式。

舞台設計利用軌道排列組合的「珠簾」景片,切割空間,搭配大量投影的紀錄影片,為本劇提供相當重要的背景資訊,以及解讀舞台畫面的參考。不過,這樣如同戲曲表演般呈現直觀的寫意舞台,卻與許多模擬與再現史實事件的場景質調──或是為了觸動群體記憶──扞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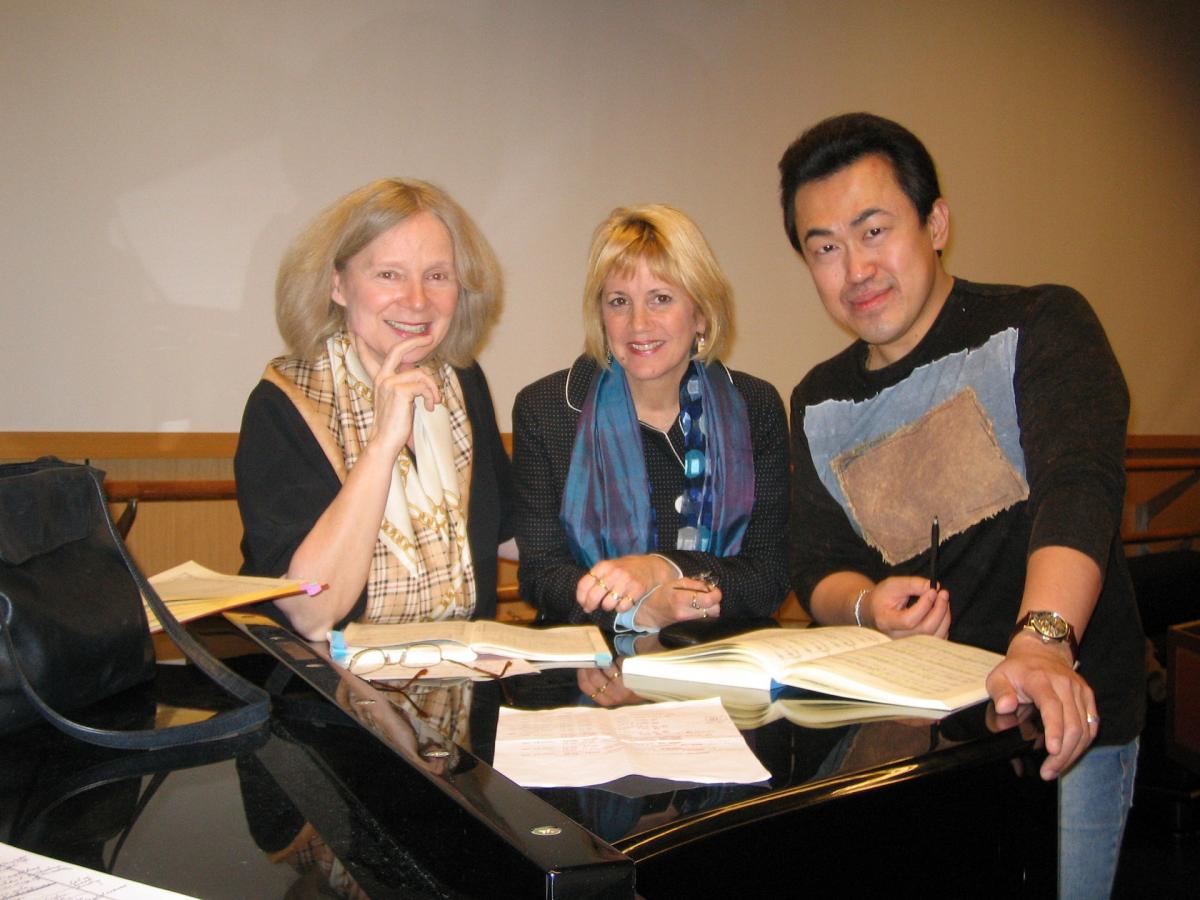
第二部分結尾的《哈利路亞》大合唱,儘管全場觀眾遵循英王喬治二世傳統自動起立,葛羅絲曼也順勢轉身指揮群眾加入齊唱,然而她並未處理得過度興奮,寧可將真正高潮保留到第三部分結尾的《阿門》合唱,讓全曲格局增大,感人肺腑至深,名家手筆的確不同凡響!

鄭明勳所塑造的《命運》,是一種朝向無情終點的不歸路,無論節奏或氣氛都極端白熱化,過程中則不乏高貴尊嚴的堅持。儘管所給予聽眾的精神洗禮,可能尚未達到前輩德奧指揮大師那般深刻境界,團員們卻毫無保留傳達出跟鄭明勳一起做音樂的驚艷與喜樂。

音樂上的創新意圖處處可見,戲劇性更為濃厚。民眾合唱的〈金剛咒〉取材自卡通歌曲〈無敵鐵金剛〉,此新編曲目因為南管音律、樂器、聲韻等因素,座落得不露痕跡;不因卡通歌曲的素材而荒腔走板、引人發笑,也不因此而怪異、破壞氣氛或上下不銜接。


崛起於七○年代戒嚴時期的「雲門」,它所意味的就不僅是戒嚴政治所賦予身體動作的一種保守性,從《薪傳》即可略見一斑,直至現今仍能看到從「太極導引」發展到以書法為概念的中國情調,無一不是身體在翻轉之中可以掰出五、六個以上的動作,大概只能說看「雲門」的觀眾,也許無法適應當代舞蹈其實可以不需要那麼多動作的,或者說動作不應該用來只是壓迫身體在移動時產生動力。這次「雲門」在最新的舞作《風.影》中,號稱與當代重要藝術家的合作,讓我們期待的是兩位大師的合作在表現當代性上,所更能揮灑出來的恢宏格局。 在拚湊起來的動作中迷失的觀點 林懷民作為《風.影》的編舞家,他的表敘能力幾乎都被覆蓋於蔡國強巨大的陰影下,如何在最好的timing把代表蔡國強符號的「爆炸」在舞台上呈現?這也不僅是因兩位大師的合作,而產生這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更可能因此創造了華人藝術家在當代藝術上一種新美學的表現形式。 然而,答案竟然是通過投影的方法來呈現蔡大師的作品記憶,這就顯得有些些抄捷徑了,當然為了這樣的呈現形式,又不得不設計出舞者模仿京劇場面的耍大旗技藝,好讓「爆炸」投影在白色大旗上面,這一切都合情合理到近乎跟看好萊塢電影一樣,令人(尤其是曾在廣場看「雲門」表演的那五萬位觀眾)在小市民的審美經驗上產生很單純化的滿足。 而當代舞蹈中所被論述的「舞蹈」之意義,在這支號稱以結合當代藝術為創作議題的舞作上,就看得出左支右絀,其「意義」不是通過身體意象的形塑而產生,卻在拚湊起來的東、西方動作之中漸漸喪失,終至看到後半部,仍然無法從編舞家提供讓我們可資運用的元素(裝置、影像、聲音)中,建構出一個在觀賞上通過現實思維得以捕捉其意的觀點。 就算有編舞家自己形塑的隱喻嵌於其中,譬如說,玻璃鏡斜掛而倒映出來的身體像顯微鏡下蠕動的生物,配上了青蛙呱呱叫的音效,詭異有餘,卻因「爆炸」語境所延展的旨意缺少了一定的穿透力,當碰到這樣稍具「意義」的隱喻,反而無法讓詭異配合作品議題而產生一定的效用性;語境缺乏了這樣的效用性,反導致作品的隱喻系統在穩定性上的不足。 動作無力形塑身體隱喻的深度感 或者說,場面上諸種所呈現的意象,是用了一種被化約了的語言所表達出來;假若那

大觀舞集的《柯》劇故事版本是參照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和澳洲芭蕾舞團的《柯》劇故事情節重新編創而成,創作者在第三幕中加入與前兩幕情節不相干的超現實〈時光精靈〉舞段,意圖延續浪漫芭蕾時期一貫以精靈般的詩境舞風,表達「現實」與「超現實」兩種精神層面。

由於劇本本身詼諧逗趣,《朱文走鬼》若是照本演出其實已經相當討好。可惜南管和舞踏雖然各自表現得可圈可點,卻在融合時出現了落差,除了南管演員在舞踏的表演上味道不足之外,整體性也因為這樣的落差而被削弱。

若能將這齣戲當作「現代歌劇」來觀賞,諸如:小青不耐地搖扇、接續白素貞以敲門動作應對法海,以及法海出場、輕喚妖怪等段落,都完美呈現了音樂設計和看戲的節奏;只是,劇本先天的台詞和結構似乎無法負擔所謂歌劇緊湊的情節與情緒變化。

《指環》在拜魯特首演一百卅年後,感謝NSO的努力,台灣終於首次在現場聽到了《指環》的音樂,展現出年輕一代音樂工作者的音樂能力,可惜只演一次。盼望不必再等一百卅年,不僅能常態性地聽到《指環》,還能在台灣的歌劇舞台上,看到《指環》「總體藝術」式的演出。

張大勝對狄爾這位主人翁得意洋洋的種種戲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樂團絃樂組在追求少女樂段所奏出撒嬌似的音質相當可喜,斷頭台場景的爆棚動態極為洶湧澎湃。更重要者,其詮釋充分展現出正統德國禁慾式的幽默,而非輕浮的嬉鬧。


莎夏.瓦茲對「雙人舞」幾乎是在抱起、放下的反覆之間造成了一種疲憊的空虛感,我們就漸漸可以閱讀到身體的詩意隱喩在《肉體》的舞作中,既是以當代藝術的空洞話語作為書寫的策略,同時也建構了對歷史記憶的再現行動。

音樂會以莫札特十一歲之作F大調交響曲(K43)打頭陣。哈丁指揮時不用指揮棒,全靠動作細膩的雙手做出提示。他對樂團各個群組的掌控可謂鉅細靡遺、無所偏廢,瞬間動態變化的雕琢尤其精采,整個演奏充滿新鮮的戲劇生命力。

全場共演出七首作品,其中陳中申、鍾耀光、蘇文慶與劉學軒的作品均為世界首演,由於主題明確、四位作曲家也都是為自己所擅長的樂器而作,沒有賣弄做作或無意義的炫技,因此沒有出現單場音樂會太多新作品容易造成的艱澀與乏味。

秦Kanoko在台灣演出的舞踏,凡看過的都會對她的身體的確充滿了充沛的能量表示同感;是的,這次她在《天然之美》中的表演,仍然用了強大的身體能量凝聚出一股興兵作亂的力量;在日本舞踏中,這股叛亂的力量往往提供了建構一種歷史觀點的文脈,將被排除於黑暗中的民眾記憶,撥弄到眾目睽睽之前凝視。

演出的節奏由沈靜而激動;從和緩到活潑;由內蘊戲劇情感到外顯肢體能量,一支支看似獨立的小品,串連出一場點題清楚的舞蹈,舞者與舞台物件及舞者彼此的互動,明確傳達出人與時空作用後引發出的各種意涵。

這一晚由莫札特G小調第二十五號交響曲(K.183)打頭陣,卡穆以不疾不徐的清爽速度推展樂句,對瞬間動態變化的掌握相當精采,表情則比較暗鬱,十足呈現作曲家當時浪漫、苦惱的心境。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