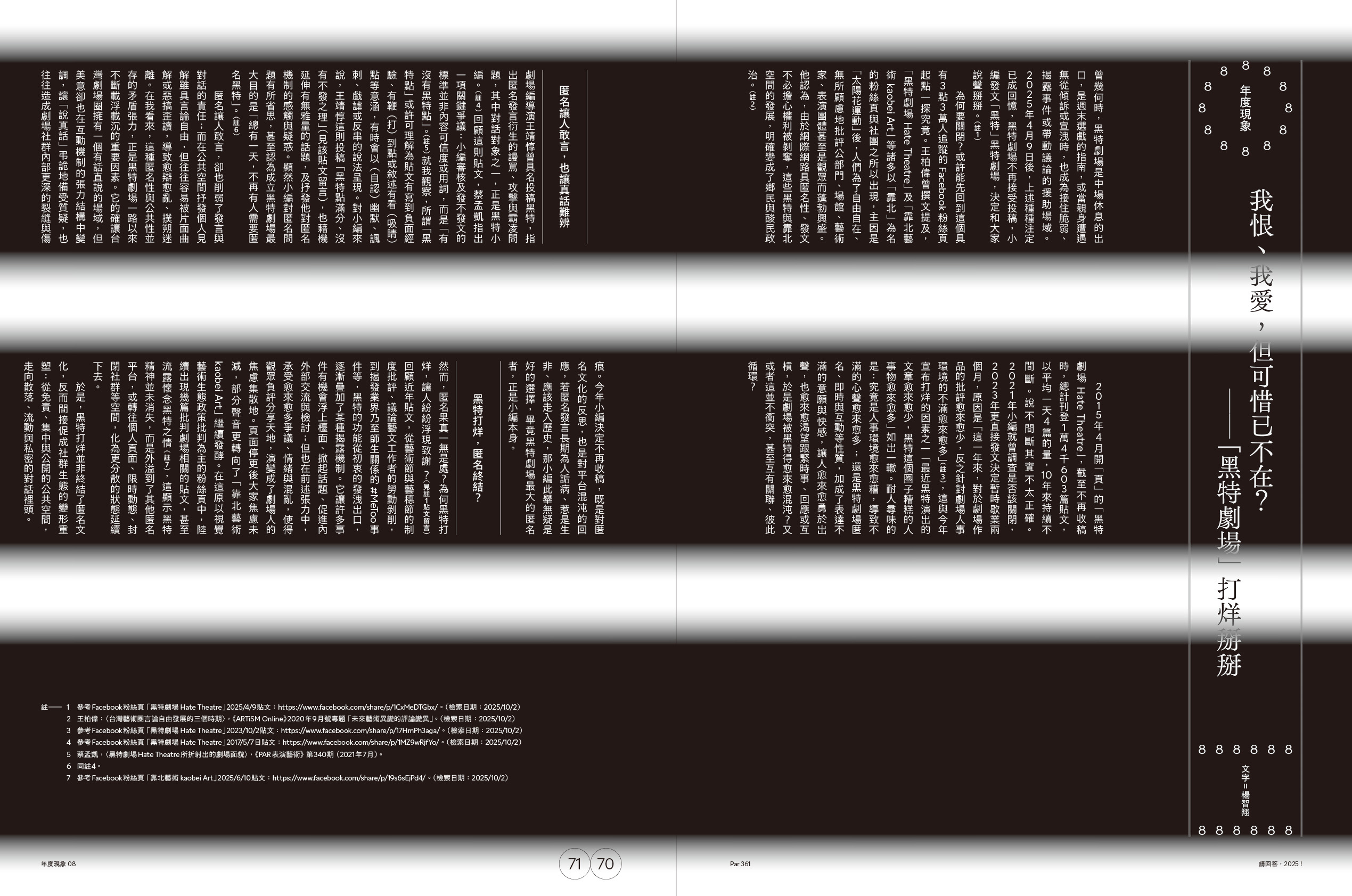音樂劇逐漸在台灣嶄露頭角,無論是演出數量、製作品質、觀眾培養等方面,都成為表演藝術圈不可忽略的類型。其中兩部爆紅作品《勸世三姊妹》、影集式音樂劇《SC驚釀小酒館》(後簡稱《小酒館》)更創下台灣劇場前無古人的紀錄,數次巡演都在開賣時迅速完售,並成功吸引大量新觀眾首度踏入劇場。
兩部作品更體現了台灣劇場的不同製作體系與生態。《勸世三姊妹》來自音樂劇團「躍演」,但獲得IP開發公司「大慕可可」支持,構成台灣少見的新商業劇場規格。而《小酒館》是從製作公司「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啟動,分別邀請導演高天恆與創作、設計團隊合作,並有百萬訂閱YouTuber「欸你這週要幹嘛」跨界演出,打造製作、行銷為起點的創作模式。
劇團與製作公司如何面對觀眾的需求?是否擁有截然不同的規劃方法與思維?又如何在(我們所期待的)劇場產業與商業模式裡頭,找尋藝術與票房間的平衡?因此,我們邀請到躍演藝術總監曾慧誠、團長侯淙仁,與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兩位共同創辦人孫明恩、陳宣,展開一場不同切入角度的對話。
主持:白斐嵐
與談人:曾慧誠、侯淙仁、孫明恩、陳宣
時間:2024/10/17 10:00
地點:二條通劇匯
Q:躍演是從劇團發起創作,這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劇場模式;那麼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後簡稱五口)以製作公司來策動演出,是否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背景?以及這兩者之間可能有怎樣的差異?
孫明恩(下文簡稱孫):我們一開始就以公司立案,主要是我們4位合夥人是表演藝術研究所行銷產業組的同學,專長都是製作或行銷類,所以五口並沒有常駐的核心藝術家。我們那時候觀察到整個環境已經有很多劇團、很多作品,相對缺乏專業分工底下的行銷、製作人才,或是以製作公司為主體的型態,這好像是我們可以切入市場的管道。
因應政府政策、或體制,其實比較難讓營利公司在劇場環境下生存,當時也有一些前輩會勸我們要成立劇團、或是非營利組織,至少可能在場地方面拿到優惠。不可否認的是,現在還是有些場地認定我們是營利公司,所以提供商業價格。我覺得有趣也可以理解,畢竟公司法第一條就講,我們是以營利為目的所設立——而這也是對我們對「音樂劇」的期待,或是說五口一直選擇做音樂劇的很大目的,就是相信也期待這個劇種的娛樂體驗是有營利可能的,也可以讓整個生態往更健康的商業模式邁進。
侯淙仁(下文簡稱侯):公司的營業項目跟執行層面跟劇團不太一樣。簡單來講,我覺得這兩個是不一樣的體系,劇團能夠獲利的時程會拉比較長,也可能比較辛苦,但通常成立公司就是想要更快獲利,並且賺錢。
曾慧誠(下文簡稱曾):躍演做戲到後來,是被我們之前的會計師追著整理財務的——從一開始不開發票到建議開發票,又從開發票到繳稅,會計師認為我們已經長到一個狀態,就應該進入這個規則裡面。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發現:以「非營利」的概念在這個產業中生存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從寫企劃給政府單位申請補助來看,經費表一定要達到收支平衡,但裡面卻連個服務費相關的收入都不能列入;所有的工作夥伴們都說要賺錢、要存錢,可是母體的概念是「不要賺錢」。所以經營劇團與公司的切入概念其實完全不同,我發現必須轉換頭腦,這也是為什麼當初會找Ren(侯淙仁)進場的最大原因——自己作為創作者的頭腦其實很難去看到不一樣的位置。所以,公司與劇團、營利與非營利,我覺得是概念問題。

Q:開啟一個製作時,你們最看重的是什麼?並且如何找到與觀眾溝通的方式?
孫:五口在每個製作開始時都會思考,我們的角色在這個產業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製作。所以在初期,其實找了很多影視製作公司諮詢開案的流程,像是瀚草、大慕。另外,因為我們沒有核心藝術家,所以每個作品都是指定命題,我們帶著已經想好的骨架、需求去找編劇,這也是我們還在磨合的部分,對編劇來講,指定命題也是辛苦的,而這就是製作公司出發、或是藝術家本身出發有的不同優缺點。
流程上,會有個開案會議。同時我們現在開始導入內容開發會議,在會議中把過去一季看到不錯的題材、或作品彼此分享,然後挑選幾個作品進入下一階段,開始有初步的規劃與想像,包含這個作品能不能落地,以及預期規模等。討論後會選擇一、兩個有機會做的,再進到財務面評估,比如規模要做到多大、或是觀眾數要多少、成本是多少、可以達到的預期效益。接下來,我們現在會想辦法讓評測的階段多一點,比如說開案時就開始在做市場的前調,以我們最近開發的《三個不結婚的女人》,就是透過漫畫家的觀眾輪廓、社群數據去做檢測,同時也找尋投資方,如果有足夠的投資人對這個作品在初期就有意願投入,也是我們的市場驗證。
然後才會進到讀劇、Show case等,我們想辦法讓這個內容開發的過程盡可能多一些階段。我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們的容錯率可以愈來愈高——可以同時開很多個劇本、或是很多個主題,但不一定每個都要走到最後。我覺得以前的狀態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大的資本,所以每個作品只許成功,沒有失敗的餘地,但其實很多作品做到一個階段後,就知道不大適合,還是得硬著頭皮走下去。

曾:其實專業經理人進場才一年多,躍演還是比較以我為出發的狀態,因此我很難講開案這件事。
現在這個階段,有很多人希望跟我們合作內容開發,我所考量的第一個是「有沒有興趣」,第二個是「我到底想要說什麼」。我可能切入的狀態不是會不會賣、到底要跟誰溝通,這件事情比較沒有在我的頭腦裡頭,而是這個故事本身有沒有讓我感動,才會讓它成為躍演的作品。我確實是以藝術家的頭腦在運作這件事,只不過我的創作養成背景剛好都在商業環境裡,對我來講,「故事要跟觀眾溝通」是基本原則。
我們其實很簡單,我跟他(侯淙仁)說要做這個,然後他就問我需要多少演員,我說個數字,他可能就會說,沒有,就6個演員。因為演員數量其實就是規模的重要根據,如果我夠愛這個作品就會想辦法在這個規模裡完成。

侯:我們應該盡量幫助藝術,而不是限制藝術,當然還是有實際考量。當他(曾慧誠)點頭說要做,基本上我們不大會說NO,只有在數字上面會控制。藝術是他負責,他有信心,那我們就來設定一些目標,還有籌一些資金。
曾:我喜歡這樣子的來回,因為我並不把它當作限制,而把它當作好玩的、有挑戰的事。
孫:製作公司的好處是可以因應每個作品去尋找適合這個作品的藝術家、或是設計團隊;但壞處就是很多作品都要重新磨合。
Q:躍演跟五口都有很多跨界製作的經驗,那麼劇場觀眾跟其他領域的觀眾有什麼不一樣的思維?跨界的時候要怎麼照顧到原本的劇場觀眾,以及想要拓展怎樣的觀眾群?
陳宣(下文簡稱陳):我們比較擅長20到35歲這個區間的觀眾,甚至是可能是沒有進過劇場的觀眾,所以題材上會盡量貼近這個族群。如何獲知我們的受眾類型,是我們在成立初期,就在Instagram上成立「走阿一起去看戲(@letsgo_theatre)」這個自媒體的原因,藉由這個自媒體才更清楚我們的受眾樣貌,也逐漸讓他們成為我們要培養的觀眾。
以《小酒館》來說,幾乎都是很新、很新的觀眾,甚至沒有來過劇場,所以一開始必須給予他們演前須知,反而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包含來劇場要做什麼、單號與雙號座位的差異等。對我們來說,似乎又賦予了藝術教育的層面。特別是《小酒館》首演時又還是疫情時期,就有更多規範得遵守與規劃。

孫:大量的新觀眾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這也是透過過去在行銷的經驗告訴我們,台灣音樂劇觀眾的天花板其實比想像中低很多,觀察下來大概就是一、兩千人左右,是真的很核心的觀眾——只要推出有代表性、或有一定標誌性作品,大概就是這個觀眾數量。所以《小酒館》的作品規模,勢必得依靠「跨界」。
當然我們在挑選跨界演員,除了有潛力、又願意做這件事情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加入整個訓練的過程。「跨界」這件事情在台灣劇場,一直有人在做,也不是新鮮事,但有時候反而讓作品被打了很多折、或者是實際留下來的觀眾數有限,多半是一次性的,所以《小酒館》就想辦法讓「跨界」這件事情除是票房助力,也確實能夠真的為音樂劇產業留下一些新的觀眾,包含為什麼要設定成影集,就是希望累積消費,然後養成習慣。
演後問卷收集回來之後,確實有40%的觀眾是第一次進到台灣劇場,這個比例真的蠻高的。那麼怎麼去兼顧這麼多的不同觀眾,我覺得還是回到合作的藝術家們——我們就有個共識,就是五口努力把觀眾帶進來,但創作、設計團隊努力把觀眾留下來。觀眾很難因為跨界的演員而留在劇場,以《小酒館》來講,他們更可能因為音樂劇演員顏顏(顏辰歡)、周家寬等,或是燈光、舞台、音響的體驗而留下。透過跨界演員進來的觀眾,可能以為他們是來看粉絲見面會,但音樂劇的精緻可能超越過往經驗,才有機會讓這些人發現,原來音樂劇可以是過去習慣的娛樂體驗之外的新選擇。

曾:對於跨界本身,我有兩個不一樣的經驗。
一個是創作上的跨界,像是做「康士坦的變化球」演唱會,我知道不是劇場,也不會想要它變成劇場。不是把它變成我習慣的樣貌,但是我們習慣的樣貌可以在既定的東西上,給予一些不一樣的體驗。我覺得做跨界最有趣的是,一直被不一樣的東西刺激。要看到別人的優點,才是跨界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自己作品找跨界的人進來。幾年下來,我覺得「沒有加分」——可能是創作者的頭腦,永遠看的都是作品。
跨界演員確實帶了觀眾進場,我覺得沒有不好,但能夠帶進的觀眾量其實有限,因為他們的觀眾沒有習慣看他們做這件事。更進一步思考的是,這個跨界演員是否願意陪我往下走。我認為,澎哥(澎恰恰)參與《麗晶卡拉OK的最後一夜》是比較成功的案例,因為他很願意為台上的東西付出,所以當他沒辦法演出時,就無法重演,沒有另一個人可以吃下這個角色;就算找到跟澎哥類似背景的藝人,我也不覺得他會願意做。
以我在國外看演出的體驗來看,作品還是要有核心重量。我看過幾個百老匯製作人談他們的作品時,都有強烈的世代關懷,就算是商業製作,還是會思考有沒有辦法跟這個世代的人產生共鳴。劇場的力量在說故事,不在於聲光效果,因為聲光效果在別的地方都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

侯:跨界的感受應該是我最深了,因為我真的跨到音樂劇圈。(全場笑)
我用自己比較熟悉的樂團來說,一個獨立樂團只要5、6個人,加上製作人跟經紀人,就可以出去演出。但音樂劇真的很特別,如此龐大的團隊,而大家都希望在很辛苦的環境下找到一條路——一個是靈魂上的自我療癒,另外一個就是實際生活上的改善。會加入音樂劇圈,最大的目標是想要改善音樂劇圈的人的生活品質。我從音樂圈出身,就算是很厲害的專業作詞、作曲,可能一年寫數十首歌才有可能中個兩首,然後獲得版稅——但一首歌平均下來,一個月可能才收到千餘元。但我沒想到音樂劇圈的人,真的更讓我嚇到,怎麼有一群人可以熱血到義無反顧,甚至還有點佛心。
我後來發覺這跟市場規模有關,沒辦法與東京、首爾相比;另一個是相較於Live House,音樂劇可使用的場館數量也少了許多,檔期就會一直卡住。我的觀察是,台灣劇場主要獲利還是在台灣,但是台灣市場實在撐不起來,真正的問題好像是台灣沒有一個模組可以支撐,讓這些想跨界的人進來,或是我們跨出去。《勸世三姊妹》是比較好的案例,不是因為票房,而是這樣的故事搭配這樣的歌曲、搭配這樣的演員,有轉IP的機會。假設拍成影集上OTT平台,版權就可以慢慢cover劇團的營運,可以很認真去想下一個案子。
討論到製作層面,很實際,包含錢哪裡來、怎麼賺錢——這就是劇場跟公司不一樣的地方,如果要談理想,大家可以一直談下去,等到我們都退休、談到老,可是沒有辦法改善大家的生活品質。
我想的是,一個作品最難的還是在他(曾慧誠)身上,不是說找錢不難,只是說如果沒有啟動資金,他滿腦子的熱血會被「沒有錢」去割捨、割捨、割捨,形成惡性循環——我很想要做一件事,但是做不到,然後過程中還都賺不到錢。

孫:其實跨界真的很難找到合適人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分享《小酒館》經驗,永遠都不會告訴大家「找跨界就會成功」。我覺得就是回應剛剛慧誠講到,跨界演員願不願意跟著團隊一起走下去,而《小酒館》就是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碰到了疫情、碰到了一組對台灣音樂劇有興趣的YouTuber「欸你這週要幹嘛」,流量高、粉絲黏著度也高,然後他們就是在頻道裡面會一直唱歌的YouTuber。他們在剛開始就打算認真做,再加上疫情期間沒辦法離開台灣,就陪著我們,上了3個月的課——每個禮拜上一堂戲劇課與一堂歌唱課。但是對於更多藝人、或是YouTuber,上小巨蛋開演唱會、衝更高訂閱量,都比演音樂劇重要。
回到最一開始,我們覺得內容還是最重要的,還有,劇場會暴露大家的真實面貌。其實跨界就是兩面刃,要不是是把作品給殺死,要不是真的會有新的觀眾有機會留下來。所以,我們也把「內容開發」看得愈來愈重要,主要是因為我們做完《小酒館》第一集後,發現作品還是得回到內容本身,而不只是「跨界」——當內容不夠強大、不夠紮實,其實一個作品的生命週期還是很有限,即便有其他的票房量能,或其他的亮點,在一個地方演完就差不多了。
現在看《勸世三姊妹》是一整台音樂劇演員很羨慕,也覺得這是身為製作人最放心的狀態,這是我們的理想。但在此之前,我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音樂劇是台灣大眾的娛樂選項之一——之前,我們還是需要為市場開拓做些選擇。

Q:最後想要問是,一個作品要怎麼樣吸引更多觀眾進來?
陳:我剛從南京回來,剛好可以分享個有趣的事情。南京今年有個目標,要完成100間小劇場——改造也行,建造也行,所有有一部分是把比較小廳的電影院,改造成小劇場,再評估電影院是否可以做額外的燈桿等,讓那個電影院同時演電影、也可以同時有劇場演出。
我認為,他們不是把電影院當成競爭對象,而是一起合作,讓市場變大,當然這跟國家的經濟體系有點關係,所以要怎麼樣突破、讓更多觀眾願意進劇場看戲,他們先用這個辦法試試看。
孫:我們還是期待多做一點觀眾開發,市場需要先被擴大、或是真的有市場存在。我覺得市場最直接就是有沒有供需,而我們現在有「供」,但「需」目前看起來比較少。所以,在整個製作的初期開始思考需求在哪裡、觀眾在哪裡、觀眾為什麼需要來看這個作品,或者是剛剛提到的各種財務面的評估——如果這個作品要賣3萬張票,那這3萬人到底在哪裡、我們要跟誰說故事。
每個作品都有它的票房引擎,不一定是演員,也可能是劇本本身、可能是IP本身,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前期會去思考的。過去做劇場時,比較容易想的是作品本身,不會去想到這些層面。以《小酒館》來說,我們知道這群YouTuber的觀眾會想要看這群人的實體演出,這同時也加入一些我們對於市場的觀察,比如說,有一些歌手超級有名,但他的粉絲沒有在他身上花錢的習慣;或是傳統電視上的藝人,因為他的觀眾有很多免費的觀看選擇,所以也不會想花錢買票,這些都跟消費習慣有關。
侯:觀眾,真的好難回答,
我覺得「票價」是個可以討論的事情。現在劇場均價大概是1,200元到1,800元,因此我們到底能給他們什麼,讓他們覺得超值的。我的直覺是,劇場之所以那麼辛苦,可能觀眾很大部分時間是有點小失望的,走出劇場之後,覺得那還不如去看電影,而看電影才300塊左右,還是幾億美金的預算去做的。最近劇場很多演出都800元起跳了,那觀眾一定會有期待。假設我們去聽音樂祭,就算那個人、那個團沒聽過,也可能會被音樂吸住,變成粉絲,這兩者對接的時程很短,一個團的一場表演大概40分鐘就可以搞定;但劇場還有中場休息,動輒要兩、三個小時,似乎那個CP值很難衡量。
但是我們又不能訂低票價,因為劇場就不是低成本,一旦拉到那個成本之後,勢必就是要從票價裡面去找獲利空間,我現在還在拿捏,還在想辦法。
曾:作品是最重要的,要學會用作品跟觀眾溝通。現在有太多娛樂,憑什麼觀眾要來劇場看演出。我當然知道創作很辛苦,可是我們若是身為觀眾坐在那邊,到底會想看到什麼,怎樣才能留下觀眾。
我可能回頭問自己,我為什麼喜歡做劇場?我為什麼喜歡進劇場?對,就是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讓我想要進去,那我能不能提供給第一次到劇場的人?如果可以,那也許有機會可以留住他。我認真覺得,沒有好作品留不住人的。
其實《勸世三姊妹》最讓我感到高興的,是裡面沒有任何藝人,因為它似乎展現了劇場的本質,就是這些人很有功夫,劇場很會說故事,我們可以給觀眾的是很不一樣的體驗。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那可能劇場不是你喜歡的,而不是因為來劇場看明星。《勸世三姊妹》給我最大的影響,是這部作品好像做到了什麼,讓很多從來都不進劇場的人,願意來看這些他們都不認識的人做的表演。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到,那劇場的大家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躍演VMTheatre Company
創立於2007年,致力於發展中文音樂劇創作與演出。藝術總監曾慧誠擁有紐約大學音樂劇表演碩士學位、美國音樂戲劇學院(AMDA)音樂劇表演文憑,擔任多部音樂劇、歌仔戲等導演。現任團長侯淙仁來自音樂圈,近年加入劇團,呈現劇團不同分工系統。2021-2024連續4年獲選為國藝會TAIWAN TOP演藝團隊。近年作品有《勸世三姊妹》、《釧兒》等。
五口創意有限公司
成立於2017年,共同創辦人孫明恩、施淳耀、陳宣、陳政達以「表演藝術製作與行政統籌」、「劇團營運顧問與品牌行銷策略」、「藝術策展企劃」出發,並以原創音樂劇為主要製作方向,結合各方資源,以製作人的思維推動台灣表演藝術市場。近年作品有影集式音樂劇《SC驚釀小酒館》、《妳的側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