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搜尋
-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演員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演員張芳瑜 相信直覺的聲音
時間倒轉回到2007年。 那年,張芳瑜是「嵐創作體」(註)全本搬演外百老匯音樂劇《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在台灣常簡稱為《LPC》)其中一名小演員,我是同樣初次登台的鋼琴樂手。我們一同來到聲音指導連芳貝家中上課,張芳瑜唱了劇中一首描述女子等愛心情的〈I Will Be Loved Tonight〉,千迴百轉的旋律線,千絲萬縷的心緒,纏繞著恐懼、期待與自我懷疑,最終堆疊成堅定的信念「我會被愛」。 最後的和弦餘音落定,老師轉頭說:「張芳瑜,你唱歌都沒在想,這樣很好。」 這是稱讚肯定張芳瑜不落入那些細微、糾結的技巧展現,反而毫無後顧之憂,跟著旋律指引的方向,拋出自身與角色、旋律與聲音的情感共鳴。訪問時提起這段往事,她說:「好懷念也好羨慕喔,我現在都想很多耶!」 很難想像「想很多」的張芳瑜是什麼樣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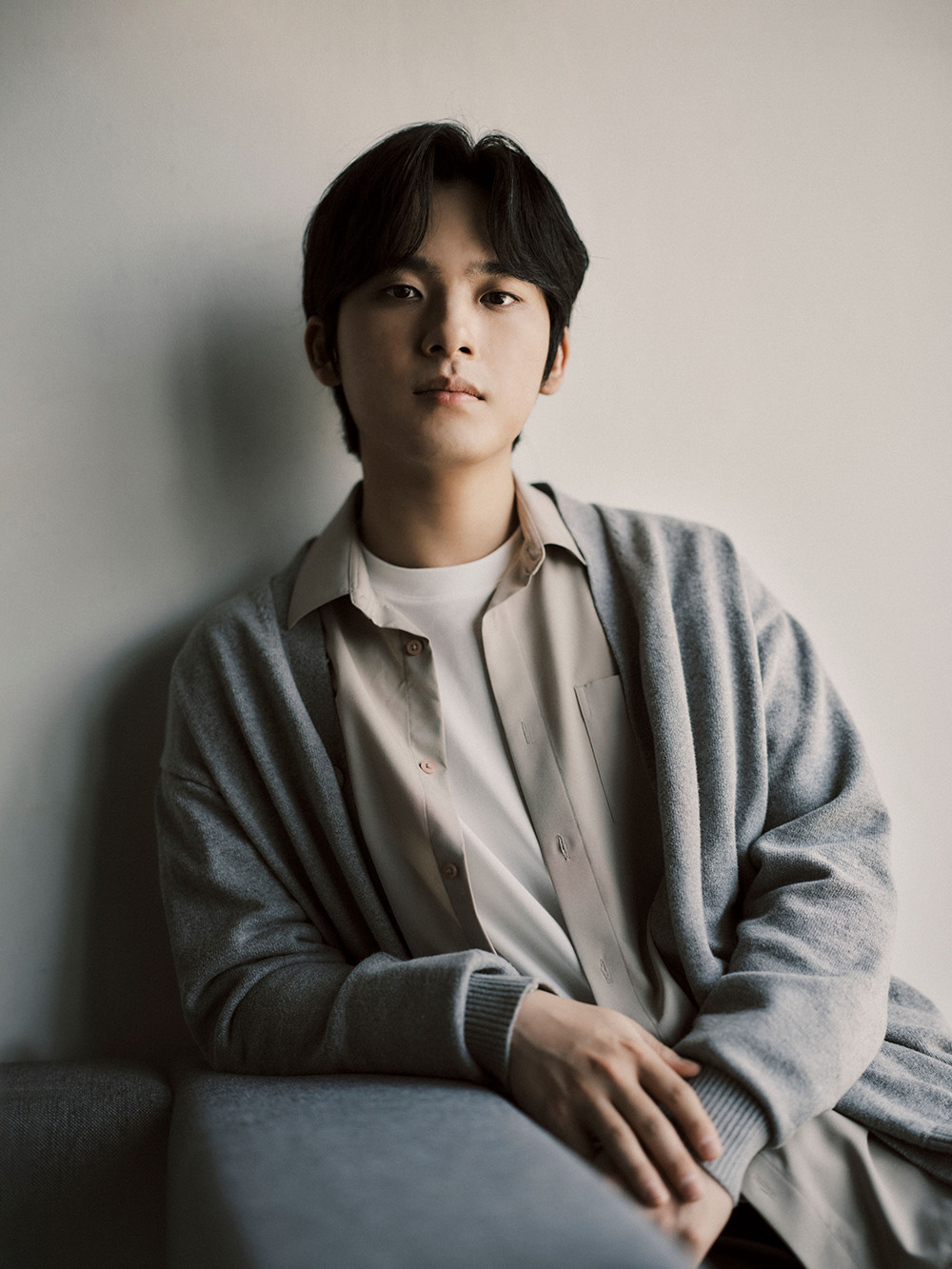 首爾
首爾光環背後的沉重 任奫燦「韓國生活宛如身處地獄」言論引發熱議
鋼琴家任奫燦(Yunchan Lim)在韓國國內的媒體曝光與討論熱度持續升溫。除了今年4月以獨奏專輯《蕭邦練習曲》(Chopin tudes)一舉拿下英國 BBC 音樂雜誌大獎(BBC Music Magazine Awards)年度新人、最佳專輯及最佳器樂演奏獎項,7月又與恩師孫旻秀(Minsoo Sohn)回國舉辦雙鋼琴演奏會,獲得高度矚目。令人意外的是,任奫燦在8月接受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訪問時的發言,兩個月後被轉譯回韓國,引發震撼。 任奫燦在訪談中坦言,自己並不懷念韓國的生活,如今僅在有演出安排時短暫停留。他進一步表示:「在韓國度過的最後求學時光,痛苦到難以承受。那感覺就像身處地獄,甚至曾想過結束生命。」他也直言不諱地剖析韓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指出韓國地狹人稠,人際競爭異常激烈,「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有時甚至不惜傷害他人。」並回憶17歲在鋼琴界嶄露頭角時,曾遭遇政商界的不當干預,「那些經歷使我深感悲傷。」 任奫燦的音樂成就堪稱耀眼。7歲學琴,以第一名畢業於藝術名校「藝苑中學」(Yewon School),隨後進入韓國藝術綜合學校附設英才教育院,師從孫旻秀,迎來音樂生涯的轉捩點。2022 年,年僅18歲的他奪得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Van Clibur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冠軍,成為史上最年輕得主。隔年孫旻秀轉任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教授,任奫燦亦隨之赴美深造。他形容孫旻秀是「我的引路者與救贖者」,足見師生情誼深厚。
-
 戲劇
戲劇藝術生產機制下的權力思辨
在劇場,勞動是隱形的。 當觀眾坐定、燈光亮起,眼前呈現的是一場精美的舞台成品。但在幕後,是一群黑衣人默默支撐這個系統運轉,從卸車、搬運、裝台、換景到拆台、撤場,這些隱身黑暗的勞動身體,共同構成藝術生產機制。 法國馬戲導演克萊蒙.達贊(Clment Dazin)的《勞動狂想》,選擇從這道縫隙切入,將後台推到前台,把衛武營國際藝術文化中心的卸貨口變成舞台,讓觀眾直視藝術場域本身就是一個勞動現場。 反思勞動的起點 達贊的創作取徑,與他早年的職場經驗緊密相關。在成為馬戲導演之前,他曾在客服與歐洲直升機公司(Eurocopter)任職,同時撰寫一篇關於「職場關係中的心理情感維度」的碩士論文。 「那時我訪談了公司很多同事,發現制度如何滲入身體。你會看到肩膀下垂、呼吸變淺、背部彎曲那是壓力留下的形狀。」他回憶說。 在他看來,現代企業的體制往往以「開發潛能」之名,實則削弱了個體的力量。這種對身體與意志的馴化,也延伸成他後來對舞台勞動的反思。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與時俱進、實踐永續 創造「明日的遺產」
2025世界劇場設計展(World Stage Design,WSD 2025)於10月18日至25日在中東文化之都沙迦(Sharjah)拉開帷幕。本屆展覽不僅是4年一度的全球劇場盛事,更是一場對劇場設計語言、科技趨勢與永續責任的深度審視。 趁此機會,本刊特地訪問到2025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專案總監賈姬.喬治(Jacqui Georg)。在訪問中,她說明了本屆WSD部分獎項調整的考量,也分享了在中東氣候下推動永續實踐的挑戰與承諾,以及如何透過與 Goumbook 合作種植紅樹林,將碳排放抵銷納入全球活動規劃中。面對強大的AI數位浪潮,她表示「當前表演設計界的科技變化既是禮物,也是挑戰。」而今年WSD的主題「明日的遺產」,「正是對這種張力的回應。」
-
 東京
東京紀念千住宿開宿400周年 「千住雙關語音樂祭」邀1010人共演
由東京都、東京藝術大學與足立區等單位共同主辦的城市藝術計畫「Art Access Adachi:音樂城市千住的緣」(音まち千住の縁),為紀念千住宿開宿(註)400周年,特別於10月12日「千住雙關語音樂祭」(千住だじゃれ音楽祭)舉辦大規模演出「來啦!千住的1010人」(キタ!千住の1010人)。這場城市參與型演出集結了1010名演奏者,以作曲家野村誠發起的創作計畫「雙關語音樂(だじゃれ音楽)」為核心,展現出幽默與自由並存的音樂風貌。 「雙關語音樂」是野村誠長年推動的社會性藝術實踐計畫,以語音相似但意義不同的詞語為起點,將日常生活談話中的雙關語轉化為音樂創作。而「千住雙關語音樂祭」是長年由居民與藝術家共同參與構成,從日常的文字遊戲中尋找聲音的靈感,進而開發出全新的作曲方法,探索語言、音樂與社群之間的連結。 2025年適逢該計畫設立15周年與千住宿400周年,這場跨越世代與國界的音樂節邀請了國際與本地藝術家共同演出,包括泰國音樂學者Anant Narkkong、馬來西亞聲音藝術家黃楚原(Ng Chor Guan)與印尼作曲家Memet Chairul Slamet。他們與日本專業樂手、在地學校樂團與市民一同登台。從跳繩、貝殼、手機、飯鍋到薩克斯風,幾乎任何能發出聲音的物品都成了樂器,創造出屬於「千住」這個區域的獨特交響。 野村誠表示:「我尊敬的作曲家們這次為1010人的演出創作的新樂曲,真的是一首非常開放、表現自由的作品,能夠直接打動觀眾的身心。這次的核心主題是『共存』。正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充滿衝突與對立的時代,所以才要舉行一場沒有任何人會被排除,『什麼都可以』的合奏演出。這並不代表我們需要對齊每個人的步伐,而是希望讓大家能感受到,當這麼多不同的人們聚在一起時會發生多麽美好的聲響。」 更多資訊請見官方網站。 註:「千住宿」是舊日光街道與奧州街道上、從日本橋出發後的第一個宿場町,也是江戶時代「江戶四宿」之一。如今的位置大致對應東京都足立區與荒川區南千住一帶。
-
 人間父子
人間父子人生哪來那麼多架好吵?
成年以後能吵的事?大概只剩開車 真:今天要談吵架這個主題,以我的立場好像的確可以這麼說男性真的不太會吵架,或者是一直想要避免爭吵。像是如果問我會在什麼場合跟人發生爭執?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過了。真的要講,可能就是開車的時候吧? 謙:你開車的時候真的特別火爆,嘴裡會一直碎碎念。不過這樣說起來,我也是啦。 真:對啊,不是只有我,多數人也是這樣啊。我有一次搭計程車,那個司機看到有人亂開車,就會舉起手假裝是一把槍,然後咻咻咻射那些亂開車的人。我坐在後面,最後就說:「司機先生,今天上路只是開個車,好多人被你射死了欸。」(笑)開車真的好難控制情緒喔。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吵架的意義是什麼?人在情緒當下,無法好好溝通啊,等於吵架只是一個斷裂而已,人跟人無法真的交換什麼新的東西出來,結束以後也不會有什麼新發現。 謙:我常常覺得,爭吵好像就是有一方放棄聆聽的過程。情緒很重的時候,兩個人常常已經不知道話講到哪裡去了,可能原先討論的話題也不存在了。會不會是因為成年以後就更多明白這件事情,才愈來愈不想吵、因而活得愈來愈壓抑呢? 真:所以說,到後來,如果你媽要跟我吵,我就會直接跑去看書。 謙:這就是為什麼,你這幾年可以一直看那麼多書(笑)。 真:不是啦,追根究柢,我覺得學生時期就應該要明白,吵架無法真正解決什麼事情,甚至無法好好釋放情緒啊。先不談我自己,小時候我經常看到鄰居吵架的畫面,非常驚險,夫妻吵到一半,會有人拿著柴刀直接劈出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對夫妻吵到一人拿刀追另一人在路上跑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現在當然不可能吵成這樣。現代人的吵架嘛?記得有次我目睹兩個人的爭吵狀態,哇賽那個畫面之激烈,其中一方盤點誰去喜宴錢包不夠自己墊了多少,另外一方又開始數自己也做了哪些事情。聽到最後,我覺得那兩個人根本不是在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從台北到大邱 讓舞蹈DNA在亞洲牽引、綻放
繼今年8月中旬於臺北中山堂舉辦的「2025 Dance Now Asia舞蹈藝術節」(下簡稱DNA舞蹈節)推出「亞洲青年舞蹈創作演出Showcase」、「國際身體工作坊呈現」及「國際舞蹈論壇」後,DNA舞蹈節更是首度插旗海外,緊接著在韓國大邱舉辦「2025 Dance Now Asia in Daegu」舞蹈藝術節。期間除演出本年度主辦單位「大邱市立舞團」(Daegu City Dance Company)與韓國編舞家的作品外,本藝術節共同發起╱策畫團隊「MeimageDance」與「日本東京藝術」帶去的來自台灣與日本、共計10支舞作,也在大邱文化藝術中心(Daegu Culture and Arts Center)演出,展現出亞洲當代舞蹈豐富且多元的樣貌。
-
 新銳藝評 Review
新銳藝評 Review馬/戲/曲:放下「本質」的追尋,看見「現在」的身體
合作社於2025戲曲夢工場《前方有三岔路口》邀集了音樂劇、馬戲、戲曲及現代戲劇演員,「從表演的『技術』出發」(註1),探索不同劇種間流動的共性與差異。導演吳子敬表示,合作社近來想探索的是:「馬戲除了『招』還有什麼?」(註2)作為一個戲曲背景的觀眾,我看到的更是:戲曲除了「曲」還有什麼?自王國維定義「戲曲」以來,「合歌舞以演一事」(註3)似乎成了戲曲的基本定義之一,然而當我們關注在「唱曲」(亦即寫定的或口傳的文學文本)時,是否遺漏了其他部分?因此,本劇以「武丑」作代表人物、京劇《三岔口》為改編文本,便企圖探討戲曲中較被忽視之要素。
-
 舞蹈
舞蹈策展如點菜 端上一席即興盛宴!
邁入第15年的「國際愛跳舞即興節」從「i.dance Taipei」到改名為「i.dance Taiwan」(後簡稱idt),見證了台灣接觸即興舞蹈社群的誕生、茁壯與變形。今年,創辦人古名伸交棒給中生代舞蹈家余彥芳,不僅象徵著世代傳承與觀點更新,亦是尋找接觸即興下一世代語言的時刻。對余彥芳而言,這是一場充滿珍惜與細膩的延續。「我本來以為會和古老師有些拉扯,沒想到順利到難以想像。」她笑著說。 余彥芳與古名伸的淵源可追溯至她的大學時代,從學生到舞團成員,之後離開成為獨立創作者。這段長達20年的歲月,給予余彥芳開闊視野的養分,也奠定回望的基礎。今年她以策展人身分回歸,以「點菜」作為策展隱喻,邀請所有即興的愛好者共赴一場「身體的盛宴」。
-
 北京
北京原創民族歌劇《紅高粱》首演 觀眾反應參差爭議不少
9月27日,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了由中國第1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和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合作的原創民族歌劇《紅高粱》。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是在政策鼓勵下眾多特定目的性的藝術作品之一。《紅高粱》是北京國家大劇院成立以來的第23部原創歌劇製作,事前引發極大關注,首演後亦有不少爭議。 歌劇《紅高粱》由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改編,這部小說曾改編過電影和電視劇,故事內容可謂家喻戶曉,莫言對歌劇版本異常重視,親自參與編劇,且在七易其稿中領悟到歌劇劇本的精髓:「要寫意,寫詩化、詩意的東西。」因此,歌劇中的高粱隱喻著人物命運,隨著氣候和劇情呈現不同的形態,劇詞也從小說家的敘事邏輯,轉向了詩人般的抒情和意境的營造,且借紅高粱「抗旱抗澇、生氣勃勃、充滿野性」的意象,書寫了中國人堅韌的生命力和奮勇抗爭的精神。郭文景則運用了故事發生地山東高密的茂腔、柳腔、山東梆子、山東快書、膠州秧歌、高密民歌等元素,與西方管絃樂隊的音響融合,極力打造歌劇音樂所能展現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兩位創作者都認為歌劇是表達人類情感最有力量的表演藝術形式,在其中植入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更是為中國歌劇的發展添加了動力。 然而,撇開排山倒海但大同小異的新聞報導,《紅高粱》到底能不能算是近年來中國創作的歌劇精品?答案是令人失望的。 從兩種觀眾的反饋,可以對這部歌劇的演出得到具體的印象。一是對歌劇一知半解的觀眾,不是對音樂不那麼悅耳多有微詞,就是對詠歎調毫無記憶感而如坐針氈;歌劇迷觀眾的評價則是南轅北轍,但都注意到歌劇演出的各個層面(音樂、劇詞、歌唱、音響、導演的舞台調度、舞台布景等)。總體而言,這部單分八場不分幕的歌劇在音樂上比劇詞要成功,尤其是合唱的部分,而劇詞的詩意落在詞語的過度重複,如「我去」、「我嫁」等,反成了笑點和出戲點;義大利美聲唱法在中國民族歌劇中的適應性仍然是最大的問題,這是臨場聽覺上最不容易妥協的,歌唱者咬字清不清晰已是最基本的問題;其他如歌唱者的肢體表演、導演的舞台調度和舞美設計的刻板意象等,專業的觀眾都關注到了。可惜的是,至今仍然沒有一篇持客觀立場的專業評論出現,這是中國表演藝術生態裡最大的缺憾。 看待歌劇的成功與否從來就有兩種視角,一是從觀眾,如何得到情緒的感動和情感的轉化;二是從藝術作品,如何讓詞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台北愛樂40年的文化實踐
成立40年的台北愛樂管弦樂團(TPO),以民間力量譜寫台灣交響的新高度。近年來,樂團透過國際巡演與藝術輸出,讓「台灣之聲」在世界舞台上愈發清晰。今年9月,首席弦樂四重奏攜手華洲園布袋戲團登上大阪世博舞台,連續3天上演融合台灣民謠與布袋戲的交響樂《挪吒鬧東海》,以西方古典結構交織在地故事與傳統技藝,吸引數千觀眾駐足讚嘆。演出後,樂團飛抵東京,將台灣民謠與柴科夫斯基第1號絃樂四重奏的感動延伸至海外聽眾心中。 不止於演奏,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更舉辦第4屆「東亞樂派論壇」,推動跨國學術交流與原創創作,累積深厚的文化能量。本專題將從多個角度,帶領讀者走進樂團的國際舞台實踐、跨界創作理念與東亞樂派的學術探索,呈現台北愛樂如何從土地出發,將台灣音樂文化推向世界。
-
 焦點專題 Focus 台灣之聲,跨海綻放
焦點專題 Focus 台灣之聲,跨海綻放台北愛樂首席四重奏的東瀛文化之旅
2025年9月初秋,來自台灣的古典音樂之聲,以室內樂的優雅形式跨越海洋,在日本「大阪・關西世界博覽會」與東京兩地連續帶來了多場精采展演,成功在國際舞台上留下鮮明的台灣印記。這股力量,便是由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首席弦樂四重奏團所組成,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前院長蘇顯達領軍,攜手第二小提琴林天吉、中提琴朱育佑、大提琴孫韻淳,以及打擊樂首席陳思廷,肩負起文化交流的重任。這次演出不僅展現了台灣古典音樂的精湛技藝,更透過東西方元素的巧妙融合,訴說著在地的情懷與故事。
-
 焦點專題 Focus 第4屆東亞樂派論壇
焦點專題 Focus 第4屆東亞樂派論壇追尋根源、重塑記憶與文化主體性的三重奏
由台北愛樂管弦樂團主辦、聚焦東亞文化傳承與現代發展的「東亞樂派論壇」,於2025年9月9日在東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盛大舉行,邀請了日本、台灣3位重量級文化領袖,以跨越千年歷史與多學科的視野,剖析東亞三地如何在儒家文化基底與全球化浪潮下,形塑其獨特的藝術與文化面貌。 3位講者分別是日本薩摩琵琶演奏大師塩高和之、台語雅歌作詞作曲家陳維斌,以及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創辦人賴文福。他們從古老的樂器、瀕危的語言,到現代的古典樂發展,展開了一場關於文化記憶與自我表述的深刻對談。 第一講:琵琶的千年傳承從皇室雅樂到國民敘事詩 塩高和之一開場便透露了傳統藝術家所面臨的實際挑戰。他指著體積龐大的琵琶幽默地說:「為了要運這把琵琶,都要花兩倍的價錢。」 這種不易搬運的「現代日本琵琶」,承載了日本音樂上千年的聲音史詩。 他首先追溯了日本音樂的源頭中國文化的輸入。早從飛鳥、奈良時代(西元6到8世紀)起,包括新羅、百濟、高麗、林邑等地的樂舞便已傳入日本。尤以雅樂的傳入為關鍵。西元701年雅樂寮(歌舞司)的設立,被譽為當時的「國際音樂大學」,女性學員比例相當高。他強調,雅樂琵琶能夠千年形制不變,持續流傳至今,在世界範圍內極為罕見。這穩定性的關鍵,在於天皇制度:「天皇周邊的高階層人士會去學習雅樂、研究雅樂、欣賞雅樂。」 然而,琵琶的歷史在鎌倉時代(12世紀)迎來了革命性的轉捩點。隨著《平家物語》的誕生,日本音樂出現了第一個完全本土化的作品。《平家物語》的傳播形式,不再是純粹的書寫,而是透過彈唱,讓琵琶藝術從原本的皇家專屬,變為「一般國民可以聽到的藝術」。琵琶因此小型化,更易於攜帶。塩高和之總結,鎌倉時代是包括茶道、花道在內,「現代的日本文化的起點」。 雖然江戶時代琵琶一度因琉球傳入的三味線普及而衰落,但在江戶末期,薩摩地區(鹿兒島)誕生了新的薩摩琵琶彈唱形式,強調邊彈邊唱,將想要講述的故事表現出來。 進入現代,琵琶在戰後與軍國主義的聯想一度使其衰退,但在1960年代末,鶴田錦史等大師開始將琵琶從歌唱伴奏轉變為純樂器演奏,並與武滿徹合作,走向國際。塩高和之為第一講做出深刻的結語:「僅模仿師父的技藝
-
 焦點專題 Focus 演出之外
焦點專題 Focus 演出之外Tech World 科技下的台灣故事
在2025年大阪.關西世界博覽會中,台灣館以「Tech World」為名,以科技為主軸,向世界展現台灣在科技、文化與生命議題上的思考與能量。這座鄰近西側入口的展館,是整個世博場域中不可忽視的一座獨立館。 Tech World 館的外觀靈感來自台灣山脈的輪廓,採用金屬綠建材折板技術,塑造出山巒起伏的動態效果。白天在光照下閃耀光芒,夜晚則透過室內光線流瀉出山影輪廓。建築採永續理念,是一座在環境與科技對話中落實綠建築理念的典範。館內共有3大劇場與多種展演空間,每7分鐘開放 40 人進入體驗。全館分為歷史、自然、未來3條主題線,不僅呈現台灣的生態、人文、技術,也結合智慧手環互動系統,即時記錄參觀者的心跳、情緒、體驗數據生成專屬的心動曲線。 Tech World 館長邱揮立受訪時提到,館內動線從頭走到底大約需要 35 分鐘,這是特別設計要讓觀眾能完整沉浸於展覽的流程與節奏。
-
 焦點專題 Focus 在樂聲中前行
焦點專題 Focus 在樂聲中前行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日本巡演的文化觀察
走過40年,台北愛樂管弦樂團2025年再次踏上日本舞台,完成大阪與東京巡演。這不只是音樂交流,更是一場民間樂團在資源有限下求新求變的實踐。創辦人賴文福直言:「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在經費方面。」在台灣,音樂人口增加、樂團數量激增,使得資源被稀釋,民間樂團能否在此生態下長期維持藝術水準,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公立樂團不同,沒有政策的保障,也無財團支持。自由自主,代表著彈性,卻也註定艱辛。賴文福說:「最大的困難不在音樂,而在永續,那是我們的挑戰。」這句話道出民間樂團生存的核心矛盾藝術自主性是理想,卻也是壓力。 弦樂四重奏:規模縮小的策略思考 日本巡演採取弦樂四重奏形式,表面看似縮水,實則構思精妙。賴文福說:「大型管絃樂團是一種形式,但我們也需要用更靈活的方式去表達。」這種小規模編制不僅降低經費壓力,也讓樂團在城市與場館間更自由移動,以「累積」取代大團聲量的效應。 大阪演出結束後立刻轉戰東京,賴文福強調:「這樣大家才會知道,有一個台灣樂團持續在日本發展。」民間樂團在國際舞台上的存在感,需要時間、策略與不斷重複的演出。觀眾組成除了台僑,也包括日本聽眾,樂團甚至與日本作曲家合作編曲,並且在當地透過論壇疊加自身的影響力。這種計畫顯示,藝術行銷與文化對話已經成為民間樂團生存的重要手段。 「東亞樂派論壇」文化定位的挑戰 藝術不只是演出,更傳遞思想。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啟動亞洲之窗計畫之後,持續在韓國、台灣與東京等地進行作曲論壇與學術交流,又從2021年逐步發展出「東亞樂派論壇」的架構。賴文福指出:「我們以『東亞樂派』為學術框架,去發展理論與實踐。」這背後隱含兩個衝擊:一是「台灣能否在東亞文化對話中占據凝聚角色?」二是「民間樂團又能否以有限資源持續推動學術與創作?」即便資源有限,愛樂依然在創作上積累成果,不僅展現台灣音樂實力,也試圖打破「旁觀者」的身分,向東亞文化提出主動性的發聲。 布袋戲交響詩:本土化的文化實驗 台北愛樂管弦的布袋戲系列,是最具象徵性的文化實驗。賴文福回憶:「我發展布袋戲交響詩是從台灣元素開始的
-
 戲劇
戲劇戲劇映照出的社會現實,是你我造成的?
在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中,官商、黑白、府會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似乎已是理所當然的現實,對一般民眾而言,即使其中充滿貪腐掠奪分贓的各種可能,只要事不關己,也就任其自生,一旦弊案爆發,一句「代誌就是按呢」,看似了然世道,其實只是犬儒心態。但對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來說,這樣的既存現實,卻可能是難以承受的重,一旦被捲入其中,如何自保、能否自保,便成嚴苛考驗。 故事工廠《一個公務員的意外死亡》,從與民生關係密切,卻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廢棄物處理議題切入,以調查報導的形式再現地方政治生態,選材具社會性意義,也有清楚的視角和敘事策略。 主人翁陳嘉偉中年轉業,投考公職,幾經挫折終於通過,分派故鄉環保機關任職,穩定收入讓家庭生活趨於平穩,罕病幼女的醫療費用也有了著落。只是,面對在地環保廠商污染環境的不法行徑,他基於職責與愛鄉情感,欲施以重罰,卻遭到上級、同僚與廠商聯手阻擋,想要做「吹哨者」,揭發官商勾結黑幕以求自保,竟連妻兒也遭受威脅,被逼到絕境的他,即使無力改變現實,但決心採取行動拯救家人陳嘉偉的「意外」死亡,引來雜誌記者林佩璇的高度興趣,決心深入地方調查事件真相,只是,當她逐漸逼近事實核心,來自雜誌高層的壓力,真相揭露的後果,都讓她不得不重新考慮:「或許真相不一定要大白?」
-
 腦海裡的旋律
腦海裡的旋律有你的大腦,藝術才得以完滿
旅途中在威尼斯停頓,看雙年展(今年是建築展)、訪美麗木橋旁的學院美術館欣賞文藝復興威尼斯畫派名家作品,當然也沒錯過波光粼粼的威尼斯大運河旁的佩姬.古根漢美術館:出身於美國礦業與銀行家族,佩姬在紐約成長,於巴黎養成藝術品味,最後落腳在「亞德里亞海上明珠」威尼斯;她熱愛現代藝術,所收藏的藝術品不論質與量都無人能出其右,在20世紀極受討論也備受尊崇。 一口氣看了許多現代抽象藝術巨人的作品: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馬克.羅斯科(Marks Rothko)、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保羅.克利(Paul Klee)心緒翻攪不已、回憶受到極大擾動,該怎麼形容這種感覺呢?欣賞抽象視覺藝術時,我常覺得,重點不是「看到了什麼」,而是「感受到什麼」: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些作品常會喚起深深埋藏的回憶,有時引發困惑,有時福至心靈,有時浮現的感覺難以言喻,卻抒發胸中一口悶氣。 「沒有觀賞者感知與情感參與的藝術是不完整的」,在現代藝術作品面前,觀賞者和藝術品產生了連綿不絕的對話,有時也會自問自答,這不禁讓我想起對藝術和大腦神經科學同樣在行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艾瑞克.康德爾(Eric Kandel)的文字:「大腦利用多種感官經驗(例如視覺和觸覺)以及情感過程(例如模擬和移情)來處理藝術作品,如何理解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是21世紀腦科學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 康德爾提出現代藝術和「觀賞者份額」(the beholders share)的概念,讓我特別感興趣。他說,一幅畫或一件作品,藝術家做完了不代表真的完成,必須有觀賞者加入自己的感受才能得到圓滿;藝術家創作完畢,接下來要有觀賞者接棒,當觀賞的人投入自己的記憶、情感和人生經驗,才能真正賦予藝術品完整的意義。 這些年有不少大腦科學家進行質性與量性研究,試圖了解人們在觀賞抽象藝術時,大腦中究竟發生哪些變化。《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了一項深入探討人類大腦如何與不同形式的藝術互動,並且建構主觀經驗的研究,十分有趣!在這項研究中,科學家線上訪問30位受試者,讓他們對抽象畫和寫實畫分別做出描述,外加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技術觀察29名受試者觀看同一藝術家所做的抽
-
 新銳藝評 Review
新銳藝評 Review聲音與形體之間的再造風景
雖未曾親眼觀賞過《泥巴》的第一版,但從之前數版《木蘭》、去年的《六部曲》,直至此次新版《泥巴》,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擊樂劇場」系列可說逐步走出一條清晰的創作脈絡;從《六部曲》至此次重返劇場,最大的驚喜在於舞台構思與整體調度的進化,也展現了團隊在形式與敘事上的持續實驗。 舞台設計甚具巧思。懸掛式樂器的配置不僅讓換場流暢、節奏緊湊,也形塑了舞台的立體感,使觀眾的視覺經驗從平面延展為層次分明的景深構圖。垂吊的樂器在光線下成為空間裝置的一部分,既是聲音的來源,也是視覺的雕塑。這種「樂器即舞台」的思考,呼應了當代音樂劇場中對聲音物件化與身體化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導演與技術團隊將《六部曲》的投影更升級,運用了即時攝影與投影的方式,將舞台上的局部動作擴大於螢幕,營造出強烈的現場感。這一設計在謝幕段落尤為動人:演出者的姓名與影像並置,使觀眾能即刻連結舞台上熟悉卻瞬逝的面孔,突破劇場常有的距離感,讓互動更為親密。此舉也巧妙延伸了作品「記憶」與「痕跡」的主題,讓觀看成為一場回望的行為。 從表演層面觀之,團員的肢體表現進步顯著。相較過往作品中偶見的拘謹與尷尬,此次舞台行走與動作節奏自然流暢,演奏者在角色與樂手之間的轉換更為自如。這樣的跨界訓練顯示團隊已逐漸掌握「演員樂手表演者」的多重身分,體現擊樂劇場的本質。然而,部分段落出現偏高的音質,使氣氛略帶親子劇場的輕巧感,削弱了作品的深層力度。
-
 澳門
澳門實際展演加上主題研討 「非常規空間演出」成澳門劇場秋季熱點
當「環境劇場」已成為被遺忘的名稱,「非常規空間演出」、「非典型空間演出」、「沉浸式」、「漫遊者劇場」、「城市漫遊劇場」、「新空間演藝」等演出分類紛呈,加上近年日常生活的急速數位化,劇場亦開始經常與數位技術連結,生產出新類型的觀演空間與關係。從去年至今,澳門就有超過50部不在常規劇院中舉行的演出,就剛過去的8、9月而言,就有近15部。這幾十部演出大部分屬於「澳門城市藝穗節」的節目,也有部分為民間劇團獨立主辦的製作。就空間分布而言,當中一半發生在古蹟、咖啡店、餐廳中,甚或是在黑盒劇場中但空間運用上以非典型的方式進行,觀眾大部分時間上還是一個觀看者、旁觀者的角色,只是演出中偶有需要觀眾參與、互動元素,不參與也無妨。例如四維空間的《銳舞︰搖擺的世代》便在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舉行,但觀眾進場後始發現平常的劇場空間已變裝成「Rave Party」的場所,沒有觀眾席、沒有清晰的觀演關係,舞者有時會邀請觀眾一起跳舞,但大部分時間你也可以靠在場邊觀看整個演出。
-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2025巴西CIRCOS — Sesc 國際馬戲藝術節(三)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2025巴西CIRCOS — Sesc 國際馬戲藝術節(三)以馬戲為核心的社會改造計畫
自 2010 年起,巴西社會服務機構 Sesc(Servio Social do Comrcio)在聖保羅發起 「CIRCOS Sesc國際馬戲藝術節」(CIRCOS Sesc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Circo),便逐步成為拉丁美洲重要的當代馬戲平台。藝術節強調去中心與普及化,節目除分布於市中心的多個場館,甚至走入低收入戶、遊民集結的下城區,讓不同社群都能接觸到國際與本土的馬戲創作。 在巴西多元種族、貧富差距及文化衝突的複雜背景下, Sesc被視為巴西民間版的「文化部」,其任務涵蓋教育、體育、藝術與社會服務,網絡遍布全國,光是在聖保羅,Sesc就有40餘個綜合型場館。對Sesc 而言,馬戲藝術節不單只是表演藝術的集結,更是介入日常、關注群體、承載多元文化的社會實踐。 CIRCOS策展團隊組成非常多元,從表演藝術領域,到建築、設計、文化傳播到法律與社會科學背景,本文採訪兩位核心策展人瑪麗娜.贊(Marina Zan)和娜塔莉.卡明斯基(Natalie Ferraz Kaminski),一探她們如何透過藝術節這個平台,貫徹Sesc的組織使命,彰顯馬戲作為文化治理工具的潛力,回應社會的挑戰的同時,也成為和所有觀眾共在、思考與感受的藝術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