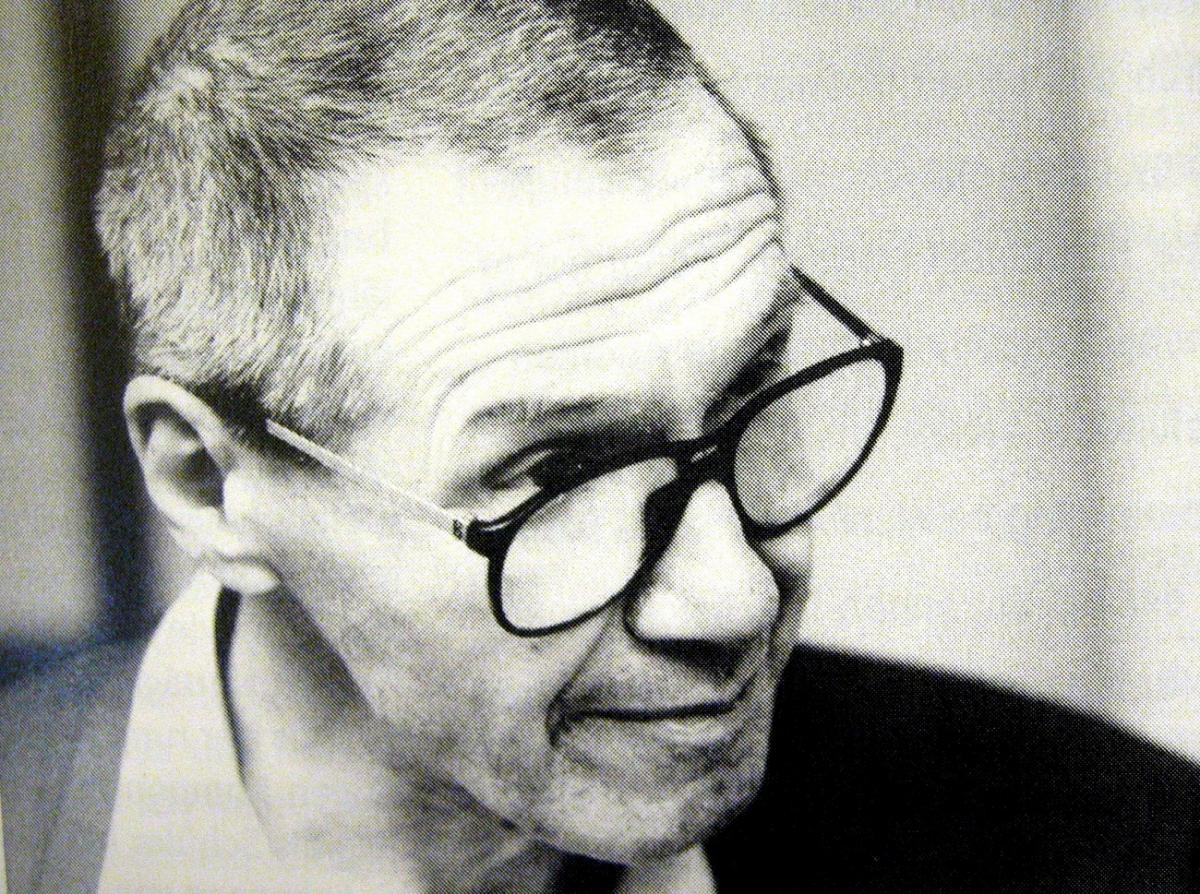小說的原生地在書場,其表演的、大眾化的本質對戲曲藝術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和啟發。正如小說不畏冒犯正統歷史一樣,具有獨特表演美學的戲曲也不會拘泥於小說,尤其是當代的新編戲,為了揭示創作的意義,對歷史、小說的解釋權不遑多讓。
國立國光劇團《王熙鳳大鬧寧國府》
5月23〜25日
台北國家戲劇院
戲專京劇團《翼德的情人》
5月7〜8日
台北新舞臺
在西方,戲劇列位文學之林,自古而然。反觀中國的戲曲,其唱、唸內容所訴求的雅趣或諧趣,循的不外中國詩、詞、謠的傳統,究其劇目,更是大量取材自中國古典小說;然而,因為戲曲乃「合歌舞演故事」,以演員為中心的表演體系鮮明而鞏固,其經典的建立,倚賴表演的程度遠勝過文本本身的文學性,相形之下,戲曲的文學系譜便不像西式戲劇那麼受重視。
四大小說原生於書場上的表演
在中國文學的「大」傳統中同樣被視為小道、裨類的戲曲和小說,其實淵源頗深。它們同樣是包含角色、動作、對話、情節的「故事」,只不過,相較於早出的小說,由演員在台上以唱唸做打虛擬出角色、情境的戲曲,顯然是更新奇而生動的載體,又因看戲、聽戲撤除了讀小說的「文字」門檻,受眾更多了。在戲曲作為大眾流行文化的時代,不斷的演出使劇目的需求量極大,小說有現成的故事,廣為流傳者尚有現成的知名度,自然成為優先考慮的取材對象。從實例上看,經典的小說未必適合各劇種,即使順利台上見了,也未必一定能「演」成戲曲的經典。但挑戰文學經典畢竟是很大的誘惑,故有「中國四大小說」之稱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一直以來都活躍於戲台之上,經過累代的錘鍊、創造,不但相關劇目多到有所謂的「三國戲」、「紅樓戲」,其中變成戲曲名作的也不在少數。
四大小說堪稱是戲曲所踩的「巨人的肩膀」,但事實上,四大小說除了曹雪芹的《紅樓夢》之外,餘三者在成書之前,書中的故事老早經過歷代的職業「說話人」在市井的書場錘鍊、創造,還有許多作為表演底本的「話本」應運而生,像最有名的「說三分」(即說《三國志》),從宋代起即是書場中的一門「專科」。由此可見,署名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作者的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等人,其實也是踩在「作者集團」的肩膀上集其大成的。正因為這些小說的原生地在書場,為了提供當下的聽覺娛樂,不可能曲高和寡,而且,其本質原來就是表演的、大眾化的,包括一人飾多角的說話人要有音韻鏗鏘的聲情表演,人物要清晰,故事性、趣味性要很強,在「且聽下回分解」的結構中,一個人物牽引出一個人物,一個情節牽引出一個情節等等。這些特色爾後對戲曲藝術都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和啟發。
各劇種發展不同的小說劇目
戲曲聲腔繁多,各自形成不同的劇種調性;劇種的劇性各異,也使它們在向小說取經的路向上各有不同的取捨。例如,越劇、黃梅戲的聲腔、身段多陰柔之風,歷來即擅長兒女情長的戲,因此詮釋起《紅樓夢》以寶玉、黛玉為重點的戲,猶如當行本色,十分對味。相對地,陽剛味重的京劇演寶、黛之情,就有點像關西大漢打著紅牙板唱閨情,雖屢有新編,也熱門不起來。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裡,京劇(尤其是京朝派京劇)就合該演英雄豪傑忠孝節義的大歷史,如「三國戲」,或是展現表演功法的戲,如出於《西遊記》的《美猴王》,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不厭精細的《紅樓夢》顯得瑣碎、施展不開。
實際上,《紅樓夢》非僅寶、黛之一端,它和其他章回小說一樣,人物眾多、事件迭出,對有「紅樓作手」之稱的陳西汀來說,《紅樓夢》直是取擷不盡的寶藏。他前後編了八齣紅樓戲曲,王熙鳳掛在劇名的居其三(註1),另外,還有讓前輩京劇名角童芷苓從舞台紅到銀幕上的《尤三姐》,刻劃寶、黛之情的黃梅戲《紅樓夢》以及崑劇的《妙玉與寶玉》等。國光劇團即將推演由陳西汀編劇、童芷苓晚年的代表作《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這齣戲之所以能與文學原著各得各的光采,首功固然歸於好演員的二度創作,但也多虧劇作家對這個大宅門的人情世故有深刻的體悟拿捏,經一番刪繁就簡,再以文學寫戲曲、更寫人性的深厚力道化入京劇的表演之中,該劇方能成為紅樓京劇的佳作。
中國的古典小說何其多,被派上戲場的當然不限於這「四大」。拿台灣的布袋戲、歌仔戲來說,在它們的「古冊戲」(註2)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沒有缺席,但有更多取材自《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楊家將演義》、《封神榜演義》、《孫龐演義》等通俗演義小說的劇目,而這些通俗演義小說與宋代以降傳下來的講史、平話,莫不有密切的關係。歌仔戲在內台的時代,因為時興演「連本戲」,從章回小說延伸而來、可以一天接一天演下去的劇目遂得到長足發展的時機。一九六○年代初期,台灣曾盛行拍黑白的歌仔戲電影,這些通俗演義遂一系列一系列地跟著戲班上了大銀幕,如本於《征東》、《征西》的《樊梨花下山》、《薛剛大鬧花燈》、《薛剛三祭鐵坵墳》,便是其一。退到外台之後,在廟會演出的脈絡裡,這些有朝有代、教忠教孝的「古路」劇目便被置於日戲(即下午的演出),主為酬神,兼以娛人。
小說是新編戲曲的幾塊拼圖
對昔日布袋戲、歌仔戲的表演者和觀眾而言,「古冊戲」幾乎同義於「歷史戲」。但戲台上的歷史,其實是正史游於「藝」之後,由說書人、小說家和戲曲藝人共同鋪演出來的,它和正史的差異,除了反映民間與官方對所謂史實的觀點不盡相同之外,也與劇性以及演出條件有關。例如,同樣是「關公戲」,歌仔戲處理的方式就和京劇大不同。京劇中由關雲長擅其場的經典,包括《單刀會》、《斬顏良》、《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戰長沙》等,歌仔戲受京劇影響很深,觀眾又嗜看關公戲,所以歌仔戲也有不少同名劇目。然而,因歌仔戲演員多為女性,且向來偏重小生、小旦行,故能勝任關公的武老生可遇不可求,關公戲的發展自然有限。最常見的,是在正戲開演前的「加演」(註3)中,安排一段如《斬蔡揚》的關公戲,這種三十分鐘不到的段子沒什麼情節,目的僅止於賣弄關公騎馬、耍大刀的功架。關公若出現在有情節的正戲裡,做法之一,是仿傚同名京劇的穿關、情節,唱曲則夾雜「外江」、北管以及歌仔戲等諸多曲調(註4),形成京劇為體、歌仔戲為用的關公戲;此外,歌仔戲為了藏拙並揚其所長,還杜撰出關羽「打紅面」之前的身家故事,從「關公出世」演到「桃園三結義」,也算是另類的歌仔戲關公戲。
正如小說不畏冒犯正統歷史一樣,具有獨特表演美學的戲曲也不會拘泥於小說,尤其是當代的新編戲,為了揭示創作的意義,對歷史、小說的解釋權不遑多讓。像去年國光劇團演出的《閻羅夢》,雖然從《三國志平話》到《喻世名言》,小說文本有跡可循,歌仔戲也有出於同源的劇目名《三國因》,但《閻》劇新穎且耐人尋味的題旨與形式,其實大半出於編導的提煉、創發。如《閻》劇當中的戲中戲融入了幾個取材自小說的傳統戲,即曹操/關羽的《華容道》、呂后/韓信的《未央宮》等,看似老戲,實則經過重新設計(註5),以兼顧表演和劇中人性格,成為符合戲之需要的典故。因此,若說《閻》劇「改編」自小說,並不適切。
過去的傳統戲大多是摘取小說片段出來,斟酌取捨之後,再加以形象化,便成一齣戲;而新編戲較傳統戲更注重首尾完整,以及契合現代人的情感思想,故對其而言,小說可以只是戲的幾塊拼圖。戲專京劇團的新戲《翼德的情人》就突顯了這樣的新關係。《翼》劇的創作靈感來自「三國戲」的《定軍山》,編劇從諸葛亮點將、老將黃忠取代猛張飛前去迎戰敵將夏侯淵一段戲中,硬是窺出了端倪。他結合「夏侯淵有一女」的野史記載,令張飛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娶了夏侯女為妻,於是陣前面臨翁婿交戰的掙扎。《翼》劇試著重塑張飛的形象,舞台上還有類似小說「意識流」的實驗,以戲中戲刻畫夏侯女想像中的張飛。雖然創新不必然成功,但在在可見當代戲曲推陳出新以抓住觀眾的強烈企圖心。
(本刊編輯 施如芳)
註:
1.即《王熙鳳》、《王熙鳳與劉姥姥》、《王熙鳳大鬧寧國府》三齣。
2.泛指改編自中國歷史演義小說的劇目。
3.戲曲界有「女演員不能扮關公」的禁忌,早期歌仔戲班「加演」作關公戲,經常自京班借將。
4.歌仔戲演關公一定唱「外江」,以顯其威武,所謂「外江」就是京劇的曲調。
5.參見王安祈〈關於《閻羅夢》的修編〉,《國光藝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