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想來,這個「拍」字,就是所有的「記」,記錄的記,表現的記,熱情悲傷,冷靜沉思的「記」而已,我要是真能把自己的生活記得如此多彩,記得那麼豐富,我就可以化成一縷青煙,揚長而去了。

當我們的肢體在一種時間性的安排下劃過空間,或在空間中暫時駐足,旋即又動,然後以時間的累積成為一串印象,我們稱它為動作。動作用來過日子,也用來跳舞。過日子講求的是功能,跳舞講求的是表現,用的是同一付軀體,要求卻是天壤之別。

他們演奏的都是魁北克的民謠,在場的每個人都對這些曲子耳熟能詳,除了我以外。他們輕鬆地對我說:「隨興地跟上吧!」這些曲子的和弦還算容易找,但是,節奏可就不輕鬆。我實在搞不定到底在哪要少一拍,還是多半句,每當曲子回到副歌時,我總是會搶拍而出糗。最後終於有人忍不住,半開玩笑地說:「你確定你讀的是『音樂』博士嗎?」

打著批判、實驗、人性旗幟的製作,為何常常看起來像是粗糙的團康晚會活動?雖然還是會得到很多溫暖的鼓勵。讓人盯著旗子,會不會讓自己和觀眾忘了風景?既然是看風景,有這麼害怕迷路需要做旗子嗎?我面向的就是事物面向我的,所以會不會實際上我呈現的是:我需要這些溫暖的鼓勵和讚賞?

如果說一個人,在靈修的路上沒有迷過路,那大概很難,沒有遇過很多好老師,這也難說,有的時候自己就是老師,每人資質、悟性不同,不過人生的大方向還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方向搞不清楚,所以個人也好,社會也好,就暫時迷路了,我,我說的我,就是我,就是你認識的那個我,現在有點迷路了,別理我,別煩我,只要關心我就行了,我自己會好

這時,心隨著眼光的轉移,時起彼落地舞動著。隱性的動作伴隨著顯性的變化,有速度、有方向、有綜觀、有微觀、有節奏、有旋律,自若地跳躍於有形和無形的空間之中。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只有在屋子裡電風扇擺頭間所流逝的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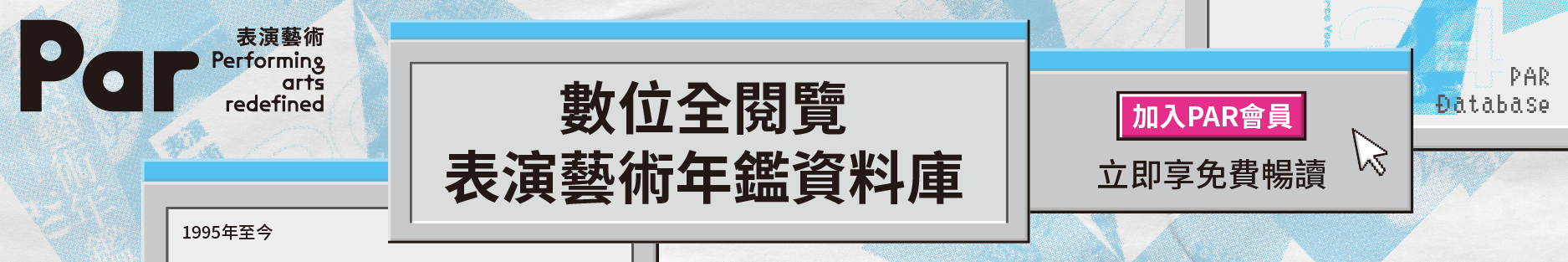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經過那麼些年的老歌伴唱,我終於了解我的外公有多厲害,不管我彈什麼歌,大家唱什麼調,他老人家總是能輕輕鬆鬆地跟著音樂,讓他絕佳的音感和音樂直覺帶領他的手指,從不彈錯一個音。這時我發現,我之前對他這種「不會看譜就不會成功」的想法簡直就是大錯特錯。因為,不管何時,只要有人點了歌,他都能立即伴唱,不像我,總是要等到我找到譜才能開始。

人到了某個年紀常會提到「勿忘初衷」,我忘性好,想不起來我做劇場的初衷是什麼,不過也會懷疑初衷是可靠的嗎?還只是一個虛擬出來安慰自己、合理化現狀,類似童年創傷的幻象?初衷會不會反而讓自己怕改變,更固執,更無法面對變動?如果真有初衷,為何初衷彷彿像初戀一樣美好?為何忘不了?

別老跟自己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七十而自由自在,過去我怎麼怎麼,現在我如何如何,這都沒用了。就是「現在」,現在在深山裡,就深山裡,在沙漠裡就沙漠裡,在大海的風口浪尖裡,就風口浪尖裡,在大糞坑裡?那如果能待得住,那也就在糞坑裡了;只要一想到萬一:隧道裡著火的那輛車是我!就算在哪裡都得「該幹什麼幹什麼」

就在上完那堂課之後,我快樂得不得了,體會到能感受自己的身體,跟自己的身體對話,原來是跳舞最大的樂趣。不為別的,以為會成為舞蹈明星的大夢,原來只是兒時不清楚自己的假象。自小一路走來會使自己繼續堅持跳下去的原因,就只因為「我真是喜歡跳舞這回事」啊!一種豁然開朗的愉悅,再度把我帶回到舞蹈教室裡頭。

另一個公證紀念日,只有在記得時我們才會慶祝。方式通常只是寫個卡片,還是一起吃個晚餐,或是給對方來場按摩而已。但今年,我突然在公證日那天下午想起這件事,而且我有個靈感,想要來唱那一首我正在認真學、好美的台語歌送給我太太。她並不知道我在學這首歌,所以這一定會是個驚喜!

不管哪一種,「報」都是一個審判的情境。完全符合現在多數媒體的「報導」,同樣是秉持著公平、公正的面貌的一場審判大會;更不用說「報仇」基本上就是懲罰有罪之惡人的正義行動。


我算是很不常逛西門町的,要去,多半是去國軍文藝中心看京戲,從十六、七歲就開始花錢看戲,把當時台灣最好的、三軍各劇團的演員,從年輕看到他們中年,再從中年看到他們退休,我也就不再去那個地方了。因為傳統戲曲,完全是看演員,精采的演員不在台上了,觀眾也就散了

看著系上老舊的設備,想不懂自己為什麼要跳舞,因為不跳舞好像才是令人快樂的事。於是我開始翹課,打混過了將近一整年。說實在的,翹課一點都不是愉快好玩的事,因為不知所措所以才翹課。翹了課卻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常常自己躲著哭,心裡一片茫然

當我發現一顆小小的蛋在鳥籠裡時,我驚訝得目瞪口呆。接著,我開始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就像你拿著對中大獎的樂透彩券時會有的亂跳亂叫一樣。我等不及要告訴別人,但是當時,我太太不在家,我的兩個女兒都在學校。我看著我家正懶懶地倒在地上睡到打呼的黃金獵犬珊迪,忍不住把牠搖醒,對著一臉疑惑的牠大叫:「珊迪,我們有小寶寶了耶!」

「監」的水面或鏡面,在現代應該就是手機的鏡面。隨時拍照,留下自我監視的證據;隨時上網,讓自己處在監視網中;隨時打卡,讓別人監視我在哪裡;一直加好友,可以讓更多人監視我。 一種正面積極被迫害妄想症的充實人生。 所以,當我監視我自己時,我的自己裡面有眾人。

十八、九歲的學生時代學會逛街,不買光看,很多資訊是看來的,看過黃牛賣票,看過色情皮條客拉膽小的男人進黑店消費,看過三、四十歲的外省軍人穿便服打架、憲兵來了全都跑人的神情,看過多少還留著西裝頭的男人,帶著穿旗袍、佯裝的女人,在西門町劃過。多少人匆忙地在等最後一班公車回家。

在我數十年的「專業」經驗裡,蒐集各種知識是為理所當然,也以為自己已有身經百戰的能力。可是這些學習傳統舞蹈的舞者,對我就像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跳舞人。他們讓我見識到自己的不足與自以為是,時間太短,我雖然從他們身上看到許多的既成事實,但是有太多的究竟還來不及明白。


我開始緊張了,當那個容易彈錯音的段落愈來愈接近時,我不由自主地開始禱告,我心裡吶喊著,用盡了全身的渴望乞求著:「親愛的天父,拜託讓她彈對所有的音,拜託,拜託。」而當我女兒完美地彈奏完那討厭的段落時,我居然抬頭仰望著天花板,非常誠懇地對著天花板說著:「感謝主!」

兩位崑曲大師傳承教導的過程,呈現了「古」的動人場景。口傳過程會徹底了解許多事情是無法書寫下來的,它會因為不同人的理解,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溝通方式和爆發不同的火花,也因這不確定性,反而有更多「古」的新可能性和莫名厚度。

在天災裡失去父母的孤兒,因為還不太清楚,也比較不出什麼叫失去,加上成長的忙碌,使人類會忘卻痛苦,所以我們十年後再見到那孤兒,已經成為一個充滿陽光、力求上進的人,或者起碼在他臉上已經讀不到那麼多失去親人的痛苦了。反觀,失去一個小孩的父母們,從小孩失去生命的那一天開始,一輩子都無法再真正歡笑了。

活在這副身軀之內,時時刻刻受到各種因素的衝擊;在每個生命的階段,感受到不同層次的身體經驗。身體就像一個實驗場,只有身體力行可以一窺究竟,你還不能隨便說不玩了。對於這種無所遁逃的功課只能束手就範,順便在一旁讚嘆:大哉身體喔!

要成為一位老師搞不好很容易,但是,若要成為一位能引導學生、因材施教、有耐心、有愛心,又能啟發學生、觀念正確、對學生有好的影響力的老師,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如果一個想學音樂的孩子,能遇到一位這樣的老師,那當然,這個孩子不會變壞。

若將味覺視為劇場,舌頭視為舞台,許多問題和思考是一致的,例如文創產業。像慢食這樣的理念當然不是為了訴求菁英品味,或是宗教式的理念信仰,慢食宣言起草人義大利詩人Folco Portinari曾說:「慢食運動,應該要由人類崇高的遊戲心所支持,而遊戲是不能成為宗教信仰的。」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