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裝舞會裡的政治伴奏
導演的創意如柳暗花明般宛轉到來,這種緩緩的力量如果持續不斷,戲就好看。

導演的創意如柳暗花明般宛轉到來,這種緩緩的力量如果持續不斷,戲就好看。

二月廿日〜三月九日期間,在香港的文化中心大廳,爲了配合碧娜在藝術節的最後一檔大製作,特別展出自一九八二年就開始只爲碧娜的舞團拍照的義大利攝影家法蘭契斯可.卡波內(Franceso Carbone)的碧娜舞作攝影展──Only You. 十六歲就開始學攝影至今,卡波內原本是從事電影攝影、後來因感覺拍電影太浪費時間,才改做報社的攝影記者。晚上爲了調和白天的工作壓力,經常躱到劇場裡看演出,並在看過碧娜的作品後,毛遂自薦地跑去烏帕塔,爲碧娜及團員們拍照。沒想到,在一個下午之內,碧娜的氣質及工作態度深深地感動了他,使卡波內決定走上舞蹈攝影這條辛苦但愉快的專業。 這次攝影展的題目:「只有你」,雖然部分原因是借用碧娜去年以美西爲主題的新舞名,但卡波內表示,更重要的,是因爲他只爲碧娜一人奉獻他的技藝。十五年下來,卡波內已經隨碧娜及舞團到世界各地記錄了他們無數場的演出。即使一九九三年時,他在巴黎歌劇院拍烏帕塔舞團演出《伊菲珍妮在陶里斯》時,摔斷了脚,如今走起路來還一跛一跛的,但他仍欣然地跟隨碧娜到全世界,自願爲她及其舞者辛勤創作出的瞬間畫面,留下永恆的回憶。 (本刊編輯 林亞婷)

碧娜旋風,其實從去年十月碧娜與烏帕塔舞蹈劇場的團員到香港停留三週,爲新作尋找創作靈感開始。在香港藝文界人士熱心帶領他們走遍香港大街小巷、吃盡各地山珍海味之後,今年三月碧娜他們回到香港,展現在藝術節觀衆眼前的作品,也充滿香港居民的生活剪影。

在台北看《康乃馨》,感受極端複雜。碧娜.鮑許雖未親身到過台灣,但通過種種轉介,早已「有形」地影響了八〇年代以降台灣的表演走向因此,十五年後,在台北的舞台上初識碧娜,不啻是一次無比親切的「重逢」。

在移植前衛的經驗裡,台灣有許多控訴、嘶吼、歇斯底里以及諸多作者的喃喃自語,這次碧娜.鮑許又帶來了另類的理性,一種受過禮敎的野蠻,夠嗆!

一年一度的台灣區音樂比賽又熱熱鬧鬧的於北中南三地再次展開,評審、工作人員、參賽者、家長們忙碌的穿梭於比賽會場中。但是在熱鬧風光場面的背後,這項動員龐大的比賽歷年來經常被譏評爲台灣音樂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花費的金錢、人力與所收到的效果完全不成比例,要求檢討改進的呼聲歷年不斷。而每一年在比賽期間或比賽結束後,抗議電話與陳情信函更是滿天飛。

習慣用地圖看「遊記」的觀衆,如果不能謹記「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恐怕就會迷失在榮念曾的山海經緯裡。


別再喊「救救傳統戲曲」、「救救某劇種」之類的模糊口號了,想要保命,只喊救命是沒用的,讓我們一次一次、一個作品一個作品地革命,或許還有保命的機會。

同志藝術節的作品,使我對同志劇場的未來仍充滿期待。但這三個「扮裝以外」的作品,似乎沒有引起太多注意,這是同志劇場被貼上了扮裝標簽的後遺症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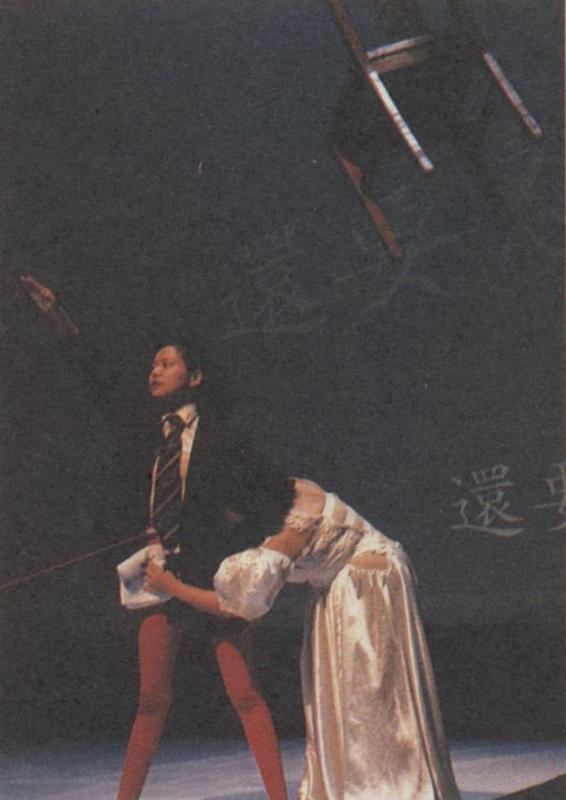
在「一九九七香港」這樣一個時空裡,一台歷史的大戲、歷史的活劇正掀開大幕。椅子的故事及各種不同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是兩岸三地的藝術家對遞轉嬗變的歷史所作出的潛意識的反應。

「一九九七」是甚麼?作爲一個香港人,問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多餘。但若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試問:對中港台三地來說,一九九七「可以」是甚麼?問題便變得耐人尋味。

我曾以爲台灣有比香港更強大的前進動力,現在不難發現台灣有另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往後拉。不是我們的政府如此,而是我們允許我們的政府如此。不是我們沒有選擇,而是我們放棄了選擇。

「中國旅程九七」的演出部分裏,六個作品中的「中國」, 幾乎都缺席而不可得見。其中的意義與背後的訊息殊堪玩味。


歷來,或爲劇情或爲展技,演員以一趕二、趕三飾演不同的劇中人,是台上台下兩邊酣暢的演出。近時卻每每可見一劇中人由多位演員分飾的表演,四個四郎,三個公主,或者單是〈拾玉鐲〉一折,前後出來四個不同顏色(服裝)粉紅、黃、藍、綠的孫玉姣。「改扮」或「分飾」在傳統戲曲表演中,是否完全自由隨興?

謝月霞,一九四三年出生於台中太平,生父家姓林,四歲時被縛入彩連社歌劇團,成爲團主謝連枝的衆多養女之一。 入班後改名謝三嬌,不到半年後便開始學戲,師事班中歌仔與大陸京劇藝人,因常以哭來抗議養女命運,幾乎天天挨打。約七、八歲時內台戲正盛,團主聽從算命仙之議,爲三嬌改名月霞,期望她成角兒。十二歲時,劇團被寄生的閒雜人等吃垮,謝家搭他班,待過勝光、三眞堂、劉文和等賣藥班及基隆益世電台、台中農民電台、南門電台、草屯電台等。十三歲時,謝月霞以《安安趕雞》、《訓商輅》、《烈女養夫》、《甘羅出世》等囡仔戲的小生聞名,被養母硬配給台中流氓,十六歲時,因參加地方戲劇比賽表現不符養父要求,被不停歇地揍了三十六小時,從此對參賽心冷;後加入台中中廣歌劇團,以梢聲小生(圈內人給她取的外號,因其聲腔沙啞)走紅,並全國巡迴演出。 養父去世後,謝月霞一心想離開戲班界,遂將幼時謝連枝所敎成套的四句連本子,如:《陳三五娘》、《山伯英台》、《雪梅敎子》、《梅開二度》、《菊開二度》、《安安趕雞》、《陳杏元和番》、《三娘乞水》、《孟麗君》、《孟姜女》等悉數燒毀,如今遺憾不已。 約廿二歲時,台北新大春劇團老闆三顧茅廬,將謝月霞聘來待班擔任文武二手小生,一個半月後,古亭區戲台成爲她的天下,交了三、四十個戲迷朋友,平均一個月演三十二天戲,個人平均每日紅面(賞金)收入萬餘,四、五萬元亦屬平常,到比賽時期更有日入十幾萬賞金的記錄。八、九個月後又爲楊麗花電視歌劇團網羅爲武生,演黑白、現場播送的電視歌仔戲,後離開電視界,搭過秀枝、雪卿、民權、鴻聲、民安等班,目前鼎力協助兒子王榮裕的金枝演社,並在生新樂九甲戲團「扑破鑼」(非固定搭班,而是支援性演出)。

印度國慶日來台演出的印度舞蹈家瑪麗卡.沙若巴伊,在主辦單位未將演出的文化背景與意義適度呈現的情況下,藝術工作已然產生了內在的危機。

夜市上一齣胡撇仔戲《俠女白小蘭》,讓看過胡撇仔的老觀衆驚奇:靑年仔也曉作opera;讓沒見識過胡撇仔戲的新觀衆訝異:這什麼烏白亂撇的opera。從日據壓制的悲情中發展出來的台灣opera,何以至今不曾光復。而透過覆面俠女白小蘭,卻使在胡撇仔戲台下分開的母子,復迎納在胡撇仔戲台上。

這場由交通大學主導的音樂會其實就是一次科技的展演,音樂家們利用「電傳視訊網路」讓舒伯特的《菩提樹》在兩地同時進行排練。但是由於技術上的限制,使得兩地聲音的傳輸延後大約0.5秒。這樣的演出重要的意義應該是在於把科技應用技術與藝術作結合,爲傳統的演出型態開創出另一種可能性。但是,如果單純以欣賞一場音樂會的角度來看這場展演,它失去了合奏者在演出當中彼此之間氣息的相互呼應所產生的合作感。

在貝那丁劇院可以看到培松地的最新劇作:《1949:假如6是9》。我們可以去看,我們應該去看。這齣戲是不可理解的,有人如此說。是眞的:那更好。


米榭爾.培松地重新修訂的《1949:假如6是9》,整齣戲一直籠罩著一種完美性的孤獨感,那是觀者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疏離,所造成的一種戲劇氛圍。在評論這樣的演出之時,羅蘭.巴特、沙特對於「詩」、「脆弱」的理解,似乎可以給我們一些幫助。

當晚的歌者可說都是一時之選,水準非常均衡,其中擔任主角「荷蘭人」的瑞士男中音慕夫(Alfred Muff)更是讓人印象深刻。陳秋盛的指揮留給歌者充分發揮的空間,在音量上也不會壓迫歌者。此次演出,中場沒有休息,三幕之間全以間奏帶過,一氣呵成,張力掌握的很好,完全沒有給人疲憊的感覺。蔡秀錦的舞台設計生動活潑,營造了足夠的氣氛。

台北這一場表演的導演用了許多後現代聲光手法,也襲用布萊希特《高加索灰欄記》戲中戲的元素與佈景,他刪略了原劇最後「救贖完成」的部分,得到二種張力,一是聖俗掙扎「多頭的結」,二是觀衆更加深層的吟味。

舞台上的戲,在演出時最忌拖沓。《十三妹》改編本的演出,放在何玉鳳替父報仇上面,那麼,著重的戲是在刀馬,當中夾入了〈悅來店〉與〈能仁寺〉的老套兒在內,不但在老觀衆的感受上,有新不如舊之感;就是新觀衆看來,也會感於文武戲份的不能融成一體。

嚴格說來,《天國出走》其實是台北越界舞團一九九四年創團首演《失樂園》的放大版、癲狂版,舞者用賁張的肢體去詮釋對混亂年代的熱情與狂想。

若說《超時空封神榜》的搞笑、卡通化、多元異質並置、反串、疏離、解構等諸種平面、無深度手法構成了這支舞的後現代風格,隱藏在《超時空封神榜》無厘頭背後的,卻是一層嚴肅的喩意。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