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一片健康的「台灣本色」
評《台灣,我的母親》原著作者在小說中,對於清朝以至於日據時代的農民抗爭,存著是一種悲憫的心,在控拆之中,是深沉而無奈的嘆息。如今戲劇將「悲憫」化成了「悲情」,把「控訴」加溫成了「揭竿起義」,為了農民、為了土地,頭可斷、血可淌,這種「鼓吹革命」的無情,觀衆難道不覺得熟悉嗎?

原著作者在小說中,對於清朝以至於日據時代的農民抗爭,存著是一種悲憫的心,在控拆之中,是深沉而無奈的嘆息。如今戲劇將「悲憫」化成了「悲情」,把「控訴」加溫成了「揭竿起義」,為了農民、為了土地,頭可斷、血可淌,這種「鼓吹革命」的無情,觀衆難道不覺得熟悉嗎?

從「多面向舞蹈劇場」多種表演形式的劇場探索,轉到今年的「如舞人舞團」,陶馥蘭的舞蹈已脫離了激情及深沈的表演形式,而回到簡單及自然。

「舞蹈異人世界Part II」跳脫舞蹈空間舞團過去一人編舞的經營方向,不同創作人的舞作讓舞團的作品風格趨向多樣化。三位舞者出身的創作者,顯然對身體的展現特別感興趣,舞台表現卻各有看法。

此次《光臨時間廊》和以往最大的差異在於作品風格的統一性,如不看節目單,還真會以為整晚的演出是出自一個編舞者之手。

舞蹈自身的價値有時甚至超出了其陳述含義的價値,從這個觀點出發,也許就不需太在乎「時間」是什麼,畢竟「舞以載道」不過是衆多詮釋舞蹈的途徑之一。

《刺桐花開》與《台灣,我的母親》已為歌仔戲編演近代台灣故事留下足跡履痕,更勇敢地躍向台灣歌仔現代戲的創發。欲由傳統戲曲的搬演程式過渡到現代戲曲的表現,也許還需要更多藝術工作者的投入,才能為兩者濟渡造橋。

相較於美國劇場界對愛滋議題的關心,台灣劇場界對相關議題的創作就顯得淡漠了許多。直接改編國外劇作的演出也許可以彌補對問題了解不足的缺憾,但是多花一些心思了解而後的眞誠創作,才是藝術家用創作抵抗愛滋的眞正意義


若以黃梅戲劇種自身的改編與發展而論,《鞦》劇最大的遺憾在於捨棄了黃梅戲裡原始的、俚俗的、卻充滿特色與生命力的小戲色彩,造成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黃梅大戲,無論是在演出内容與形式上,均有朝向京劇、舞台劇形式靠攏的現象,以追逐所謂「現代化」的改革與創新,而原來最具特色、與其他劇種分隔之界限,竟逐漸模糊、消失了。

「左」派份子的成員沒有專業舞團的資源,能在南部成軍已屬不易,她們都年輕且有熱忱、肯努力,値得鼓勵。況且此次演出才僅是第二年,假以時日希望能持續而累積出更好的成果。

《沙漏》在舞台設計、音樂選擇及創作意念上,都有不錯的想法,但在舞蹈語彙及架構上,卻無法與這些媒材或主題訴求產生靈巧而貼切的互動或呼應,十分可惜。

李.瑞金的聲音輕柔乾淨,可能更適合錄音,然而在國家音樂廳的大廳中,則顯得單薄而缺乏穿透力。他似乎也感受到這個大廳給他的壓力。

黃心芸的《涙》一開始就展現了舞台魅力,尤其她的右手及肢體的放鬆,使得聽衆在沒有壓力的視覺上,盡情地欣賞享受她的演奏。

卓庭竹與布拉瑞揚兩位雲門力捧、具潛力的編舞者,以十年不到的編舞齡能有此作已屬不易。期待新一代的編舞者能熬得住並且持續創作,多思考、多歷練,成爲台灣編舞界的生力軍。


彷若世紀末總要有個大回顧、總整理之類的儀式,此次的屛風演劇祭即有大會診的味道,不同劇種、風格的劇目在三個禮拜內連演,雖然劇場是小的,但是劇目卻包羅萬象,短短三星期可以看到風格迥異的演出,無疑是進入戲劇大觀園。

一則是由於劇中人物的自我認同與所處的空間,一則是由於所觸碰議題的私密性,《天亮之前我要你》的戲劇情境是相當封閉的;而和這個封閉的戲劇空間/情境相對應之下,《天》劇的角色們也建立起一個封閉的關係網路,觀衆只能冷眼旁觀,或者偷窺竊喜。

偷窺眞實,原是誘人的元素;觀衆透過第四面牆窺見一場百無禁忌的私密聚會,卻因爲距離(展演形式與戲劇文本)的稀釋,轉化成不酸不辣的白開水──除去止渴,沒有其他趣味。

對於流著南歐血液的他,德奧傳統那又沉又厚的低音,或許是難以承受的重。辛諾波里追求的詮釋固然引進了活潑、明亮感,卻也讓音樂帶著浮躁、不安定的氣息。

聆賞著這段淒美的牽手情緣,在刺桐花開的季節裡幕起幕落,讓我們見識到歌仔戲力求突破的新實驗。然而,是否創新一定要棄守歌仔戲的「主體性」呢?戲曲的現代化,並不意味著要與傳統決然斷離,而應該是「立足傳統」再加以「轉化創新」吧!

整齣《惡男情書》流露出小品劇的氣質,這類論述城市男女心情的故事其實很容易引起一般觀衆的共鳴,夾帶原創劇本貼近本土生活的特性,在擁有越來越多固定觀衆群之後,戲班子劇團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小品式的作品能更見醇厚、餘韻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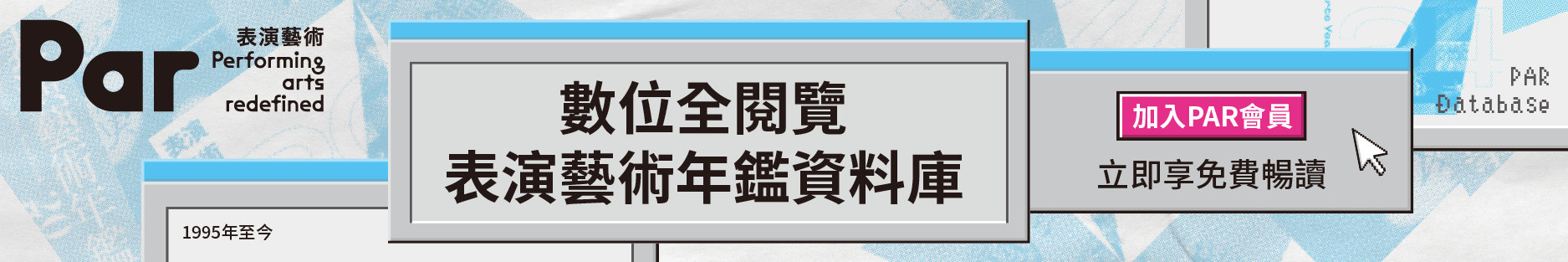

感動不見得與濫情劃上等號,但是感動也絕對不是一種感情表現的圖騰;過度強調感動的藝術鑑賞論的結果,不只化約了藝術鑑賞的複雜性,也容易一不小心就淪落成爲濫情。

「四物遊擊」一出場,馬上將聽衆帶入另一個時空,持續強烈的音響鼓盪在音樂廳裡,白緞帶隨著演奏者的遊移不停地飛舞飄盪,雖然絕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聽到、看到這樣的表演,但是絲毫沒有任何隔閡。

朱哲琴,站在一個漆上金色的五級活動高台上,背後的天幕投射燦爛的金色雲海,那莊嚴而空靈的樂聲,鮮活地描繪出藏人把死亡看成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沒有半點悲傷。

張岫雲六十餘年的表演藝術生涯,在她卸下戲衫、潛心向佛之後,終因其不容忽視的卓越成就,與多位女弟子在海峽兩岸的亮麗表現,又再度使她成爲衆人的焦點。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在今年一月舉辦的「千禧風華」兩岸豫劇聯演活動,是一記遲來卻隆重的注目禮。在國立戲劇藝術中心成立前夕,面對諸多問題喧騰未定的局勢,在此回顧張岫雲與台灣豫劇的發展軌跡,更有其積極性的歷史意義。

巴魯耶哥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對不同時期音樂的風格皆有不同的詮釋,他的技巧是爲了表現音樂,而不是爲了技巧本身而存在。西裔英籍的包尼爾是第三度來台演出,三次演出曲目大同小異,他顯現出過人的技巧及豐富的音色,但也由於這些優點造就了他的缺點

拉脫維亞是個俄國風味濃厚的國家,民族性情反映在音樂中,就顯得率直厚重,而拉脫維亞向來也有悠久的合唱傳統,在這一次的歌劇演出中可以印證這一點。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