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與求變的現代川劇《變臉》
魏明倫以其一貫喚醒女性意識、尊重女性社會角色的關懷與省思,創造出狗娃與水上漂這一對祖孫,其實也是另一場男女議題的爭辯。只不過他將重心從男女關係轉化成爲祖孫情感,更符合傳統苦情戲的特質。

魏明倫以其一貫喚醒女性意識、尊重女性社會角色的關懷與省思,創造出狗娃與水上漂這一對祖孫,其實也是另一場男女議題的爭辯。只不過他將重心從男女關係轉化成爲祖孫情感,更符合傳統苦情戲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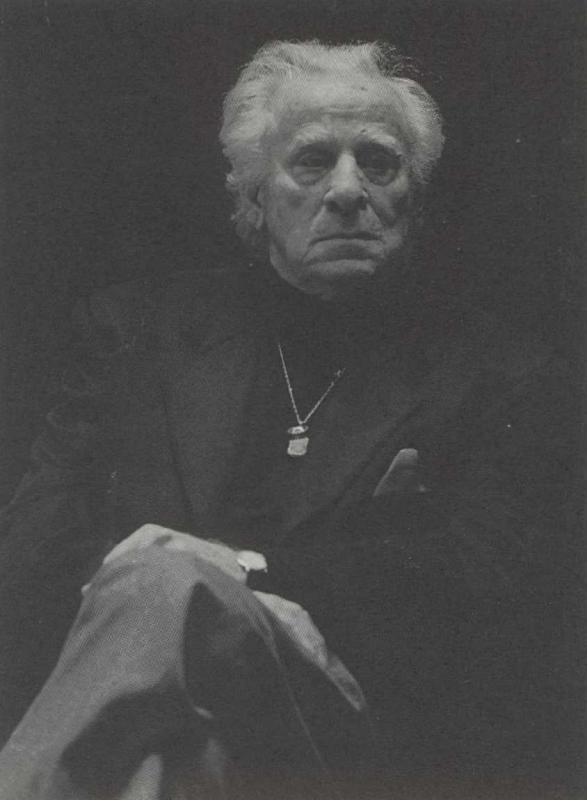
陳宏寛充滿豐富個性的鋼琴彈奏,早已跳脫出一般人所習慣性期待的聲響技巧展現與感官愉快的追求;當他單獨彈奏時,讓人聽到鋼琴家獨特的彈奏個性與非比尋常的藝術特質。

他是一本文法大辭典,一個個音符聽來都對,譜子上一個個連線符號,一個個強弱標記都亦步亦趨忠實於原作,但連起來一聽卻什麼都不是了。現在的他是「廉頗老矣」,他的疲倦是從心底裡透出來的身心俱疲。

今年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根據他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京劇《駱駝祥子》,在年初北京舉辦的「第二屆中國京劇藝術節」上,獲得頭名金奬。一些戲曲界的專家紛紛高度評價此劇是「本世紀京劇現代戲的壓軸之作」。

由香港進念.二十面體策劃,海内外不同領域華人藝術家「同台獻演」的「中國旅程」,已經進入第三年。 演出部分今年請來了北京的孟京輝,上海的張獻,台北的魏瑛娟,澳門的李銳俊,香港本地的陳炳釗和榮念曾。其中半數(張獻、魏瑛娟、榮念曾)爲去年「回鍋」的客人。這種組合,持續交流的意義遠大於「競技」,雖然兩者並不牴觸。

一直以來葛羅托斯基被套以不同的思想主義解讀,不同的文本呈現不同的葛氏說法,以及隨即而來的爭議,「葛羅托斯基」已然成爲一個複合名詞,定義隨著文本而漂浮。大師已故,如歐忍辛斯基語重心長地說:「豎一座紀念碑將是讓他眞正死去的鬧劇」。

導演爲本地示範了前衛活潑的高難度劇場作品,然而也在如此複雜的語言指涉裡,犧牲了觀衆對這齣戲及其原典中淋漓挖掘的人性往復的期待。


克雷默的CD已達百張以上,曲目包羅萬象,得獎作品不勝枚舉。他不但樂於首演當代作品,更勇於發掘新聲,不少作曲家因爲他而受到世人矚目。

欣賞弦樂四重奏時,絕對不能只聽單一的旋律或聲部,而必須考慮整體,否則將無法聽到音樂的全貌。一個理想弦樂四重奏的演奏應該是大家一起都「同意」以某種方式來進行,然而茱莉亞弦樂四重奏這次的演出並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

此次茱莉亞建團五〇年來首次上海之行,演奏作品的年代跨越了三個多世紀,足以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十足的大師風範。

布克納依眞實故事改編的《胡錫傳》,是多位導演執導下常演出的劇碼。今年香港藝術節請來瑟夫.納殊的舞蹈劇場,又是《胡錫傳》另一場跨界版本。

庫尼取材於政治意味特濃的緋聞,未必有所影射,重要的是有賣點。然而,如果沒有圓熟的編劇技巧,賣點不可能成爲賣場。活用傳統浪漫喜劇諸元素就是庫尼展現的編劇技巧。

洋溢《鄭成功與台灣》全劇的光明色彩,劇中不時出現「革命者」握拳仰視前途的畫面,如此單純信念是全體創作者的選擇;但「思想起」這素樸的聲音,與偉人聖潔化事蹟之間,連繫的是什麼?


或許是想轉型,或許只是嘗新,該團本季邀請自英返國的黎美光,編作三支口味淡雅的赤足小品,然而實際呈現於舞台的光景,卻未能如預期夢想般綺麗,甚或有些淒淸。

自古以來,不論中外,人們爲藝術最高的境界定下了一個標準──眞、善、美。柏林愛樂首席獨奏家室內樂團首次來台的兩場演出,相信爲熱愛古典音樂的人們,對眞、善、美帶來新的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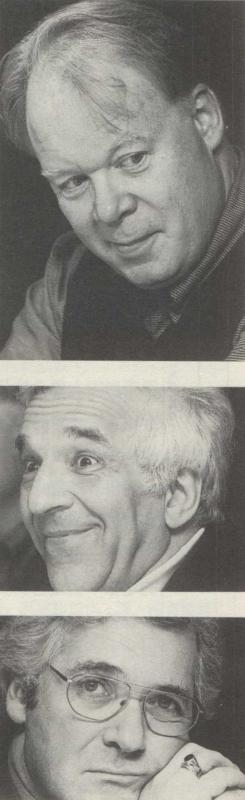
除了擁有「技巧無懈可擊」的共通性之外,阿胥肯納齊的冷峻工整與祖克曼的感情奔放或哈瑞爾的和煦柔腴,可說是南轅北轍,非常不搭調。因此他們的演出,並非建立在親密的合奏關係,反倒像是互較高下的競奏。

從電影搬上舞台的作品,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商業性,如此才足以支撐「搬上舞台演出」的效果。果陀所選擇的費里尼《卡比利亞之夜》,雖然不是一部大多數觀衆都熟悉的電影,但是苦命又樂觀的妓女和落魄夜總會主持人之間沒有結果的戀情,卻具備了音樂歌舞劇必要發展的可能情節。

整齣戲是一幅意識流的拼貼,雖有神秘意境,但事件的軌跡卻模糊難辨。劇本刻畫人物與情節用盡極巧、非常細瑣,但大量卻片斷的歷史訊息以及過多全知觀點的敍述,讓這場皇帝夢像喃喃自語的散文篇章。

多樣片段的影像在視覺中殘留,卻也似有似無巧合般地銜接,給荒謬劇場一個新的窗口,也使得多焦的思緒同步運行。結局是什麼?什麼是完整?似乎不是很重要了。


這種依附史實(或歷史故事)變奏創造的人物與情節,有其創作的方便性與結構的曖昧性,更有時間與空間、遊戲與競賽、眞實與虛擬的多重辯證趣味。

我們終究還是無法眞正穿透《春季》的曖昧與沉默,無法眞確地貼近創作者的意識與直覺,在戲劇動作與現實情境之間建立起眞確的聯繫,而只能接受創作者溫柔的拒絕(詮釋),讓自己的意識像演出的投影螢幕一樣,任他將一幅幅的畫面、一段段的聲音貼上或撕落。

《春季》靈感取自日本十九世紀浪漫派作家泉鏡花的小說《春晝》及《春晝後刻》,原書講述的是一段在陰陽兩隔後仍相互追尋的淒美愛情,到了小池手上,意境被無限擴大,連性別的界線也模糊了。百年後的《春季》,勾勒的到底是末世紀的前景,還是憂國者的心像,或者,一切不過是午後寤夢裡的浮光掠影?

此次《荔鏡奇緣》,選取了閩南語系中的古老戲文〈荔枝記〉做爲演出骨架,以加強「故事情節」爲訴求,更加顯示「漢唐樂府」立意邀請觀衆進入南管世界的誠心。

報紙廣大的發行範圍,和電腦網路的新鮮魅力,或許對戲劇推廣會有相當成效,但粗糙錯亂的評選活動對這樣的目標絕無助益, 只會讓創作與欣賞的專業知識與態度離我們更加遙遠。

以一位未接受完整肢體訓練的創作者而言,可能會令人擔心舞作的語彙是否合理?內容是否豐富?會不會覺得「外行」,但從「畫家從舞」的方向去看它,創作的元素更爲豐富,表現的方式又有更大的可能性。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